影响你生活的虚拟空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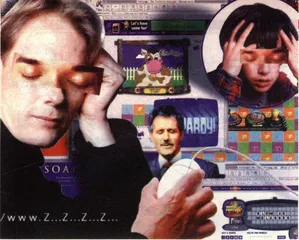
另一个空间
1982年的某一天,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年轻美裔科幻作家,在温哥华的一条娱乐街上闲逛。街道两旁有许多电子游艺厅,看到厅里孩子们在电子屏幕前聚精会神打游戏的情景,吉布森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从他们高度紧张的姿势中,我能体会到这些孩子有多么入迷。似乎存在某种循环:光子由屏幕激射而出进入孩子们的眼睛,神经元在他们的体内游荡,而电子则在游戏中到处运动。这些孩子显然相信游戏机所投射的空间的存在。”
这一景象在吉布森脑子里盘桓不去。他不懂计算机,也没怎么玩过电子游戏——但他见过许多计算机迷和游戏狂。他发现,几乎所有沉溺于计算机游戏的人最后都不能自拔,把想象的游戏空间视作真实的存在。“他们开始相信,屏幕之中另有一个真实空间,这一空间人们看不到,但知道它就在那里。”
吉布森把这一空间命名为“电脑化空间”,并把它作为他的小说的前景。在这些小说中,电脑化空间是一个由电脑生成的空间,故事人物只要插上插头即可进入,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脑中植入插座,以便接通电极。当他们到达电脑化空间后,能够看见巨大的三维信息库。电脑化空间就是电子数据所居住的那个飘忽不定的空间。
这一空间并不难于感知。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拿起电话和朋友通话时,你们的谈话在何处进行?在你桌上的电话机里吗?显然不是,肯定也不在另一座城市的另一部电话中。它似乎是在两部电话之间的某个地方,在外面的一个无限的空间里。在那里,你们两人相见并且互相交流。
苏东坡的《琴诗》问得好:“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根据约翰·佩里·巴娄(JohnPerryBarlow)的说法,电脑化空间可以通俗地表述为“当一个人拿起电话交谈时所进入的那个空间”。巴娄从前是摇滚歌词作者、牧场主、诗人哲学家,后来成为计算机爱好者。他的定义虽然简单,但却易于领会。
如果这一定义成立的话,那么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到过电脑化空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打电话时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你和别人通话时常常会觉得双方坐在同一间屋子里。
当然,电脑化空间的范围比一次通话所涉及的要大得多。它集合了成千上万台由调制解调器连接到商业性的联机服务大公司之上的个人计算机——当然是经由电话系统的——以及更多地通过高速线路与局域网、办公室电子邮件系统和Internet连接的电脑。它还包括:迅速扩张的无线通信设施,如传输着大量移动电话信息和数据的微波塔;仿佛明珠一般镶嵌在同步轨道中的通信卫星;还有那些不久就会像忙碌的小蜜蜂一样在地球上空飞来飞去的低轨卫星,用来把相距遥遥或是不停移动的人群结为一体,等等。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电视机实现了互动,也会成为电脑化空间的一部分。
电脑化空间的出现,使人类的时空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唯一真正的边疆
物理空间曾经对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往的人们终其一生,活动的区域可能不会超过居所附近步行可及的范围后来,火车、汽车、轮船和飞机带来了人的流动性;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我们曾经幻想会有永无止境的“边疆”等待我们去开发,但当我们从太空中俯瞰过地球之后,这种幻想被击得粉碎。开发殖民地的时代已彻底成为过去。这一方面使得土地的价格飞涨,另一方面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依靠自身创造力来获得不断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财富和权力的聚集应该发生在另外的层面上。
现在,唯一可供我们的文明继续扩张的领土——就是电脑化空间。
电脑化空间并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但在其中发生的事情会带来“真实”的后果。以电话来推论,人们已同这样的空间相处了上百年。
20年中,这一空间拓展疆土的步伐异乎寻常地迅速。电话开始与计算机杂交繁育,巨大的电子蜘蛛把整个世界织成了一张网。尽管电脑化空间仍然虚无缥缈,但却开始具有某种奇怪的“实感”。
现在,已有无数人在电脑化空间里开创事业。人们在那里相遇甚至相爱,建立自己的社区,聊天,说长道短,筹划事情,互致信件,交换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姑且不论这些数据合法还是非法。
例如,在Internet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用电脑收发电子邮件,到银行存取款,调阅图书馆的藏书和当天的报纸,参加国际会议,看电影和听音乐,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平时在现实空间环境里的工作、学习、娱乐,在电脑化空间里都可以做到。对于许多Internet的忠实用户来说,电脑化空间一点也不比现实空间更加虚幻,或者说,电脑化空间就是现实空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原计划用2000万美元修建新的图书馆大楼,经过比较,改用了一套电脑装置,把计划中的图书馆变成了一个用电脑网络访问的电脑图书馆。在此,电脑的虚幻空间打败了实体的建筑空间。
这种事例今后会越来越多:非物质的、无固定场所的虚拟空间将替代、或部分替代现有的物质实体空间。有人描述说,将会出现许多虚拟的商场、银行、图书馆、美术馆、大学,等等。它们的形象就是电脑屏幕窗口里的一个个设计精美的小小图标,你用鼠标轻轻一点,就进入到那虚拟的迷宫般的电脑化空间。城市的概念也将发生改变,实体城市以外,还将有虚拟城市;交通网络被形象高速公路所取代,交通法规变为电脑软件使用规范,公共场所成为虚拟的电子广场。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可以用光速访问政府某首脑,去美术馆查看印象派著名画家的不知名的作品,或与朋友聊天和游戏,等等。
到那时,所谓的信息时代的建筑和城市将会出现,而实体建筑和城市形象也将大大改变。城市不再有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和种类,现在林立的办公楼、商场、邮局、银行等多种建筑将会变得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一组组的居住小区,每一个小区都有和全球通信系统相联系的网络:家居的外形可能十分简洁,而内部则布满了各种敏感元件、电子插座开关等;电视、音响、电话等家用电器都由一台隐藏在墙壁里的电脑所取代;唱片、磁带、报纸将在物质上消亡,转而通过信息网络来发行;人们很少需要出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坐在自己家中办公、上课、读报、看电影,或上虚拟商场购物、上虚拟饭馆点菜等等。当然买的和吃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非电子商品和虚拟的京酱肉丝。
真与假的界限
这听起来当然足够刺激。有人说,由于真实的三维空间(3一Dspace)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类的双眼只对电脑屏幕这样的二维虚拟空间感兴趣。神秘的虚拟空间已经堪称新奇了,但它的钟情者们却仍嫌不够:他们期望把这个人造环境变得更真实。这就是3一D电脑化:三维技术正在向Internet走来。
即使技术的迅速变迁已使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三维技术仍可以说是一个“量子跃迁”(aquantumleap)。不错,由于有了易于使用的浏览器,在环球网上航行已非难事;不错,环球网正变得日益丰富多彩,曾经枯燥的文字世界里现在已充满了图表、声音和图像。尽管如此,到你想去的地方仍需打出一长串难解其意的字符,例如http://www.sgi.com/index-TOC.html之类。但这很快就会改变。一种叫做虚拟现实模式语言(VRML,VirtualRealityModelingLanguage)的软件技术正在把虚拟空间变为三维空间。
许多公司都在尝试这方面的工作,领头羊是硅谷图形公司。它在1995年推出了一种名为WebSpace的3一D工具,可以从网上免费得到。位于旧金山的协同实验室公司总裁丹·梅普斯说:“在过去,3一D总被看作非常专业化、开支巨大的事物,就如同来自中国的名贵香料一样。这种日子已经飞逝而去了。”他进一步说:“我们认为3一D只不过是把信息从某个头脑传递到其他头脑中的高品质的方法。”
这就是为何3一D电脑化如此重要的原因。大脑像海绵一样吸收三维的信息:我们生而如此。意大利的画家早在15世纪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画中加入了透视,这得益于佛罗伦萨的建筑师弗利波·布鲁内莱斯基的几何洞察力。今天,电脑使走进这种透视图像并东张西望成为可能——比如说,在一个虚拟长廊中四处游荡,接着回头望一下你进来的路。
假使你想从一家虚拟商场里购买东西,你可以把商品拿起来仔细端详,并把它转来转去以看到它的每一个面。或者,假使你购买了一张足球比赛的门票,通常你希望前面没有柱子之类的障碍物挡住你。有了3一D工具,你可以提前检查,可以进入虚幻赛场里坐到你的位子上体会一番。
1995年,人们首次在环球网上建立了满是3—D物体的“房间”,而不是页面——这终于给电脑空间加上了广阔感。硅谷图形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爱德华·麦克拉肯(EdwardMcGracken)说:“总有一天,所有的电脑都将成为进入三维空间的窗口。”
人们在热烈拥抱3一D之时,也应明白它的局限所在。无论电脑模拟系统看上去多么逼真,它也不可能同现实一模一样。有个恰当的例子: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在深入调查1992年以色列航空公司747飞机撞人荷兰低收入居住区、导致43人死亡的空难事故时,发现他们的有限因素分析压力模拟系统不够详尽,忽视了将发动机固定在机翼上的“保险钉”设计中的几处薄弱环节。随着一处保险钉的脱落,飞机开始了它致命的俯冲。相同的模拟缺陷导致1991年挪威海湾的一个巨大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
传统的思维会因此得出结论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但现代技术的膜拜者们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眼中,真与假的界限正在消失。在这一点上,曹雪芹老先生倒是早有卓识: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种前景也许使你激动,也许使你倍感恐惧。不管怎样,电脑化空间都会影响你的生活空间。 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