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辩的人事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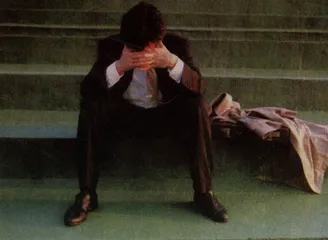
以稍远一点的距离观照身边的人和事往往能得出投入其中所不愿接受的看法,这种所谓的距离不是时空距离,而是指心理距离,不激动也别着急上火,在这种观照中,一时一地的小事会显得不那么小也不一定拘泥于一时一地了。
防蚊门
夏天来了,蚊子也来了。为了挡住蚊子我们家准备安一道“防盗门”。用防盗门防蚊子好像有点小题大做,或者有点文不对题,但实情如此。我们住的那个楼有点怪,每一单元的每一层有4户,上得楼来,左右两边分别有深入两米多的小过道,过道尽头是两扇紧挨着的门。这两米多的小过道又暗又背风,是个藏蚊子的地方,每次开门出门都能放进一批蚊子。所以,应该把蚊子挡在小过道之外。“防蚊门”也就应该安装在过道口。可一个过道里是两家,这就得跟邻居商量。其实这是一个“共荣”的方法,一个门服务于两家,多好。可是,当我把这个好主意跟人家商量时,我得到的印象使我莫名其妙,因为邻居满脸写着的是莫名其妙。我被婉言拒绝后真的有点生气。等到把这件事当成个事儿,不一定与我有关的事儿,讲给别人听,并把它当个题解的时候,就与之有了距离,就不生气了。
虽然我们隔壁而居,共用一个小过道,共用一个楼门,一个楼梯,远而及之,共用一个小花园,共用街道,共同城市的各种设施,但是远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公共意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仅靠非常疏旷的规则维系,在这些大规则不能覆盖的区域人们就尽可能不发生关系,如果有一方非常突兀地要与另一方有点关系,这关系就显得缺乏根据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像我与我的邻居。
我写过一篇讲公共空间的文章,当时看了很多也听了很多“盗用”公共空间的事例。对比起来,我有一点不解,无数人容忍别人在他必经之路随地吐痰,只要别吐在他家门之内;容忍“夜半歌声”搅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视之为生活的常态,但是却不能接受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这里的逻辑也许是,既然是陌生人就是没关系的人,要是一方要与另一方有关系,不是侵犯人,就是有求于人,不然瞎搭个什么。所以,在陌生人面前,要么是警惕的目光,要么是怜悯的神情。
既然如此,我再次找邻居商量时,摆出一幅可怜相,说出的理由都往自私自利那边靠,说我们家人多,出出进进地带进屋里的蚊子太多,说我们家的小孩儿被咬得满脸大红包,痒得乱哭乱叫,叫得人心烦,然后,求他行个方便允许我们在过道口安个门,麻烦他每次回家得多开一道门,当然,是我们家“独资”,哪能让人家出钱呢?诸如此类。这次,他听懂了,答应了。
报答
就在我琢磨这件事情时,电视里讲述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丹东市某派出所的片警小温,片警作了很多年,和他所辖的那个社区的居民相处得鱼水一般,是个优秀的警察。他所在的分局就把他提为警长派到另一个派出所。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原来他管的那个社区不答应了,一群居民到分局“上访”,要求分局收回调令,让他们的小温回到他们的社区。有一位老太太哭着跪在分局领导脚下,说:“小温走了,我就活不了了。”还有人给小温写信,请求他回来,别去当那个警长。最后的镜头是小温又回到了这个社区,居民们欢喜得合不拢嘴。
报道者和分局领导的口径是一致的,一个人为社会做了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会加倍地报答给他的。
这里的报答倒更像是“赖上他”了。既然“帮人帮到底”是义举,那么你怎么能干着半截就走了?怎么能还没“帮到底”就去当警长呢?怎么能置这么多信赖你的人的后半辈子死活而不顾呢?
报答在这里是不是有点矫情?
这是与我安门的故事完全不同的关系。我的故事是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小温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充满情义的,有眼泪有欢笑,有割舍不下,有义无反顾,但从中也能读出一种与隔绝同样令人不安的关系。
这位片警为这个社区内的居民服务几乎完全放弃了个人生活的时间。在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中,人是否有义务放弃私人生活?令人不安的是,那些热爱他的居民们没有怀疑到这一点。事实上,当社会呼唤一种“善意”时,常常把善意推得过于深远,把它推广为无私。一方面以莫名其妙的目光看待普通的互利的善意,另一方面又要求着一种宗教性的牺牲精神。在以被宗教化的善意为基础的关系中,人和人之间是友爱的、亲密的,不允许有间隔的,不允许有个人化的生活。他人的生活就不是在公共意义上共有,而是把公共生活彻底地拉进私人生活中。这岂不是既没有了公共空间,也丧失了私人生活,混混沌沌成了一个大家庭。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以家族为本的传统所致吧。
然而,大家族的生活不是在20年代就已经被质疑,被否定过了吗?并且,现代城市的运作方式所导致的生活场景中,被提出和强调的更应该是与之相符合的公共空间的建立和私密空间的维护,是公共规则的约定和个体生活的健全,是协作和自立。
把公共生活中相关的人拉进一个大家庭像是穿着莲花底的鞋蹦的,虽然看起来可能有点儿俏丽,但是这不利于蹦也有害于鞋。
既便是在一个真正的血缘家庭里,是不是家庭成员之间就应该是没有间隙的?
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节目报导过一则家庭“纠纷”。70老妪有5个子女却无人照管,要求法律援助。当律师前往找到了她的5个子女后,又是另一面的哭诉。子女们一方是因为怕这位母亲,不敢与之相处。因为从他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常常让他们感到害怕,动辄发火,并且他们都不明原因。稍长的两位子女在小时候被母亲责令去捡破烂,每天每人必须交给她5毛钱,如捡不到这个数,就不给饭吃。他们成年以后,老母依然如此,以至于他们渐渐地干脆不去母亲那里。几个人曾凑钱为她请过一个保姆,后又被她赶走了。
早有古训“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里的是非缠结难辩,既然清官都难断,那就不去断它。抽身出来一想,清官之所以难断那一定是所依据的准则不适于裁断这些事,或者家务事之所以如此难断,那一定是生活依据的准则撑不起一个家庭。
“社会经纬”中的老母与子女双方的哭诉似各有各的理。他们的确是一家人,一家之间产生了距离就不能让人忍受了。子女对长辈的孝道以怎样一种方式体现才算是恰当的,又是一个常谈的话题。如果子女把年老的父母送进养老院,常被以为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虽然有些开明的父母自愿去养老院,子女通常也心怀愧疚,多感不安。所以有另一种赡养老人的方法,就是为其请一保姆,代行照料家常之事,这样可以使老人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双方都显得心安理得了一点儿。但是同样也有刚才提到的那位老母亲,不要保姆。像许多老人一样,她要的是儿女常在身边,要没有间隔的亲情关系。这样的要求通常是以报答养育之恩为借口的。而养育的过程真的是一方向另一方施恩的过程吗?把养育视为施恩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我喜欢把发生在人中间的自然之事放低到一个自然的层次来看待,自然之中,无论老虎狮子类的大型高级动物,还是小虫小鸟类的低等动物,大概没有视养育为恩情的。养育子女是养育者自己的事情,此事虽必然地有一个养育对象参与,但这不是那对象的事。并且,养育和被养育本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怎么可能在几十年后以同样的格式再现,并且是以角色对换的方式。
反过来,虽然心理学家断言,不良的家庭氛围会影响儿童乃至成年人的心理,但是,子女是否有权让父母成为一个绝对善于控制情绪的人,所有属于个人的悲情与欢乐都放在子女心理需要之下呢?
当我听着“社会经纬”中老母与子女各执一辞的哭诉理由时,我想,她们双方是否都有越权的倾向?把对父母子女的要求扩大为对一个个人的要求,这是我们传统中对角色要求的强化与今天生活之间出现了差距的一个现象。
3种故事,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是个体人,任何人都在各种关系中与他人相关。既要维护独立性,就要建立一种关系中的恰当距离是每个人面临的自我设计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