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4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黄建初 邵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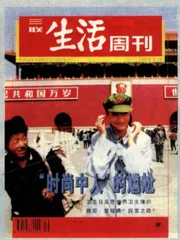
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中国的时尚与巴黎的、米兰的时尚的差距?与巴黎、米兰同步或以民族主义排斥巴黎、米兰,恐怕都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
北京 黄建初
数字化生存质疑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本人是一个有九年软件编程经历的程序员,看过尼葛洛庞帝(以下简称尼)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后,总觉得有许多话不吐不快。看了贵刊对尼的专访后,便想借贵刊一角对尼和他的数字化生存提出一些质疑。
《数字化生存》开章明义就褒“比特”贬“原子”。可是作为一个程序员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知道:“计算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尼把比特吹成了近乎万能的东西,却不知现在世界上所有计算机的比特存贮能力、存不下一个原子的信息。单是一个原子的直径就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亿亿亿亿亿位,直到无穷。更不要说原子无穷无尽的运动规律。有限的比特永远无法表现无限的现实。不要小看比特在小数点后十几位之外对现实的忽略。浑沌学正是从这一细微之处向牛顿经典力学发起了挑战。“北京的蝴蝶搧搧翅膀,纽约就会下雨。”这是浑沌学最著名的蝴蝶定理,它反映了微观细小的变化,会引起宏观事物的重大变化和转折。我们是生存在“决定”世界,还是生存在“概率”世界?这一问题重新提到了人类的面前。数字只是现实的抽象,决不是现实本身。计算机作为“决定论”的产物,在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里,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它不可能是万能的。
尼的前言就是“一本书的悖论”,既然数字化生存,“为什么还要用古板的老办法出书”,“还要把《数字化生存》作为原子而不是比特发行呢?”尼将其归结为计算机还不够普及,电脑界面还没有发展到“即便蜷缩在床上也能使用的地步。”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本质上讲:信息的权威性与信息发布的成本成正比。在现代社会,原子的成本高于比特,所以尼必须以原子形态增加其论点的权威性种说服力。在人类文明初期,信息的发布与获得成本都很高,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并反过来增强着这种特权。现代社会获得成本已大为降低,读书已成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成为通向仕途、获得特权的手段。现代社会信息的发布者仍然只是少数人,少数受过专业训练,受职业道德约束的人才有权发布信息,这并不是特权,只是为了维护信息的权威性,或称信息的内在价值。
尼在书中给我们展现的未来信息世界是“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赋予每个人制造比特信息的权力,“50年后,大多数人都会同比特打交道,也许只有5%的人与原子打交道。”但是由谁来提供这些比特?尼没有明确回答。在“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一章中,尼认为:“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无疑尼想说明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尼在论述电视时谈到电视的节目内容比电视画面质量更重要,否则“空有57个频道,却毫无内容”将是一个笑话。但是尼却没有想象一下:网络中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接近一比一时,网络信息的内容和街谈巷议的内容还有什么区别?
不错,网络还可以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为所有人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机会,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在“听”;但是说些什么?又能听到什么?只有不知道。就像过去村口的大槐树,能把全村闲杂人等聚拢在一起,山南海北,漫无目的的闲聊。50年后,网络这棵地球村的信息之树想必会无比粗壮。地球35%面积的陆地被树干全部占满。海底光缆就像树根、深入地球另外70%的海岸。树冠覆盖了整个电离层,树梢直触到月球。地球村的全体村民都可以在树下说自己想说的,却不知道有谁想听,想听的却被亿万个声音所淹没。计算机界面也许会像尼想象的那样,一个眼神就能联络到你想找的人。但是面对几十亿的村民,你却不知道自己想要找谁。也许你想将一张告示贴到树干这个“公告栏”上。将自己介绍给感兴趣的人。这时你却发现树干上已贴满了几十亿张类似的告示。电子公告栏的泛滥使其已沦落成路边电线杆上的招贴。这些招贴与书刊和电视广告的区别就是发布成本。信息化开始的时候,比特能带来金钱、信息化完成以后,凡是能比特化的就没有前途。就像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流水线产品贬值一样。
信息化的确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决定着我们的生存。就像电视机出现之前,有的人晚上是到邻居家串门聊一聊张家长李家短;电视发明之后,这些人晚上改在家里,通过电视肥皂剧,看着遥远某地摄影棚中虚构的张家长李家短。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怎样使用它。
要想隐藏起一片树叶,最好是将它藏到森林里去。在浩瀚的网络森林中,你如何能找到你所需的比特树叶?尼引入了“关于比特的比特”的概念。“这种比特会告诉你关于其他比特的事情。”它通常是一种信息标题。”但是由谁来给这些信息贴上标签?谁来保证标签与内容相符?也许那时你想在网络中找一本包括神,皇权、性、神秘、悬念等等内容的小说,你一口气输入了一百多字节关于比特的比特,得到的却是:“上帝啊!皇后怀孕了,这是谁干的?”这三十几个字节的著名微型小说。也许那时已经发明了一种眼镜,能通过瞳孔的扩张分析人对事物感兴趣的程度,能通过眼球的转动分析出画面中人感兴趣的区域。可这也帮不上什么忙,这种设备没有心灵感应能力,你必须对它进行训练,且不说你如何找到训练素材。也许你戴着这种眼镜看了若干小时战争影片的血腥与残暴,它向你推荐的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爱因斯坦如果生活在比特时代,谁来证明他相对论的正确性?也许那些载有相对论的比特上,还需要若干著名物理学家的电子签名来证明其权威性。但是谁又能证明这些物理学家有资格裁决爱因斯坦的理论呢?我们是跨越原子与比特两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初等教育,包括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来自原子世界,那比特的一代呢?那些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呢?在纷杂的比特世界里哪些信息是正确的,有用的呢?他们依据什么判断呢?也许他们的计算机是“老练的英国管家”,是“值得信赖的数字化亲戚”,会为他们做出必要的决定。但是这些“管家”或“亲戚”又依据什么做出决定呢?知识又依据什么更新呢?
后信息时代是个“信息垃圾”满天飞的时代,而对信息爆炸,人类需要的是更多的判断能力。信息不代表知识,更不代表正确的知识。这里没有用“知识爆炸”这个词,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并没有“爆炸”,仍然是按数学级数缓慢增长。只有知识的载体——信息在呈几何级数爆炸。知识包括“知”和“识”两个方面,《数字化生存》只能让你更多地“知”,却不能让你“识”。尼总爱引用米切尔·瑞斯尼克的礼堂鼓掌研究案例。但是这个研究案例只能说明:信息的交流可以使人趋同。但趋同并不等于正确。
尼鼓吹的另一点就是《我的日报》和“黄金时段就是我的时段”。数字化生存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自由选择接收信息。且不说这种兴趣爱好和需要是怎样形成的,单是这种选择就很有盲目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原子世界,随时随地都有事情发生,有的影响重大,有的则很无聊,有真有假,这都可以称为信息。传媒工作者对其收集整理,归纳提取以书刊电视形式供公众使用。以其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约束,保证了信息的真实和内在价值。可有些人不读书,不看报却总喜欢自己跳进网络这个信息垃圾堆中寻找。无论找到什么都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只因为是自己找到的。看到蚂蚁打架,也像发现了新大陆。
尼是一个优秀的比特推销员,《数字化生存》是一本优秀的传销手册。“奔向临界点”一章,举了个例子:“第一天挣一分钱,此后每天挣的钱都比前一天增加一倍,最后能挣多少钱?假如你以新年的第一天起开始实施这个美妙的挣钱方案,到了1月份的最后一天,你在这一天挣的钱会超过1000万元。”这是老鼠会传销时必备的所谓“市场倍增理论”。尼用它来形容电脑和数字通讯的发展。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尼也知道,他只能用:“最后3天的意义非比寻常。”“假如1月短少了于3天,那么到了月底的那一天,你只能挣到130万元。”其实根本不存在非比寻常的最后3天。任何新生事物,开始都有一个指数增长的成长期,然后是稳定增长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就像投硬币,你可能让它连续10次正面向上,但你决没可能让它连续31次正面向上。它的概率大约是十亿分之一。不但最后3天不存在,能维持头10天都不容易。电脑和数字通讯的发展并不是像他说的正奔向最后3天的临界点,而是正从指数增长的成长期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成熟期。所谓倍增理论,只是世纪末人类浮躁、肤浅一面的表现。
如果说尼是“数字革命的传教士”,这里有了印地安人关于白人传教士的寓言:“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有土地,他们手里有圣经。后来,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如果有一天人类拥有了比特,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原子,计算代替了思考,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西方这种对技术的崇拜,就像一种新兴的拜物教。著名科幻小说《最后的解决》的末尾这样写道:最后一台巨型计算机说道:“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计算机不是万能的上帝,我不信上帝,更不信计算机。
(北京 邵昌平) 数字化生存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