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3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方志安 刘华 陶伟 杨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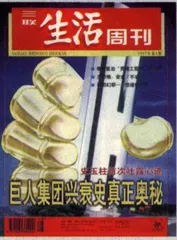
巨人集团的兴衰其实是中国民营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引人深思的是,在我看来,“巨人”这样的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家长”统治的单位,家长意志决定了“巨人”命运,民营国营似乎无大差别。
北京 方志安
数量概念还是质量概念
编辑先生:
向你们反映一点我的心情。眼下我所居住的北京中关村正在拓展马路,从北京图书馆到当代商城再到中关村,大变样儿了。
吊车架起来,推土机开进来,工棚搭起来,新沟白线画起来……好不覆地翻天。当然,人行道的路砖被搬走了,树砍了,花没了,草没了……
这场面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违章”也不是“滥砍”。据消息,“改造两年前就开始酝酿了”,属市政府1997年为市民办的60件实事中有关市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建设工程的“第一件”,是今年市政建设的“重点”。
“牵动人心的白颐路改造工程终于开始了”,媒介以急不可待夹道欢呼的姿态加入到建设的“热流”中来。北京一家颇有市场的报纸把一系列调访数据公诸于众——“64.1%的商家认为改建对中关村的发展大有好处;36.4%表示即使施工影响生意也希望尽快予以改造”,最后该报道作者“有话要说”了,“从经销商的态度看,绝大多数对此表达了迫切的希望……白颐路改造可说是众望所归。”
笔者这里有一点疑问:这个“绝大多数”是谁?如果商家“深明大义”是因为施工带来的营销损失完全可以为改建后的经济繁荣所抵偿,那那些没有被列入采访调查之列的居民老百姓呢?如果对“繁荣兴盛的明天”的预期可以构成“砍伐乔木6000多棵,灌木1500余棵,拆迁1万多平米”的充足理由,那附近居民吃灰吃土,“听机器轰鸣,任白日炙烤”的理由是什么?
这篇报道发表在“电脑乐园”栏目里。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白颐路是出入中关村的“大动脉”,电脑又被告知是与吃饭穿衣睡觉平起平坐的事儿,关乎生活质量,所以是“大局”。
对“大局”吹毛求疵被认为是“小青年”的事儿,我不想被认为“不成熟”,我只谈谈最近一次经过白颐路——我大学4年老邻居——的所见:
觉得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树没了。推土机。吊车。用纱巾蒙住脸走路的姑娘。烟摊没了。和路雪的车子哪去了?民工在啃馒头。慌了。风来了。
大学4年也无甚可吹。先是“双安”,后是“当代”,每天晚上“在机器的轰鸣工地的灯光”中入睡,不像四十几岁的校友有“东门菜地西门水田”可堪回首。
对发展,我可没什么情绪。但我要引用海因里希·奥特的一个质疑: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该是个数量概念,还是质量概念?
对我白颐路沿线人大、北大的诸位兄弟姐妹,我引海德格尔的名言安慰你:我们不可能“克服”,但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将“经受”。
中国人民大学 刘华
无法迁移的户口
编辑同志:
我国《婚姻法》规定,男子22岁、女子20岁可以结婚。然而,各地计划生育部门出于自身需要,又相应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补充规定加以限制。以北京市城区为例,今年年初,一对新婚夫妇按《婚姻法》有关规定登记结婚之后,家住东城区的女方在当地派出所办理了把户口迁出到位于西城区的男方家中的手续,却在西城某号称是全国最大的派出所的户籍办公室里见到这样一则《入户通知》:“根据区政府指示,15至49岁的女同志先到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具育龄妇女迁入证明。”并详细告知了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地点及联系电话,不可谓为群众想得不周到。然而,当这对新婚夫妇到指定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迁入证明时,却被计生办的办事人员挡了驾:“这个女的怎么刚刚22岁就结了婚了?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女的要到23岁半才接收呢!到了之后,签订生育规划,双方单位盖章,再来我们这儿办!”这对新婚夫妇向她解释:“您要不给开证明到派出所就上不了户口,而女方已经把户口给迁出来了。”女办事员回答得更干脆:“再迁回去,够岁数再来!”
万般无奈,女方只好到东城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迁回来。但是,麻烦事又来了,管片儿民警说:“人已经迁出去了,要想迁回来可以,先到接收地派出所落一下户,再办个迁出手续,我才能让你入户。否则,没有手续,我也无法给你迁回来!”
于是,两人又到男方所在地的派出所跟户籍警商量:“咱们办事处说女方不够岁数,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能迁过来,所以不给开迁入证明,让先迁回原址。但是,原地派出所又要求咱们这里先履行一下接受手续,然后再迁回去,人家才接收呢。因此,您能不能把户口给空落一下,再盖个迁出章?”男方住地的女户籍警回答得也很干脆:“我要是能让你落户,何必再让你迁出去呢?你们既然领了结婚证,《婚姻法》都承认,她凭什么不给你开证明呀?你去找计生办领导去!”
两人只好再次来到男方户籍的计生办,拿着女方的迁出证明要求办理迁入证明。这回换了一位小姐接待,态度也比上次好得多:“有小孩吗?……没有就更麻烦了,特别是对你们这些结婚迁入的。咱们这儿要求,必须得先办生育规划才允许入户,你得先到女方档案所在地的计生办办理生育规划,拿着规划书我们才能给你办理。”没想到,女方所在的计生办回答得也如出一辙:“不够23岁半我们不给办生育规划!”这对夫妇提出:“我们并不想马上要孩子,您能不能开个两年以后的规划?我们签个协议也行。”对方的回答不容置疑:“我们从不签什么协议!你到岁数再来吧!”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按照计生办的规定,如果他们选择不要孩子,自然就没有什么生育规划,看来这户口岂不要终生没有办法迁移了?退一步说,女方到接收地所在的计生办来当场办理生育规划,难道就不可以了吗?形式主义害死人!再说,《婚姻法》并未规定要等到到了多少年龄才可以生孩子,难道这不是变相制定地方土政策给群众办事设置难关吗?
看来,我们的办事人员有必要学习一下小平同志“出来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做点事情”的思想了,只要心里想着为群众做事,很多互相扯皮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北京西单 陶伟
我也是“学者”!?
编辑先生:
新年刚过,我就接到某省社科院科教兴国丛书编委会寄来的信,打开一看,是《当代中国学者大辞典》入选通知。通知说:“经有关方面推荐,编委会审核,认为你符合入选条件,拟将您的辞条选编入书。”而且郑重声明:“拒收一切不合理费用。”
给我第一次戴上“学者”的桂冠,却未引起我些许的兴奋。回到家里,我给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伴说了此事。老伴说:“啥叫学者?我不懂。你索性把信念给我听。”我把信念了一遍,老伴说她还是没有弄明白。我成了“学者”,却一下子解释不清什么叫“学者”。于是,我打开《辞海》,找出“学者”,释义有二:①求学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我给老伴读了第二条释义,老伴说:“我越听越糊涂了。”我知道她肯定是被“学术”和“造诣”两词弄昏了头脑。于是,我又查“学术”一词,释义是有系统学问的人。“造诣”一词的释义是,学业所达到的程度。这回我不念辞条释义,变成通俗的话解释说:“学者,就是有很多学问水平很高的人。”老伴说:“这回我算明白了七八成。你大学毕业,算有很多学问,写了很多文章,算高水平,那就够得上学者。反正人家不要咱的啥,不妨把情况写写寄给他们,印到书上,好让我和儿孙们荣耀荣耀。”我说:“现在不要钱,将来免不了买人家一本书。不买书,你拿什么在人面前荣耀呢?这书装帧精美,估计一本书至少要百把元。”老伴沉思片刻说:“荣耀还得花钱买,那我不想荣耀了。”
丛书编委会真有耐心,因3次来信我未复函,最近又第4次来信寄上入选通知。可见他们认定我是最具资格的“学者入选人”。他们根据什么确定我入选?通知说“经有关部门推荐”。我问本单位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领导,他们均不曾推荐。那又根据什么?我想,无非是根据他们偶然从身边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老实说,我写文章只求达到发表线,挣点稿酬就心满意足。功利动机太强,文章品位自然不高,当然谈不上学术上有发现、有造诣。我想,那些编“学者辞典”或“名人辞典”的先生,恐怕犯了同我一样的毛病,因为太功利,所以编不出好辞典来。
我写不出好文章,但我从不拔高自己,更不敢愚弄他人。编“学者辞典”或“名人辞典”的先生可不同,他们有拔高档次和愚弄他人的绝招。所有这些招数,都无法掩饰其卑琐的人格和低俗的眼光。下此评语的证据,一是不管入选的是论文还是辞条,一概不付作者稿酬,且作者负有购书或发行的职责;二是缺乏起码的责任心,对论文并不做严格汰选的工作,我所接到的四家“论文汇萃”入选通知,入选文章都是我上百文章中最次等的货色。
我有时突发奇想,如果有哪位先生编本《“老母鸡”辞典》,我倒愿意入选。因为我的确够得上标准的“老母鸡生存模式”,一年到头闲不住,整天在爬格子中企求觅几条小虫,找几粒米,好给儿孙们吃。
陕西渭南 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