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手术能否改变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蔡曙光)
1963年,约翰出生时是个小男孩,因做包皮环切手术失败,对阴茎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于是,当年,他的父母带他去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求助,按照那里专家的建议,他们同意由那里的外科大夫对孩子进行了阉割手术,然后从保留的细胞组织中制作了一种阴道,由此完成了对该孩子的变性手术。专家们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激素治疗将会完成他从一个男孩到一个女孩的转化过程。
从此,约翰改名为琼。这一变性手术被当时视为性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盛行的一种理论的活的证据。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在确定性角色方面,后天因素比先天因素更为重要。专家们说,儿童生下来是中性的,早期只要及时对他们进行调整,就能使这些孩子按人们的愿望而改变。这起性改变实例在医学和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中被广泛地引用。其结果,儿科专家们十分自信地劝导遇到同样情况的其他父母让其孩子也做变性手术,并把他们当作女孩来抚养。
然而,这些大夫及家长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一轰动医学界的变性手术完全是失败的。前不久,夏威夷大学的解剖学和生殖生物学的一名教授弥尔顿·戴蒙德与加拿大卫生部的一名精神病学家基思·西格蒙德森博士在《儿科和青少年医学档案》上发表研究报告表明,那位变性后名叫琼的小“女”孩根本没有真正适应后天为“她”设计的性角色,实际上,在70年代后期,琼就重新接受了手术变回到原先的约翰,现在他已建立起幸福家庭,是个有3个领养子女的父亲。
据戴蒙德和西格蒙德森声称,琼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受到的女孩“待遇”表示反感,还在“她”刚刚学步阶段,当母亲为“她”穿上女孩的衣服时,“她”总要想法将衣服脱去;总是愿意玩男孩们玩的玩具,与男孩子们在一起玩。上小学二年级时,“她”觉得自己做个男孩更合适些。但是,每当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夫时,大夫总是回答,这些感情完全是正常的,“她”只是个假小子。1994年和1995年,约翰在接受戴蒙德和西格蒙德森的采访时说,他当时以为自己是个畸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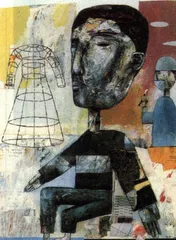
在学校,虽然同学们并不知道琼的手术经历,但“她”男孩似的长相和行为举止常常受到他们的取笑,在公共浴室,她尤为感到不自在。“她”常常坚持站着小便而弄脏了衣裤和坐便器。上初中后,为此女生们不让“她”进女厕所,逼“她”去男厕所。这时,琼觉得自己肯定是个男孩,但是,无论“她”怎么对大夫和精神病专家讲,他们都坚持要“她”按女性的方式行事。“她”终于打消了去说服他们的念头。如今,他回忆道,“你无法同这一群穿白大褂的大夫们争辩,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个毛孩子,他们的想法业已定型,根本不会听你说什么。”
1977年,14岁的琼面临两种抉择,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像男孩一样生活。面对“女儿”痛苦不堪的情景,父亲把他出生时做变性手术的真相告诉了他。约翰回忆时说,“我感到一切豁然开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我是谁。”父亲领着“她”另外找了别的大夫,做了复原手术,重新做了一个阴茎(尽管体积小一些,没有正常性器官的敏感性)。
手术之后,大夫劝他们全家搬到别的地区,另上一个学校,重新开始生活。但他们拒绝了大夫的建议,他们认为,人们总会发现真相的,还不如就留在原地把一切向人们如实相告。这一选择看来是正确的,约翰为同学们所接受。当他第一次约会时,他把自己的情况对女友说了,并对自己的阴茎能否有正常功能表示没有把握,她却把此事传到学校里去。然而,他原来的老同学们却坚定地站在他一边,拒绝听这个女孩不善意的饶舌。
这一事例一方面说明了一个男孩为选择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和表现出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过于自信的科学界也应引以为教训。戴蒙德和西格蒙德森说,遗憾的是,对于约翰最早拒绝使他女性化的情况没有作出跟踪研究报道,其结果,其他数十个男孩后来也像他一样做了这种不必要的阉割手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专家们辩解道,他们无法进行跟踪研究,因为这个家庭后来不再去找他们了。戴蒙德和西格蒙德森担心,像约翰一样的大多数手术变性的“女孩”一旦到了发育期也将会拒绝他们的女性身份。另一些专家则不以为然。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一位外科大夫兼精神病专家威廉·赖纳博士(他没有参与当初对约翰的变性手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案,他们最终会给我们答案的。” 西格变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