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梦想的实验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范海燕)
从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的一角,静静矗立着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一座典雅的白色建筑。走进这座建筑,恍若置身于奇妙的未来世界,呈现在眼前的是电子控制的各种声光设备、可穿戴在身上的电脑、或如幽灵般悬浮在空中的立体影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可遏止的创新活力,更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
这就是被称为“创造未来的实验室”的“媒体实验室”。
1976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向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发一种随机存取的多媒体系统的项目建议书,这一系统将使用户能够和已经去世的著名艺术家进行对话。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B·魏思纳(Jerome B.Wiesner)审阅了这份异想天开的建议。他非但没有把它视为书生的疯狂之举置之不理,反而答应提供帮助。
尼葛洛庞帝从小就醉心于艺术和数学,大学时代他原本主修建筑,进入研究所以后,却因为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而一头栽进了计算机科学的领域无法自拔。他开始在光碟上进行研究,魏思纳则敦促他开发出更成熟的语言,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艺术的研究。到1979年,经过讨论,决定筹建媒体实验室。
除尼葛洛庞帝外,媒体实验室与计算机科学界另外两位伟大的人物密不可分:一位是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大名鼎鼎的“人工智能之父”;另一位是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计算机教育的开拓者。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者们向广播电视、出版界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纽约时报》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es)。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他们中有计算机专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研究的领域横跨数字电视、全息成像、电脑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电脑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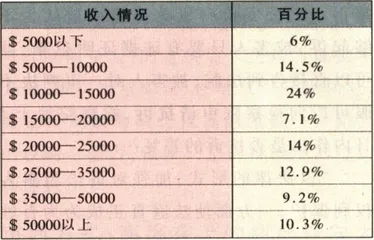
这群人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当时的电脑界仍然是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体系结构的天下,维系他们的并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他们都相信,随着电脑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群人的结合可谓占尽天时,因为当时,个人电脑已经诞生,用户界面开始受到重视,电信工业也解除了管制。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厂和电视台的拥有者和经营者都开始自问:未来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两位聪明的媒介巨擘,时代一华纳的史蒂夫·罗斯(Steve Ross)和迪克·门罗(Dick Munro)凭直觉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疯狂的新项目,对他们来说,用不着下多大的本钱。于是,媒体实验室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研究机构。
而多媒体科技和人性化界面的蓬勃发展,更令媒体实验室多年来融合艺术与工程的努力备受瞩目。今天,它已发展成为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赞助者遍布全球,共有75家,包括电脑、通信、娱乐公司,新闻媒体,甚至于政府机构,研究经费达上亿美元。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媒体实验室拒绝了10倍于上述基金的赞助。它被誉为当代探索计算机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的最权威的机构。
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
会思考的东西
媒体实验室走过了第一个辉煌的10年,第二个10年又将如何?
媒体实验室的宗旨是:不为当前技术所限,发明和创造性地利用新的媒体,以改善人类生活和满足个人需要。它利用超级计算机和新奇的人机交互设备进行实验,正是为了使之成为明日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东西。它的一个不那么隐讳的日程是,以崭新的洞见和突破性的应用来推动技术发明,打破工程僵局。
尼葛洛庞帝肯定地说,这一宗旨在下一个10年不会改变。如果说第一个10年与第二个10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指出,那将在于研究重点的改变。“前10年媒体实验室致力于将比特内容与其物理表现分开,造就出一个迅速崛起的数字媒介世界;后10年,比特要与原子重新联结。”80年代,内容重于物理表现;而在90年代,能力强大的比特呼唤着能力强大的原子。世界正经历由原子到比特、再到“比特和原子”(from atoms,to bits,to bits and atoms)的过程。
这样的总结也许很令人费解,但听尼葛洛庞帝从细处娓娓道来,则令人茅塞顿开。而且,你得承认,听尼氏描述未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设想一下,你出了车祸,完全失去知觉,医生们准备对你进行皮下注射。突然,针头上红光闪闪,显示你对针管中的药液过敏。医生立刻停下来,换上其他的药再试。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如果媒体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名为“会思考的东西”(Things That Think)的研究项目得以完成,这就不是天方夜谭。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实现“无所不在的计算”——计算机将不再只局限于一个笨重的金属盒中,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物体上,如门把手、鞋和注射针。
听起来有点发疯是吗?也许是这样的。尼葛洛庞帝说,对媒体实验室这样一个以创新为生命的机构来说,1/20甚至1/30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它既从成功、也从失败中学习,而且就是想要与众不同。媒体实验室常常关注一些让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会思考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这一项目横跨媒体实验室目前的3个主要研究领域:学习与常识、感性计算以及信息与娱乐。它的关键之处在于“使用日常事物进行交流”,尤其是那些“紧密包围人们”的东西,诸如衣服、家具、地毯、墙壁,等等。使没有联系的事情发生联系,这是“会思考的东西”面临的最大挑战。
例如,该项目正在探索把身体变成区域网的可能性——“将比特在你的脚和手腕之间传来传去,直到有一天,你的鞋将聪明到能够测量你的体重或血压的程度,数值则可以从手表上读出,”项目负责人迈克尔·霍利(Michael Hawley)指出。
另外一些奇怪的想法包括发明“智能书”和“智能鞋”。在进行研究时,媒体实验室的指导方针之一是:新技术至少应表现得同以前的技术一样良好,直到这时,它才是令人满意的。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传统书籍在各方面都优于电子书——它毋需启动,可以随意翻阅,阅读时也更轻松。媒体实验室正在试验新的显示技术,使电子书就像印刷出来的书一样。“你可以蜷缩在床上摆弄它,它可以像纸一样轻巧,像皮革一样味道丰富,如果那样使你觉得带劲的话。”而它优于传统书籍之处,是可以随时变化。一本智能书会由电子纸张构成,上有可施以变化的特殊“墨水”,书脊上则装有按键。你可以选择一个书名,按下按键,30秒后,打开书你看到的将是《李尔王》。读罢这部名剧,你可以合上书,再选一个书名,重新按下按键,这时你可以阅读最新一期的《连线》杂志。
智能鞋又如何呢?另一位项目负责人尼尔·葛森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解释说,两个穿着智能鞋的人可以通过握手交换数据。鞋里安装有微型计算机,握手不妨视作将两台计算机用调制解调器连接起来,身体的能量带动数据传输。智能鞋然后用手表作为数据的显示器。“忘掉环球网吧,我们有全身网(Person Wide Web)。”
为什么选中了鞋?因为人们每天都要穿鞋,鞋内有不少空间,并且,走路会提供最佳的动力源。还有一桩好处:把计算机穿在脚下很安全,你的个人比特会有很好的私密性,除非你决定与别人共享这些比特。
难怪“会思考的东西”得到了耐克公司的赞助。
在媒体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忙着将计算机嵌入各种物件中,以使这些物品更聪明,使我们的生活更容易。如果他们的梦想得以成真,我们的生存定义将被改写。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 电脑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