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大作对邓小平的逝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随之忆述战争年代,回顾年轻时的岁月与志愿,以至日后的种种发展,娓娓道来,饶有趣味。
池田:跟金庸先生进行第四次对谈的4日后(2月19日),建设中国重大发展基础的邓小平先生突然逝世,享年93岁。早前听闻近年来身体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不过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年寿终究会有时而尽。我也很理解中国人民此刻都很伤心悲哀。
金庸:邓小平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先生离我们而去,那确是无比重大的损失。幸好整个完善的方案已设计完成,适当而能干的营造师、工程人才也都已选定,主要工程已顺利进行了一段时期,以后继续根据方案施工就是了。施工者千万不可混乱,自相争吵,任意改动方案和蓝图,只要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个伟大的工程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设计及建造起来的,以前,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相信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金庸
回忆与邓小平的会见
池田:我曾跟邓小平先生见过两次面(于1974年12月、1975年4月),我不能忘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邓先生谈及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他说,“在中日之间有2千年以上的交流历史,不愉快的期间只有接近100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不单只是中国人民,也包括了日本人民。”他那不是以“中国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本位来看待问题,而是本着不管任何国家,也站在该国人民一边的人民立场这份中国的睿智来看事情,真令我叹赏不已。
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最后演说中呼吁“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被压迫的民族那一边!”我相信周、邓两者的心意是相通的。在第二次的见面中,交换了有关日中友好条约的意见。那时候,邓先生直率地说出“中日两国不应只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该要求霸权。”换言之,大力要求加进“反对霸权条款”是中国的立场。
在那数年之前,我在小说《人间革命》中曾主张:“日本应该与以中国为首的地球上所有国家缔结和平友好的条约。”两国人民都期待的友好条约的缔结,是我跟邓先生对话后的第三年才达成。金庸先生第一次跟邓小平先生见面是1981年7月的事吧。
金庸:对。我记得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希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池田:尤其是,邓先生曾问:“新闻界对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呢?”金庸先生直率地向他说:“希望中国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
相信这是发自担心“香港未来”的发言吧!所以为了消除大家对将来的不安才说:“不轻易改变政策。”是为了民众的将来,先生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先生也回说:“确是这样。”文豪与大政治家迸发火花的对话,正是一幅名画般的场面。金庸先生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关于《基本法》的制定,邓小平先生也给了不少的指示吧?
邓小平十分重视《基本法》
金庸:我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主要是指中国当时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不仅是指香港政策。邓先生对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十分重视。我们《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第一次到北京开会,邓先生就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接见全体委员,并和大家共同照了相。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原则,就是邓先生设计和制定的,这原则具体地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又根据这些原则而制定《基本法》。
可以说,香港即将实施的《基本法》,是邓小平先生一手亲自制定的,我们这些起草委员,只不过将之写成法律条文,再加上一些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等等补充条款而已。
池田:香港《基本法》这座大楼也是建于邓小平亲手巩固的基础上的吧!
然而,刚才谈到《中英联合声明》,两国间的谈判虽然花费颇多时间,但邓先生所提出的原则,意外地被英国全盘接受了。
金庸: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的确为期颇长,但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用在斟酌文件的字句、字眼等等方面。中国提出这样合情合理、顾全大局的各种原则,英国人听了不禁喜出望外,意想不到对方的提议居然比自己可能期望的还要好得多。
香港会像解放初的上海吗?
池田:英方最初是怎样想的呢?
金庸:他们想象,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管香港之后,当然会像对上海、天津、广州那样的治理,从北京派来“港督”和全部政府官吏,将香港的大小企业都收归国有,由政府管理,废除原有的全部英国法律,改换中国法律。法院、法官、律师等等司法制度全部改为中国式。宣布港币无效,改用人民币。英国人投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都归中国国家所有及经营,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居民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等都将受到限制。哪知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后,在香港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同时由本地居民自行选举而产生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即使交由英国去提议,英国也决计不敢提出这样高的要求。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主要的谈判是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
中国提议将这些原则列入《中英联合声明》,并不是中英双方谈判的结果,只不过将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地列入一项国际条约之中,好使香港人放心,也使全世界人士对香港的将来怀有信心。
池田:我明白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对于香港的将来也花过很大的气力。
如果没有邓小平……
金庸:对。若要评价邓先生对香港作过怎样的贡献,带给香港怎样的幸福的话,我们不是可以这样想吗?
如果中国没有了邓小平,没有他对香港的前途提出这许多设计,没有他以个人的威望、魄力和见识来加以充分推行,以至实现,那么到7月1日以后,香港将是怎样一个样子,完全是可以推想得到的。事实上,不用等到1997年7月1日,在此之前的几年,香港早就已经乱成一团糟,已不是一个可以正常运作、平安居住的国际性大都市了。
池田: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先生是如何期待香港回归这“一天”呢?他曾经希望“九七之后能到香港看看”,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刚才就香港与邓先生的关系已向您请教过了。我想就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中邓先生的存在与角色,再向您请教,您的看法如何?
金庸: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肯定不会如今天这样富强。1989年6月,我曾在《明报》上写过一篇社评:题目是《大家斗命长,仍盼邓能赢》。主要的意思是说,中共党内,仍有思想保守的人士,不赞成改革开放。只有邓先生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只要邓先生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反对派就不能为害国家。所以我热切盼望邓先生健康长寿。中国古语形容一位重要人物说他:“一身系天下安危。”当时所说的,其实就是中国(我看日本在战国时代也是这样,所谓“天下”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邓先生在过去20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
池田:这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知道的事,关于“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中国怎么办?香港怎么办?

池田大作
金庸: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曾譬喻他是一位“大旗手”,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带领中国前进。听说他不喜欢这个譬喻,说:“江青才自称大旗手。我不做大旗手。”我想,“大旗手”摇旗呐喊,带领人马冲锋陷阵,既不合统帅的身份,同时过于鲁莽急进,缺乏稳扎稳打、战则必胜的名将风度。“总设计师”的比喻就好得多,而且更加现代化,目标在建设而非破坏。
池田:确是如此。
金庸:那是事先精密构思和计算,画出整个大建筑的内外面貌、建构式样,规定了所用材料、施工程序和计划等等。设计完成之后,自己缜密检查修改,再和大家讨论,接受多方面意见,所有缺点和不安全的因素全部除去,直至尽善尽美。设计方案既定,就交给营造者去执行,总设计师则监督和检查工程进行的程序和规格、标准,而主要的营造者也是总设计师亲自指定推荐的。这一条路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池田:中国今后仍然继承这条路线的话,对香港也会有好的影响。
金庸:对。对香港的设计固然重要,但在全中国而言,仍只是一个小小地区,只要中国这座大厦建造得坚固完美,香港这个小房间也一定不会太差。
池田:您曾会见邓先生,而与他作了长谈,您长期关注世界及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您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请从这些观点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
金庸: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当年我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
战争使我站在民众一边
池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是一个不能与战争记忆分割的时代。

金庸
去年春天,您在创价大学演讲时,有位创大的学生向您提问:“金庸先生的‘站在民众一边’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您简要地作了以下回答:
“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成长的时代。战争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难的时代,我看到民众的苦难,因而就决心从此要与民众站在一起。”
——日本对亚洲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犯下了许多野蛮的行径,而数千年来,正是中国传给了日本诸般文化,受此恩惠的日本应将之视为“恩人之国”,然而,不谈“报恩”而还之以一犯再犯的罪行,真是罪不可逭。
金庸:在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期间,我就已知道日本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反对这场侵略战争。战后我数次旅行日本,曾会见好几位日本当年反对侵华战争、战后尽力对中国友好的社会领袖,例如:冈崎嘉平太先生,还有文化界的某些领袖人物,他们都是胸襟广阔、有远大见识的人物。
池田:我们日本人的心胸不够阔大吧!战后,日本没有对中国道歉,反而是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继续敌视中国。直至最后也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日本也有一份。然而,对于这样的国家,中国则抱着极大的宽容,说是:“犯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民众是无罪的。”
我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时,就听他说过:“中国没有要求战争赔偿。因为日本人民也同中国人民一样,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如果提出索赔的要求,却是同为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来偿还。”中国人民的这种高贵的心意,日本人做梦也不应该忘记!
金庸:我了解到,在日本当年以及今日的舆论气氛下,池田先生公开对当年的战争表示谴责和负疚,不但需要明湛的智慧、关怀全人类福祉的仁人之心,更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那真是所谓“大智、大仁、大勇”。中国古代的圣人孟子说:“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意思是说,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合乎正义、正理的,那么就算有成千成万的人反对我、攻击我,我仍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能身体力行去贯彻始终的,不就是池田先生吗?
池田:您过奖了,不敢当。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曾说过:“日本只有获得亚洲各国的信赖,才能称为和平之国。”以心交心,正是我要付诸行动的打算,若非如此,日本会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在那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也对先生的故乡(浙江)造成极大的破坏吧?
金庸:日本军队侵略我的故乡时,我那年是13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随着学校辗转各地,接受军队训练,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困苦。我的母亲因战时缺乏医药照料而逝世。战争对我的国家、人民以及自己的家庭作了极重大的破坏。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英文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得稳固,到了大学时代及大学毕业后才再补上去。
然而战争给了我有益的磨练。我此后一生从来不害怕吃苦,战争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
青年人应有更好的磨练方式
池田:确实令人感慨,这一切可说是人生的弹簧,金庸先生这样坚强的人格是在青年时代练就的,青年人有必要去经受磨练。
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接受军事训练是具有教育青年的效能和作用的,但结果却是这种教育不是让青年丧失生命就是强化了他们杀人的动机。况且,现代化战争已经远远超过人会从中领悟人生之精神食粮这样的立场,这才更加悲惨,是绝对不应允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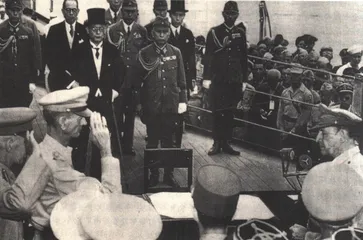
签署了投降书,并不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者低头悔过
以前,美国的哲学家威利·约翰曾倡议:为了更好地将人的斗争本性引导到优良的方面去,有必要创立非战争的其他“道德的等价之物”。何谓此“物”呢?譬如说,创设专事和平和建设的部队,“那些有钱人的少爷,如果让他们各自选择,有的去煤矿或铁矿,或者去铁路运输,有的去寒风劲吹的渔船队,或者洗碗涮碟子、洗濯衣物、擦窗子,或是被征用去建设道路和隧道、铸造工厂、汽船的轮机房或高层建筑的工地,娇生惯养的孩子气就会从他们身上消失,他们将带着更健全的感想和坚定的理想回到社会中去。”
金庸:这是很好的倡议。我十分了解池田先生您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尽力,创造向上的精神价值,致力于磨练人格。
池田:惭愧、惭愧。我曾多番强调,创价学会的各种“文化节”的意义也一样表现出这种意图,就是为青年们提供“更好地成长”的锻炼之园地。同时,“创价班”、“牙城会”、“白莲组”等培养青年的小组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为了教育青年,为了那些未经历过战争的世代,我想请先生谈谈战争在您心中留下的最深记忆是什么?也许那是一种痛苦的回忆,但还是请您谈谈。
金庸:战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空军投掷的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下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我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
另一次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在浙江衢州城上空投掷鼠疫的细菌疫苗。当时我在衢州中学上高中,在乡下上课,鼠疫在衢州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人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任其自死,七日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
池田:真是太沉痛的话题。旧日本军的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它所留下的伤痕仍然是余烬未灭,挥之难去啊!
金庸:当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同班有一个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钱出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义不容辞,黑夜中只得跟在担架后面,直到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和姜老师全身互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池田: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当然令人汗颜,但更令人感到可耻的是,许多日本人忘掉了这段历史!
我曾听说中国人在辱骂人时用的最重的名词是“忘八”。我想那也许是对忘掉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8个德行的人的贬义词,对这种“健忘”的行为是十分轻蔑的。换句话来说,日本人是健忘的吗?但是那些在有关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大言不惭的政治家却层出不穷。对于亚洲诸国的严厉批判的声音充耳不闻,对于自己的“问题发言”(指否定侵略战争的讲话)侮辱了亚洲人民也置之不理,怎样伤害了别人也毫不理解,当然连自己所表现的愚昧也不明白,这是许多人所指出的。“和平”,到头来意味着要与这种“健忘”战斗。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先生在德国投降四十周年时发表著名的演说中曾说:“对于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到头来现在也是瞎眼的人。”忘记过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和赎罪心情,也不能誓言和平。
日本人对于这种“历史的健忘症”必须彻底地予以纠正。若非如此,就不能被世界视为朋友。
军国主义教育与日本人的性格
金庸:对于战争中的经历,我也有一些问题向您请教。我知道先生的令尊于之吉先生是一位坚毅有责任感的长者,本来从事紫菜制造业。
池田:是啊!周围的人都叫他“固执的先生”,倒是很贴切啊。(笑)
金庸:战争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先生的4位兄长都被迫参加了战争,长兄喜一先生在缅甸阵亡,另外3个哥哥到战争结束才从中国回国。先生的父亲和兄长都强烈反对侵略战争。虽然日本是侵略者而中国遭受侵略,但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分别受到战争的重大损害。
池田:我的长兄当兵被派到中国去,他有一次回家时一副不满的样子无从发泄,他说:“日本太过分了!对中国人真是太狠毒了!”这句话我至今仍然萦怀难忘。

池田大作
金庸:战争期间先生年纪还小,不知是不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据说先生曾想投考海军航空学校,因父亲不许而未果。这是由于家境穷困呢,还是由于想做军人的英雄式感召?
池田:老实说应该是后者,适如您所说的,与我同时代的少年都是在军国主义教育中成长的。当时的日本教育,考虑的是怎样在孩子们的心中培植歪曲的人生观和思想,然后,又如何将更多的少年驱赶上战场去卖命。没有比错误的教育更可怕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金庸:这段时期中所受的正规教育一定不充分,后来先生到新泻钢铁厂做工,先生身体并不强壮,做钢铁工人一定感到吃力,但相信也是一项有益的锻炼,对先生今后人格的成长很有益处吧!
池田:战时是一个没有壮硕的身体就不行的时代,体弱就被视为“非国民”(不合格的国民),我也曾因自己体弱而自卑。但是,也因为以多病体弱之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获得难得的经验,特别是知道人间的温情、体贴和同情之心。
例如,在寒冬的日子里,有位上司对我说,不来这火堆边歇歇,说说话吗?我当然确实十分高兴,他是知道我的肺部不好而这样做的,那时与他交谈的话,他的样子,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他像鼓励自己的儿子一样对我说道:“年纪轻轻就踏入社会,就像打相扑的世界一样,不要焦急,而要沉着,那就好些。”那位厂长也是一位好人。每当我生病时就给我鼓励,送我去医务室,特地用人力车将我送到家中去。当时极少有人坐人力车(黄包车),因此旁边的人看到都感到十分惊奇。(笑) 金庸香港日本中国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