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自嘲咨询业上赶着 伤感着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王力是一民间谋士,1987年辞去记者工作,创恩波公关事务所。因成功策划“亚细亚商战”,被誉为“中国公关第一人”。在制造“亚都现象”之后,辞去北京公关学会副会长之职,告别公关业,转入咨询业,现任恩波智业顾问公司总裁。
王力的父亲为国民党将领,随傅作义起义。受教育于北京实验一小及师大附中,均为名校。文革期间,17岁进海淀区清洁队扫大街。1984年,创天坛旅游开发公司,又创北京第一支时装模特队,均败。此后,其自传称进入《经济时报》当记者,实为该报下属《中国花卉报》记者。
1987年9月,王力辞职下海,到工商局申办“公关事务所”的执照,被告知“没这个行当”。于是,他没事就往工商局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逮着机会就公关。一天,工商局官员顿悟:“你这行当就是拿嘴挣钱呀!”
最初,王力是从累年积攒的名片堆中,精选出10张含金量最高的,按图索骥发出自荐信,然后做梦:如果一家每月付50元顾问费,10家就是500元。不料信如石沉大海,梦想破碎。王力第一笔“公关业务”是帮人筹备会务,从选择会址到安排就餐再落实纪念品,认认真真交了差,所获50元。
1990年王力开始公关生涯的第一大课题——郑州亚细亚商城。他从商业文化入手,把“亚细亚”炒得红遍中国。但给“亚细亚”公关策划一年半,仅获得3万元咨询服务费,而且差旅费也在其内。不仅经营上大赔本,王力与“亚细亚”领导人恩断义绝,内幕双方秘而不宣。
此后,王力与“亚都”总裁何鲁敏合作,共造“亚都现象”,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创成名牌企业。历时2年与亚都结帐,何鲁敏问:“亚细亚给你多少钱?”王答:“3万”。何说:“我给你10倍。”
1993年夏季,王力转入咨询业,如履薄冰。1995年8月,他和公司人员全部扑在投资5亿的海南望海商城,耗时一年,拿出6万字的战略策划及实施细则,仅获利10万元。而且,王力被绑在望海商城的战车上,负责所制订战略的每一步实施,等于兼任相当一部分管理职能。按合同规定的利润分成比例,如果3年后达到利润目标,王力公司将分利1000万,达不到将白辛苦。行家评价:王力所为已使咨询策划变了味,成为管理公司。王力苦笑。

1979年,王力是天坛公园的花匠
时下,王力想办一所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的学校,他又想从咨询业告退?王力有苦不说。
王力是个大忙人,1月底他刚从海南风尘仆仆而归,便被本刊记者逮住。疲惫不堪的王力,一谈咨询业便大放悲鸣。
记者:王力先生,据我所知你也是靠“卖点子”起家的。但近两年,你在很多场合对“卖点子”大贬特贬,这是一种自我批判呢?还是针对咨询业的一种普遍误区呢?你如何评价“一个点子救活一个企业”的说法,是神效还是神话?
王力:我一开始说是公关策划,其实就跟后来的“卖点子”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切入点跟公关比较近,有些相关的点子。
我第一次“卖点子”挣钱是1987年。成都酒家是我第一个作品,那时候上海甲肝流行,北京没人上街吃东西。怎么办?全新的装修、全新的服务员、服务态度也好,可没人吃饭。针对这种消费者心理,我来了个“当众二次消毒”。非常简单,4个脸盆,把卫生防疫站指定的药水瓶搁那儿,来吃饭的,凡是对餐厅卫生不放心的,可以举手当众二次消毒。
就这么个点子,实际解决不少问题。肝炎来了,就是中央下一通知说肝炎走了,都没人听。只有让大家感觉到,咱们能治这肝炎了,就行了。
我不是说点子不好,因为我过去最早也是靠点子起的家。那时形势迎合了这事。但你要说点子是包治百病的药,那不可能。点子是药房里的药,感冒了,你买“感冒通”也没准管事。换句话说,真正得了病你得到医院,大夫给你把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一些东西,这是系统工程的事。
我觉得,前一阵子把点子说得太神了,神到“一个点子救活一个企业”。过去,我不敢说一个点子救活一个企业,只能说使这个企业活起来,活了一段,我只能做到这儿。
记者:我听说,你现在仍不时给人出些点子。那么,究竟如何客观评价“卖点子”?现如今,很多人热衷于“卖点子”。这是否意味市场需要这个“新行当”?“点子热”症结在哪?
王力:去年,一房地产开发商惨了点,我一句话让他卖出一幢别墅。它旁边有一跑马场,马没人骑,我就说你卖房搭上一匹马,顶多花500块钱;第二天见效,卖出一栋去。这也叫“策划”吗?
点子在市场上会生存下去,也还应该行。因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它是一些主意、想法包括小革新、小创造,后来社会化、商品化了。现在是讲究实效,媒介又说点子变钱快,所以很多人想走捷径。但说到点子职业化,我觉得还得有个过程。
那天,一个朋友讲点子就是主意的俗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合理化建议,都是过去咱熬药用的是砂锅,注重的是药的疗效。现在不管疗效,拿一玻璃烧杯煮这些药。让大家看这草根一开始是绿的啊,待会儿开了变成黄的啦,全炒的是这个。
所以,就出现那年点子大会,几百个卖点子的,折腾来折腾去,根本没效果。严格来说,点子是技术革新,应该归到技术专利、发明创造。如今没人往那儿归了,而且归到“尊重知识,知识也能卖钱”,鼓噪得太热闹了,弄得神乎其神。
整个咨询业,我认为是个提高素质的问题。我们做咨询告诫委托人不要拍着自己脑袋想问题。我们本身也不能拍着自己脑袋想问题呀。自从“卖点子”炒热后,好像冒出一拨高智商的人,超脱在众人之上。这些年“点子热”,到底热在点子的神奇上,还是“卖点子”的表现形式上?
记者:你自称,“亚细亚商战”是第一笔像模像样的公关策划。然而,虽然商战赢了,可你本人却输了本钱,砸了人缘,只赚了个吆喝。
王力:1989年,我很快转向了“亚细亚”,在企业发展的战略定位上做了一个尝试。因为亚细亚是一个新办单位,有了人马,有了阵营,只是向东向西的问题。我当时提出一个概念,商业评比当时只有两个,一个是营业额攀比,还一个是全国十大商场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亚细亚”当时只有5个党员,想得那个不可能。就在这时候商业部长胡平拿出一篇文章,提倡“商业文化”,我说先拿单项这个第一,用单项第一实现公关战略定位。
我是设计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只能用未来可能出现的事说服他们,建议他去做。当时“亚细亚”,哪能接受商业文化呀,问我的第一句话:“商业文化咋计算利润?”真他妈的一针见血。我那时看到门口挂着“党办”的牌子,就说“这屋怎么计算利润,商业文化就怎么计算利润。”
当时我先做市场调查,第一全国没有一家商场开展商业文化的,我也了解到全国商业有没有办报纸的,所以才决定以“商业文化”树立“亚细亚”的形象。

1984年,王力成立天坛旅游公司
“亚细亚”跟我谈合同时,开价2万。那时候我没标准,只知道要是还价4万,翻一番了,他们接受不了。我要是不还就没行市,所以和他们扯了一天,最后他们没想到我说出3万,成了。这3万还是分6次付完。做了18个月就这么点钱,肯定赔了。
记者:你在公关界摸爬滚打数载,好不容易弄了顶“公关第一人”的桂冠,为何轻易改弦易辙,撒手而去,此中隐衷是什么?
王力:公关本来是挺不错的事,后来被一些人弄得呀,一说公关不会喝酒不行,不会跳舞不行,我也很困惑。你说往下做吧,弄得什么事都得干,说不跟那些人搅一块吧,说你清高算便宜你了,说装大个算对得起你,骂你的话多了,都得听着。
我还撞上个问题,我后期接触很多企业,伤了一批记者。为什么?我知道每个企业周围都有一圈记者,而我把人家饭碗抢了,自然会挨骂。我先不知道这个,后来人家告诉我,这是记者圈的毛病。我一想,圈里圈外部不好惹,干脆转到咨询吧。
记者:现在咨询业是否跟当初公关界一样?现在咨询业究竟是市场问题,还是本身问题?
王力:1993年咨询业势头绝对非常好,很多企业觉得光靠自己的才智不足以创造财富了。而就在这个非常好的时候,又出现咨询业本身鱼龙混杂的状况,这是咨询业的悲哀。突然冒出一批超级天才,长着聪明绝顶的大脑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哪来那么多“心想事成”的事,我就烦心想事成,想当皇上的多了,想嫁皇上的也多了,有几个成的?整个唯心主义。

1988年,王力成立北京公关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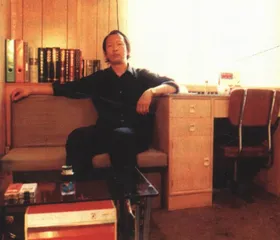
1989年,王力置了一间有些模样的办公室
我始终觉得这个咨询业,一个人或几个人救不了。那些小事人家找你咨询可以,真正策划比较大的事情,要靠层出不穷的思路,层出不穷的创意,一个人总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我感觉不是现在需求市场不足,而是咨询业自毁长城,什么人都搞咨询,动不动就是策划,搞得人烦了,分不出真假,挺好一个咨询市场被搞得乱七八糟。咨询业是明白人干的,现在越干越没劲。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进入专业咨询的可能性不大。房子怎么盖,葛洲坝怎么建,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一般都是干决策咨询,而决策咨询需要的是通才。
中国咨询业的市场和国外不大一样,委托人往往“无路可退时”才借外脑。国外事情还没成形,先找外脑咨询,然后决策。我们是无路可退时才找咨询。所以我说咨询业卖的是“马药”,死马当活马医的那种马药。治活了,这点钱花得值,治死了,这点钱花的也不糟蹋。这种情形的市场,干咨询的就惨了,委托人无路可退时找我们,我们往哪儿退?逼得我们只能在思路上与他们错开。有时甚至立场不变,脑袋歪过来也能看到前面。
现在的咨询市场表面上是总量问题,实际上是结构问题。好的咨询公司业务做不完,差的公司揽不到活儿。现在于咨询的90%都是上赶着,那种抢活的惨样让人伤感。现在包括广告公司也要搞一个客户部,不明白什么意思,反正肯定不是做业务的,可能是取悦客户的部门。
我觉得,中国咨询业的困境主要来自自身,不让别人拍脑袋而自己拍脑袋,而且只自己拍脑袋。我作为别人的外脑顾问并没有局限我个人的脑袋,我也有很多外脑。但作为咨询业务决策人,又不能把张三李四王五的意见摆在那儿,给委托人5个意见。我的功能就是把5个意见综合归纳,找出一个更可行更适合委托人的东西。
记者:外国人说,中国的咨询业是一座独木桥,只能在很窄的缝隙里求生存。但实际上,国内咨询业人士又奇招迭出,作为圈内人你感受如何?
王力:在国外有很多策划可以无所顾忌,只要委托人高兴,国情国力的问题不考虑,在中国你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往往把国情国力、法规政策放在第一位,超过这个我不干。比如,有一年上海搞了一个中国首届“济公杯”蟋蟀大赛。从策划角度上看搞这活动有新意。上海人斗蟋蟀有瘾,一晚上能把一千平方米的绿地踩平了,逮蟋蟀。上海园林局给建设部打报告说,你们要再不干预,公园里假山砸死了人,我们可不管。再说也得看看当时形势。“六四”刚过,紧接着亚运会,大家情绪激昂地跟着中央创业,弄这事绝对不符合国情。所以,下令取缔了吧。我当时讲,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麻将都行,什么时候见过老干部中心围一圈,看两蛐蛐斗着玩?这就是国情。
亚运会的时候,有一公司也干了件奇事,要出卖长城的碎石头。紧接着新闻媒介开始炒,炒了没几天,就出事了。第一,这碎石头从哪儿来的你说不清;第二,你带着别人去弄这事,别人找好石头去砸。这也是国情。
所以,凡是能出两个邪招就叫策划,这真是悲哀。
记者:所以说你对CI设计有一番怪论,可否谈谈。
王力:这一块,我历来跟一些人唱反调。我就经常讲这CI是个富贵病,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状况,才整点这玩意。就跟解放军进城,原来破军装,进了城才开始有标志,有制服。到今天,我没发现哪个企业是靠CI发迹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了,才开始精益求精,搞点CI的东西,整点CI效应。现在怎么穷人只靠这活着?
记者:有人口出妙言,咨询业是“捅窗户纸的行业”。你却大发奇谈,说咨询业是“下地狱的行业”。
王力:我想最简单的事可以这么讲,如果都是那“捅窗户纸的行业”,咨询业就活不下去了,成算命的了。我把我的方案给你看,那是窗户纸吗?铁壁铜墙啊。
我自己想创新,但不想过早说大话。中国咨询业要照目前这样发展,没有前途。整个行业衰了,我们不下地狱谁下?而且,人们会记着,这行业是在我们手里砸的,你说还有翻身之日吗?从另一角度说,咨询业在中国刚刚起步,等变成了一个产业被社会普遍承认,我也老了,甚至死了。 亚细亚公关行业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