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3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仁强 元丁 胡辛 王晓中 费隽 陈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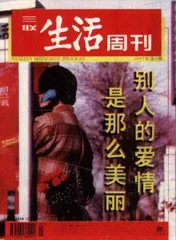
感谢贵刊向我们提供冬天里的温暖的爱情故事。爱情其实不仅是浪漫的代名词,更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财富。当平庸的日常生活使我们越来越疲惫时,我们更加渴望那种也许是奢侈的诗意。
北京 金仁强
这样退票吃亏的是谁?
编辑同志:
贵刊一直很关注我国铁路客运问题,今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售票制度改革是铁路走向复兴的关键,这确是切中肯綮之谈。
然而,最近铁道部对退票制度进行的修改却带来一些意见。新制度规定,退票时每10元票价核收5元钱的手续费,发车前6小时不再办理退票业务。据说,这次变更是为了打击票贩子,减少火车票额损失。
诚然,火车票长期以来都属于紧俏商品,尤其在春运高峰期更是如此。“物以稀为贵”,一些人借机囤积居奇,加价卖出,大发其财,有些不法分子甚至伪造火车票坑骗旅客,群众意见很大,也扰乱了铁路部门的客运工作。因此,采取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综合措施严厉打击票贩子,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打击票贩子的同时,也可能使老百姓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计划赶不上变化”,订了车票又临时变更行程的事情谁都可能碰上。过去退票时退票款的80%,开车前两小时不再退票的规定,群众也能理解和承受。问题是退票的有关规定应该以什么作为依据?。
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因为突发原因不能成行的旅客,只能退得一半的票款;而要是票贩子再以高于50%的价格收购退票,旅客把车票再卖给票贩子呢?对退票时间的限制同样也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铁路部门出台这些新规定,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但是不是会重视了一些社会现象,而忽视了另一些现象呢?我认为,对于一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制度,行政部门在制定规定时,应该过细地全面考虑一下老百性的利益,尽量比较周全地解决社会矛盾。
北京 元丁
闹心的音乐
编辑先生:
我对出租汽车司机一向没有好感。不是因为他们礼貌地把车停在你的身边,礼貌地问你去哪儿,当你回答去东四的时候,却礼貌地告诉你没油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把你当向导,从不清楚应该走哪条路,总爱就此征求你的高见;更不是因为他们在找钱时,看不清计价器上的零头。而是因为他们在拉人时常把车上的破收音机开得声音老大。
记得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位乘客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声音,把手中的冰激淋摔在了车上。
仅仅因为司机爱在乘客旁边收听令人头皮发炸的歌曲,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用冰激淋袭击他。
原谅我对司机如此仇视,我实在是受不了公共场合的喧闹音乐了,这东西好像无处不在。所有的商店、餐厅、车厢、机舱都布满了低保真度的音箱,它们放出的声音一定出自同一盘母带,标题是:没人喜爱的音乐。
我并不在意在我进餐的时候,那儿有一位实实在在的音乐家,远远地在钢琴上弹出轻柔的音符,但为什么餐厅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让人连谈话都觉得费劲?
为什么我想轻轻松松地逛商店时,没有任何事先警告,店里的音箱就突然高唱“我的眼里只有你”?当然,我的耳中只有它——噪音。
我居住的居民小区,每天早上7点,一群老大妈们会准时在楼宇间的空地上扭秧歌,伴奏音乐自然是锣鼓。你可以想见7点钟还呆在被窝里的人们的烦恼。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什么。最后,我觉得自己受够了。通常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把被子掀到一边,跳下床来,决定不论承担什么样的个人风险,我都要写一篇文章抨击这种事。
我希望有人能发明一种强有力的发射机,可被方便地带在身边,一旦有些家伙开始在你身边制造噪音,你只需简单地按一下按钮,发射机就可以发出一种信号,使他们的头脑发炸。比方说那些出租车司机,他们车中音响设备的低音,总令人担心会把路面震裂;如果我拥有了这样的装置,他们就会噤若寒蝉了。而且,这种发射机还应当能够用来关闭邻居家的卡拉OK机,以及一切说客们的嘴。
北京 胡辛
陈毓祥和余纯顺
收到了1996年最后一期《生活周刊》,从封面上我一眼就认出了陈毓祥。他那大张的嘴也许是在喊“拉我一把”,但也许是在高呼“保卫国土”。真的我很高兴贵刊能在年终回顾中选出陈毓祥和余纯顺这两位勇士,我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两位是最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人。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出色的人物,但他俩最令我感动。
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中国的仁人志士、知识分子都坚韧不拔,总有一些人深沉,也总有一些人激昂、呐喊,天真和率直并不是个人的错。但如果这样天真和率直注定要酿造悲剧,那么这悲剧也是美丽的。总之,我觉得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人为她的美好去真正地做些什么,或许是赴汤蹈火,或许是默默奉献。
呼和浩特 王晓中
人会变成乌鸦吗?
最近,上海电视台时常在节目间隙插播一个公益性广告:一只长大的小乌鸦飞来飞去“反哺”老乌鸦。这个广告多看了以后,总觉得里面有些不太对劲。当然,我要是反对,这自然是违背了传统悠久的孝道,可能要被人认为“乌鸦都不如”了。
以孝治天下是历来皇上的技巧。孝是能引申出忠来的,这是层政治因素。也有实际的考虑,没有退休金领的老人自然得靠满堂儿孙了。那时候除讲孝道以外,还讲究人伦亲疏,还形成一种宗族制度。宗族制度后来被搞得极臭,成为万恶的封建制度的具体表象。然而,它到底也曾有过温情的一面,人谁个没有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的,自然只有靠周围的亲人了。
原先这些东西是见于文献之中,然而有一天却在电视里见到,我们被教导说,要像乌鸦一样反哺。这令人吃惊。
本以为,人类总是在进步着的,我们从农业社会走出来,步入现代社会,这是种进步。究其根本,这种进步便是让人们不再局限于一种大部分是依靠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多种欲求的社会。无疑,这种方式是脆弱的,也是低效率的——不过,面对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也是比动物、比初民要显得更强些。
现代社会当然应该更好。比如,现在的儿童能享受免费教育,还有就是我们开始有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绕了个大圈子,我这才明白,正因为如此,我看见这个公益广告才会犯嘀咕,我们会不会变成乌鸦呢?所以才有些担心,有乌鸦般的孝子固然好;可万一碰上个不孝子又该怎么办呢?实际生活当中不仅仅是这些,这个社会好像是在用着“自给自足”的脑子建设着城市,建设着所谓的现代生活,因而缺陷也就难免。当我骑着车每天上下班看见满街的自行车流,我就在琢磨,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是怎么回事?
上海 费隽
中国球迷没有名片
迷恋中国足球近20年,使我有幸见过不少足坛名人和体育记者的名片,印制精美,职务显赫,令人敬仰。名片是他们工作的需要,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然而,偌大之中国足坛,持有这种名片的毕竟是少数。千千万万痴情的球迷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这种名片。多少年来,苦难的中国球迷用发自肺腑的呐喊,为同样苦难的中国足球献上了自己的一瓣心香,默默推动着足球之舟奋力前行。
毫无疑问,中国足球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足协的领导,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那么,中国足球的发展能否离开难以数计的普普通通的球迷呢?
在有些人眼里,球迷算什么呀!素质差、水平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跺跺脚,鼓鼓掌,摇摇旗,说不定啥时候还会惹出大乱子。中国体育同世界接轨,实行职业化,需要的是体制的转变,是金钱的刺激。球迷能做什么?
于是,在不少省市、地区,足球俱乐部急急忙忙地成立了,球迷协会却无人管、没人顾了;精明的经营者则把票价的提高同物价的增长“适时而有机”地结合,有钱的大公司、大老板向有名的球队频送秋波,一年收入数万、数十万的球员,竟然还在公开叫苦哭穷!
可是,球迷呢?有谁想到了我们可爱而又可怜的球迷了?8小时的工作一会儿也不能耽误,因为“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3口之家的里里外外不能扔下不管,因为那是自己的大后方;球赛又不能不看,因为那也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过高的票价,又令多少工薪阶层望而却步,那水平忽高忽低的联赛,又让多少球迷心急如焚。中国球迷,你有多难呀!
轰轰烈烈的’96甲A联赛过去了,俱乐部论功行赏,足协评这个优,发那个奖,圈内圈外人人兴高采烈,球市看好,观众增加,赛场没有出现大的意外,而这一切该归功于谁呢?有谁能给千万球迷一个公正而准确的说法呢?
“中国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中国却有世界上最好的观众。”外来的和尚施拉普纳先生虽然未能念好中国足球这本难念的经,却说出了国人难以说出的大实话,实在发人深思。
石家庄 陈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