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永 林森 布丁 刘慷)
我所厌烦的广告
李永
我打开电视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喊大叫卖啤酒的广告。
我换了一个频道。每次看到大喊大叫的广告时,我总是这样做的。我宁愿观看供求信息、地方戏欣赏甚至“农村各地”也不想观看这类东西。
我的解释是,这些广告不是由厂家出钱播出的,而是由其他电视台赞助的,好让我赶紧换台去看它们的节目。很久以前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那是基于另外一种经验:街面上的小商店常常会挂出“挥泪大减价”、“血本无归大甩卖”的招牌,仿佛架起高音喇叭招呼每一个过往行人进店,但我却总是疑心那些招牌是毗邻的大商店为了招徕顾客而偷偷放在小店门口的。
还有一个恼人的广告是,一个肥头大耳、表情猥琐的家伙坐在宝座上,直着脖子问还有什么好吃的;一个太监模样的人一路小跑过来,献上一只海碗,极其奴才地说了一句:“皇上,吃××黑芝麻糊……”
我相信这则广告起了分裂社会的作用,因为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既不想当皇上,更不想做太监。
我还要告诉你我反感的另一类广告。“每个月的那几天,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车胎爆了,真倒霉,但最倒霉的还是每个月的那几天——”。最倒霉的是电视观众,亲爱的广告商,因为正常的生理现象引发了复杂的心理反应。
准确地说,最倒霉的是女观众。不知从何时起,女人是否还是女人开始依赖于她们是否使用某种产品。幸好我不是女人,否则可能精神会崩溃。
广告就是劝别人买你的东西,但这种“劝”要有分寸,有风度。几年前,北京电视台创办《电视商场》,男女主持人带着观众逛商场,态度和气地为消费者提供参考,男主持人被评论称为“大众女婿”,女主持人被称为“百姓儿媳”。但是,这对男女推销的色彩越来越重,现在,他们不叫什么大众女婿或儿媳了,他们被称作“北京最大的两个托儿”。
戴个眼镜
文◎林森 图◎王焱
我的一个朋友静悄悄地结婚了,没有举行婚礼,所以得见新娘真面目的人并不多。这位朋友早年间是个迫求完美的人,而今娶了亲,我就特想知道那该是个怎样的美人。
于是我便向另一个朋友打听,是否见过新娘。回答我的第一句话是:“见过,戴个眼镜,长得……”
听了别人的转述,新娘的样子反而更加模糊,我就再找个人去打听。这第二位又给我形容了一遍,开头是:“戴个眼镜,摘了眼镜还可以。”
听别人讲某人长得什么样,实在是件费劲的事。两位朋友所描述的实在像两个新娘,共同点是“戴个眼镜”。我决定不_再乱打听,那太无聊。
没过两天,又有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作客,聊着聊着,说某某结婚了,新娘戴个眼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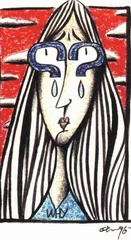
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这3个家伙说起那位新娘都以“戴个眼镜”开头,可见戴眼镜是个大特点。西方人有句话,叫不与戴眼镜的女人调情,想来,他们认为戴眼镜的女人是“另类”。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桩旧事,想起了我的一个老情人。那姑娘的眼睛很漂亮,我不愿意和戴眼镜的女人谈恋爱,也不愿意和小眼睛的姑娘谈恋爱,所以,我以前的女朋友都一律有一对大眼珠子。不过,最最火眼金睛的那还得算我。
某日,我见到了那姑娘的一个老同学,他知道那姑娘是我女朋友,便打听近况,我就说了,也向他打听那姑娘的旧事,他也说了。说着说着,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即那姑娘曾是个大近视眼。
知道这消息,我并没有觉得怎么样,依旧很爱那姑娘。并觉得自己不找戴眼镜的姑娘实在是个错误的原则。
有一天,我与那姑娘在街上散步,过马路时,她表现得有点儿迟钝,那一刻,我忽然克制不住地说:“你今天没戴博士伦吗?”
她听了,呆立在马路中央,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让她留神汽车,她却只对我怎样发现了博士伦感必趣,不顾车流不息,一再向我追问。
那以后,那姑娘对我渐渐疏远,大概认为我这样的人,到处搜罗姑娘的情报,有点低级趣味。而我当时坚定地认为,博士伦的秘密是个导火索。
现在,我还是那个臭毛病,老爱乱打听,而姑娘是否戴眼镜依旧是块病,藏在好多人心里。
受迫害的叔叔
布丁
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某个夜晚,那时我还很小,算起来是20年前了。那个夜晚,爸爸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屋里密谈,讲的是“江、姚、王、张”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说所谓“四人帮”。
爸爸的那位同事,我当然是叫他叔叔,这位叔叔是所谓“高干子弟”。我记得我去过他家,他跟他的父亲住在一幢小楼里,房间的面积很大。在那里,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作电视的东西。
再后来,这位叔叔的工作有了调动,但仍旧常来找我爹谈论时事,他们还是用姓氏来指代大人物,很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这令年少的我很是敬佩,非常喜欢他们说话的口吻。
终于,我长到足够大,也可以和他们一同讨论,比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如“反腐倡廉”,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盼望这位叔叔的到来,因为我难以跟我爹两人谈论时事,那缺乏平等的气氛。
这位叔叔到我家作客极有规律,一般是全国人大开会、党的大会期间,来的频率极高,再就是某位领导人发表某个重要讲话,第二天准会来,《人民日报》发表了什么社论,他也会在第二天来我家作客。
他到我家,总会给我烟抽。那曾是我可以在我爹面前安然吸烟的唯一机会。
再往后,我可以坦然地在我爹面前抽烟了,因为我又长大了,而且工作了。烟也越抽越好了,跟我爹说话也平等了,而且越来越像个大人,可以向我爹嘘寒问暖,并赏给他一支“骆驼”或“万宝路”。这就不需要那位叔叔赏我烟抽了。
渐渐的,我对参与他们的讨论毫无兴趣,我爹也老了,跟他说话越来越少,他更愿意问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之类的问题。
那位叔叔已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每次见他来我家,我都惭愧地想,昨天的《人民日报》又有什么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了?电视、电台中又播什么新闻了?叔叔忧国忧民的态度让我自责——太不关心时政了。
整整20年了,这位叔叔到我家来讨论问题的习惯未见更改。认真的态度也没有丝毫减弱,谈话的口吻依旧。他的生活当然有了变化,结了婚,生了孩子,但这不影响他继续以天下为己任。他的衣服寒酸,并没有利用他父亲的权势为自己谋什么好处,当然,他的父亲也是已谢世。
现在,我已与父母分开住,但回家的时候还偶尔会碰上那位叔叔,他见了我总有讨论问题的兴致,这让我痛苦而难堪。不过我爹仍有耐心听他说话,送他走后总有无奈的苦笑。
坐在马桶圈上的“规则女孩”
刘慷
某老外,男,属于入乡随俗的那种,临来中国先学会了使用筷子,到中国以后又学会了随地吐痰,被戴红箍的老大娘开了单子之后,恍然明白一味地随俗并不一定安全。大多数人都做的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符合该社会规范。
有鉴于此,他在马桶圈的问题上开始坚持原则,上中国人家的厕所时,也不忘了小便过后把马桶圈放下来。由于一般的中国男人已经能做到把马桶圈提起来再撒尿,所以他如厕时倒是少了“举手之劳”,只是完事后总要再把那些中国男人提起的马桶圈放下来,不如人家一走了之来得潇洒,心下十分委屈。为求心理平衡的缘故,他向一位中国女人抱怨中国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恶习,提醒说放下马桶圈来是为了女人再用的时候方便,这在西方社会是必守的规则,而中国人还缺乏这样的Common Sense(普遍认识),云云。
孰知该中国女人并不买账,说既然在中国没有这样的Commonsense,那么他这么做就极不合时宜,会让人从他放下的马桶圈上误读出“他小便时没提起马桶圈”或“他蹲着撒尿”等信息,那岂不更加冤枉?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儿,中国女人说,她根本就怀疑这样的规则是不是自作多情:很多女人——以她自己为例——并不一定想做什么“规则女孩”,因为诸如此类的规则都无非是ladies first(女士优先)的套路,它们把女人设为老幼病残一样需要特别关照的对象,反衬了男女两性依然不平等的现状。能不能relax(放松)一点,诚心心疼女人的话女人自己会感受出来,并不在于马桶圈上的花活,所谓“包子有馅儿不在褶儿上”。否则人际关系简化成了规则的遵守,不假思索亦不费力气,掉进了仪式化的怪圈。
说到这里,在旁的某中国男人忍不住调侃了一句:“就是。一味强调规则的结果是,我还可以说,你(指那女的)上完厕所为什么不把马桶圈替我提起来、为我行个方便?”
女的打断说:“你这样说就是矫情。别忘了我们的讨论上下文仍是在男性社会里,女人一向在‘与人方便’,现在刚刚开始考虑‘自己方便’的问题。若是大多数男人在抱怨他们的不便了,这世界岂不是倒过来的。” 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