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3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辛 费隽 黄侯兴 邹洪波 孙桂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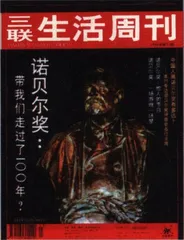
贵刊以详尽的资料与难得的独家专访,引导我们阅读了诺贝尔奖背后较丰厚的文化思考。这是一个世纪文化蕴含的象征,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游戏与梦的关系。
北京 罗辛
也谈“焚书”
翻开贵刊第19期,《读者来信》的第一封,赫然是《期盼焚书》,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人在盼焚书呢?
然后,作者称,焚书并不可怕,关键是看焚了什么书;然后,作者又谈到目前学术书籍每况愈下的状况,等等。虽然松了口气,然而我终究不能释然。
或许有这么本书,又有这么个人读了这本书,撂下书本之后,他便去做坏事了——比如偷、比如强奸(很多人讲有些书诲淫、诲盗)。那么,这本书该不该焚掉,依我看来,还是不该(或许你一个人,或许你和另一些有相同看法的人在一起,决定把该书焚了,这当别论)。为什么不该焚?因为,假如可以焚烧的话,接下去的问题便来了:第一是焚书不标准;第二是谁来制定这个标准。
或如文中讲的,秦焚书尚有一条可嘉许的标准,是焚了“不中用之书”。并且,作者又称,此标准亦可用于今天。那么,什么叫不中用?被秦焚毁的“不中用”之书不可考,不知是不是有中用的。不过,罗盘只对风水先生有用,然而在国外却是于航海技术的发展飞跃功莫大焉。而在老先生却是把“无用”作有用,且言之凿凿。可见“用”与“不用”也是因人因时而异。由此推想,这“不中用”一说是过于危险了,它极可能埋没“有用”的东西了。
如果连“不中用”的书都要焚毁,自然,像《红楼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书自然要焚。然而,这些在过去时代的禁书,在今天却是份优秀的遗产。
或者,我们很聪明,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办法,然而,又有个疑惑,有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全国同胞一心一意,则万事大吉。这全国同胞万一冒出一两个人来反对,他认为这书有用,他认为这书无害,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的意见?
或者上面讲的全不成问题,还有一个是我最反对可以焚书的理由。比如,有这么个专管焚书的机构,姑称之为“A”,今天A 说“诲淫诲盗的书要烧”,我们就说,“对”;A明天说“琼瑶的书是好的,不能烧”(A喜欢这类书,因此这么讲),我们又讲“对”;这其中又有好事者写本专著叫“论××与××”,来证明琼瑶的书十分了得。第三天,A说,“陈寅恪的书要焚毁”,我们怎么办?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不过陈寅恪的书倒是没给烧掉,因为,在某个年代,陈寅恪的书就根本没能出版。
于是,A开始为所欲为,不喜欢的书要焚毁;认为是威胁到自己的书也要焚毁。比如说秦皇帝的焚书原本就是出自此目的,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却不仅是焚书,接下来两个词是“坑儒”。同样,在不让陈寅恪出版书的年代,大家也知道曾发生了什么。
有生物学家说,人类之所以选择两性繁殖,是因为这样遗传能产生多样化,而多样则有利人类对付各种变化的环境,因此,也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单细胞发展当然很纯,一代与一代,一个个体与一个个体都一样。人类的繁殖并不这样,因此人类也就有了各种文明,当然,也因此有了“贤”、“愚”、“肖”、“不肖”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宽容,那怕某物某人叫人憎恶。花固然可爱,可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办法让自然变成一个只有花的世界。
焚不焚书也是同样的,如今书架上或许是有些叫一些人不齿的“粪土”或“泡沫学术书”,可也有其它。更何况,如果焚书的话,焚到最后,书店里只有革命领袖著作和鲁迅的书了。
幸好,冀君只是发发议论,只是要警诫一番。然而,我也只是发发议论。
上海 费隽
话说“圆汽车梦”
“让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近来,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关于这方面的宣传,或者说是“制造舆论”,可谓足矣。不少百姓——尤其是年轻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天天在做汽车梦。
眼下流行“三大件”:电脑,住房,汽车。过去流行的彩电、冰箱、自行车的“三大件”,早已过时。
我是属于想“圆汽车梦”里的一个,但据我看来,目前的汽车宣传,制造舆论有余,科学分析不足。
问题之一:“圆汽车梦”的时间多长?1年,3年,5年?倘若定为3年,即1997-1999年,按现在北京市民的年人均收入计算,假设一户3口之家,两人就业,每年节余两万元,3年合计6万元。即使如此生活水平,除非降低车价,否则还是买不起车的。更何况要达到每年节余两万元的标准,现在北京的工薪族还不算太多;更何况那“三大件”的电脑、住房也还要用钱去购置呢!
问题之二:所谓“千家万户”,“普通百姓之家”,是否应该有一个量的概念?即普及率达到50%,抑或是70%?按50%计算,北京市现有人口1200万,假设一户为3口人,3年以后,北京将有200万户人家拥有私人小轿车。现在北京市私人拥有小轿车约20万辆,这就意味着3年后将增加10倍!
问题之三:这200万辆汽车(还不算企业、机关的车和外省市进京的车)的车流量问题、停车场问题,需要有序、配套地解决。诸如交通、能源、环保、卫生、城建、管理等诸多部门,3年后是否能跟上这飞速发展的需要呢?这不是“杞人忧天”。日本可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去过几回繁华的东京,那里堵车的现象十分严重,迄今也并没有解决。……
我们过去吃过许多宣传过热带来的苦头。曾记否,1958年农业丰收,于是新闻媒体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说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吃饭不要钱,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饭……结果呢?教训不言而喻。
北京 黄侯兴
仪表和素质
编辑同志:
从仪表中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这个道理似乎不用笔者多言,因为当今社会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的人们都能理解。因此,注重仪表,提高素质,相互提携,共同进步就成了“文明人”的必然追求。尤其在演艺圈儿里,由于职业的特点,这个问题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留心一下演艺圈儿的“现场直播”,您会发现;令人忍俊不禁,甚至瞠目结舌的“出演”不绝于眼!有时您很难想象,口口声声要对得起观众的一帮俊男靓女们(其中以年青后生居多!)在大庭广众面前竟能如此“毫不为己”地“遭贱”自己,整个一“混不吝”的气派!
前不久,电视上播出了有关流行乐坛十年回顾与表彰颁奖晚会的新闻。时间不长,镜头不多,但就有那么几个镜头令本来对此很感兴趣的观众(如本人与家人)看后如鲠刺喉,大倒胃口。在如此庄严而隆重的颁奖晚会上,在如此正式又郑重的社交场合上,竟有人身着脏兮兮的牛仔装登堂入室,更有至少两个“星星”背着小学生式的双肩背挎包在镜头面前摇来晃去、侃侃而谈。
也许有人会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你管得着吗?这话乍听起来不错,但一细究,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试想,再各有所好,您能穿着小背心大裤衩出席这种晚会吗?您再各有所好,也得讲究场合和地点。记得曾有文章以北京有人身着老头衫儿大裤衩出入人民大会堂听交响音乐会的事儿大发感慨,声言国人素质低下。虽然是平头百姓所为,也确值得揭示与警示。但面对目下还有人精心包装的“星星们”都如此这般的不入流和不着调,足以显示这已经不是哪个阶层和群体的小问题了。
对一些演艺圈儿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要想对得起观众,您得先对得起自己!要尊重观众,您首先要尊重自己!否则,在“各有所好”的旗帜下站着的只能是一群“我是××我怕谁”的主儿!这将是一幅多么可怜,可笑又可悲的图画啊!
北京 邹洪波
“暴利”与“名流”
现在商界牟取暴利的现象,莫过于服装行业。北京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主持人,曾揣摩着“暴利”这个概念,想对“暴利”作定量分析。他们去询问了经济学家:“赚多少钱才算暴利呢?”不料,经济学家回答说:“中外经济学界,对于‘暴利’,并没有一个界定。”
其实,这不算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普通市民百姓心理,早有一个不成文的答案。譬如一件皮制短大衣,成本800元,销售价1000元至1200元,这是合理价格;倘若标价3000元,乃至4000元,这就是牟取暴利。
当皮制短大衣刚流行、属于卖方市场的时候,商界如此牟取暴利,可能会被一些想赶时髦而口袋又鼓鼓的人所接受,因此门庭若市。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以后,这种行为就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抵制,所以会变成门可罗雀。
近来,许多销售服装的商店、大厦,常常挂出一块大牌子,或7折让利,或5折出血。实际上,这“5折出血”,对于经销者来说,仍大有赚头。
我由“暴利”联想到“名流”。如今想当名流和已经“挤”进名流的人,可谓多如牛毛。倘说“暴利”尚可粗略地作定量分析,那么,“名流”就很难作量的测定。譬如电视播音员,电影演员,他(她)拥有广大的观众,是不是就算“名流”了呢?而一位教授,终年只面对几十个学生讲课,知者甚少,是不是就不算“名流”了呢?
正因为“名流”更难测定,于是奉谁为“名流”就带有主观随意性;然而,一个电视台,一家电影厂,这也是“名流”,那也是“名流”,处处是“名流”,那“芳名”也就无须“流传”了。最近某家出版社编纂文化名人词典时,播音界只确定齐越、夏青二位,我以为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因为几乎都是“名流”的播音员,收录谁与不收录谁,都是无法平衡的一个难题。
古人讲“桂冠”,今人讲“头衔”。头衔越重、越多,就越是“名流”。且不说当某一学会的“理事”也算“名流”,还郑重地印在自己的名片上。还有那“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你知道它都囊括了什么人吗?本来叫影视演员、相声演员、播音员、杂技演员、舞蹈演员、戏曲演员……大家一看一听就很明白,现在却偏要冠以“表演艺术家”,甚至还要称以“表演艺术大师”,这又何必呢?难道奉为“家”、“大师”,身价就抬高许多,观众、听众就认可了吗?
鲁迅先生希望自己的著作“速朽”,临终前的遗嘱也希望活着的人们“忘掉”他,但愿想成为“名流”和已经“挤”进“名流”的中国人,学一点鲁迅的品格和胆量,让“名流”热降点温。
北京 孙桂春 焚书名流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