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0)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刘慷 布丁)
多多不益善
舒可文
我有过一副价值10元钱的手套,深棕色,衬里是血红的一层绒布,样式质朴,短粗的,底边刚好与手腕相齐,绝对是“手”套。没有分毫越权,指尖圆秃秃,结构起整个手套的所有缝合线都暴露在外,套在手上有一种要干点什么的架势。其实我戴着它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为,冬天,走在路上戴着它们双手显得从容一些,骑自行车不用缩着肩纵容袖子兼顾着手,手里提了重物不致血脉不通。我之所以把它们观察得如此仔细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特别的好,是因为我戴了它们4个半冬天。第5个冬天里的一个傍晚,我戴上它们提着草篮去买菜,菜还没买齐,手套不见了。我沿着买菜的路线一路折回去找,起初还心情平静,丢了的东西自然应该找一找,如果找不回来就算倒霉,小小一双手套丢了,不过小小的倒霉。但是这起初的平静心情经不起4个半冬日与之相伴的淡淡记忆的冲挤,一点一点挤走了平静,心里越来越堵得慌,至今想起它们还是耿耿于怀。
我也有过丢钱的经验,丢得多的一次是把100元的当10元付出,过后回过味来时,骂一句“孙子”了事,不疼不痒。丢得少的一次是下楼去存自行车兜里装上10元钱准备回来时顺路买冰棍,走到冰柜前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张10元钱了,叨叨一句“莫名其妙”空手回家,多少有点烦躁,也是因为没有及时吃上那一刻极想吃上的冰棍。钱的意义很抽象,丢钱只是丢了某种可能性,丢东西则丢的是现实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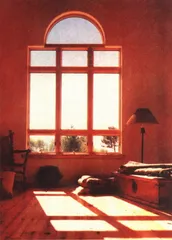
“分居”的生活
刘慷
原本是想用《“同居”生活》作题目。“同居”虽然加了引号,恐怕还是要引起误解,索性改成“分居”,发觉还是匪夷所思——其实“分居”和“同居”在我来说是一回事。“生活圆桌”主人愿闻其详,我才发现我和别人(而且还是个异性)合伙租房子住这事,在汉语里还真欠个“说法儿”,兼又联想起一位长辈既惊且奇的嗔怪:“一男一女合租,行么?”
乍一下不知这位尊敬的长辈所指为何,后见她脸上很不好意思的表情,才明白她把这事儿想复杂了。
其实我绝没有要领风气之先的意思,如果单位分我房子我何苦租房住?如果一个人租得起两室一厅,我何必要与人分室居之?我们充其量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碰巧是一男一女。如果这种组合让你担心的话,换个女伴给我不怕我搞同性恋吗?
我的意思是说,合租房子,或是任何一种人为营造的合作契约关系中,性别结构可能不那么要紧,要紧的是你是否有足够成熟的心智、有对自己和对方足够的了解和把握。
当然,合租房子的伙伴关系还不单是一种契约关系,而契约之外的关系正是人处在相互的“人”的关系中的那种关系。不夸张地说,这样一种既有公共领域又有私人空间的生活氛围,或许恰是现代人正在摸索的一种理想情况,因为人正是在这种情感纠葛以外的关系中洞见和发展自己。
“分/同居”这种字眼儿过分暖昧,我需要引入share这个词,它可以释译成“分摊”,也可以理解为“共有”,总归是“a portion that a person receives from or gives to a common amount”。我理解和学会使用这个词正是从租房子开始的——最开始的一次还是“群居”,是在国外留学期间,和来自德国、加拿大、印度3个不同国家的4位陌生的同校同学合租了学校附近街区的一幢小洋楼(house),楼上是各自分开的卧房(bedroom),楼下是共用的客厅(living room)和餐室(dining room)。洗手间和地下室的洗衣房当然也是共用(share)。房子是典型的西方家庭结构,我们这么一住也挺像个大家庭,只不过没有家长,谁也别冲谁撒娇。关上各自的房门时都好办,一到共有的空间里,权利义务划分不那么一目了然,要靠很强的自我意识兼他人意识才能处得来。这种生活氛围非常培养人的修养,处好了相当惬意,忙完了各自的就在一起开party、在后院桃子树下面烤肉吃,我对自己和对别人、别国文化的了解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头故事很多,关于每个人都有一箩筐,讲出来像肥皂剧,摆到“生活圆桌”上会显得太铺张。
回国以后仍是租房子住,share的情况也很多,虽没有异国多元文化的斑斓色彩,但也绝不乏味。上一次我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与人合租了一套两居室,也是个异性,是个开公司、做生意的小伙子,他真把我害苦了。我一般是每天闭门读书写字,动静不大,可他是每天迎来送往,客厅里老是人声鼎沸。后来客厅里干脆还住进了人,等于是把公共空间划到了他的私人空间里。由于平日里他对我颇多照应,我也不好过分锱铢必较。直到有一天大清早,他和几个哥们儿在客厅里为股票上扬了多少个点欢呼雀跃把我从甜梦中吵醒。我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地从房间里冲出来,冲他大唬大叫了一通,顿时有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之效果。可我的怨气有如冲堤的洪水一泻千里,把平克·佛洛依德的音量开到最大,在墙倒屋塌的音乐声中扬言要和他算总帐,然后穿好衣服摔门而去。
待我在北大找了间教室看了半天书回来,果然如我所愿看到他的房门安静地关着,却不知他刚才在我摔门而去的一声脆响中应声昏倒了,现在刚从医院回来。“他低血糖,一着急就昏倒,搭着今儿天儿热,”他的哥们儿解释说。我听了悻悻然回了自己的房间。整个单元里静得让人别扭,我听到自己肚子咕咕叫,便起身去敲他房间。“干什么?”他的声音里有了明显的距离感。我说请他到外面吃涮羊肉。他开门说——声音已稍释然了些——他身体仍感虚弱,恐怕消受不了涮羊肉,有要推辞的意思。我说可以给他点些稀粥之类的,总之是把他拖到了餐馆中去。两人一落座,我正要问女招待有什么粥类,他止住我说:“我要吃涮羊肉。”
现在我已搬出另找地方住了,但我和这位“室友”(roommate)仍有互访,彼此是朋友。他和我以及我交往的其他朋友一样,很不完美,但因为是成熟的人,所以可以交往。所谓成熟,有一种定义说是指具有独处和社交两方面的能力。而这恰恰能从share的生活中体现出来。
穿过你的游戏的我的手
布丁
事情又有了变化,现在,我每年淘汰掉的衣物大多远比我那副手套的价格高,也大多比它们新,淘汰前我对待这些衣物也比对待那手套尊重的多,淘汰时我像流水线上做工的人,绝对客观冷静。流水一般的买东西,流水一般的扔掉用过的东西,流水一般的认识新的面孔,流水一般的忘掉见过的面孔,生活真丰富多彩啊,以至于只有翻看照片才知道(不是想起)我竟有过那么那么一件衣服,那么那么一条围巾,而照片上站在左边的第2个人,站在前排的第3个人是谁呢?我完全不记得了。“多”是使每种东西贬值的一种方式。
罗大佑有一首歌,叫《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歌的名字有点儿绕,但读起来唱起来真有些起伏,没真正爱过哪个姑娘的人不会这么缠绵。
如今,摸谁的头发也不会有如此的感觉。不是处于热恋之中,你摸上去有可能都会忽略头发的存在,唉,不就是个脑袋吗?
这就是衰老的表现之一。
衰老的另一种表现是很难再熬夜,没那么大的精神,夜深了,也就洗洗睡了。
然而,最近的一次熬夜又让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太老,那是打游戏,从晚9点到第二天的早上,足足有10个小时,打完后接着上班。这么看,还是年轻人。
游戏是最近最为流行的《金庸群侠传》,在种种游戏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角色扮演模式,幻想自己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慢慢地升级。如果游戏以金庸小说为题材,那就更可爱了。
以前念书,老师讲过,文学作品都有些“母题”,比如“寻找”和“争夺”,当然还有别的,不过我现在只记得这两种。能记得这两种,就是因为时常要打游戏,游戏中的主角大多被赋予了“寻找”的情节主线,找武功秘芨,找宝藏等等,还要和别人打架,这该算“争夺”。
按文学老师的说法,爱情小说的“母题”大多是“争夺”,比如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姑娘,这就叫“争夺”,这种模式的确在许多本爱情小说里看过。
遗憾的是,我生活中的“争夺”已经结束了,没这回事了。我也没“寻找”什么,由此看来,我的生活已没什么意义,没有文学上的意义。
而好多人有另一路毛病:唯恐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故事或故事性太差。实际上,我也有这毛病。打游戏可能是种替代品,这里面肯定有特丰富的心理意味,要分析清楚是理论家、文学老师的事了,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
我要说的是打游戏的心理感受,不过一句话也就能说完:那就是穿过你的游戏的我的手。
套用这句歌词是因为打游戏也颇为缠绵,你要“embrace”键盘,凝视显示屏,也会脸红心跳,你用手穿过的将是一大堆故事情节,那比谁的黑发都复杂得多。
然而,打完游戏,回到现实生活中,我又不得不面对没有“母题”的日子,想一想,我会争夺什么,我会寻找什么,什么都没有。人们可以把这种日子定义为“等待”,实际上,我也不等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