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楚人 布丁 阿肯)


“猫性”、“狗性”与人性
刘君梅
人对动物有偏见,就象人对人不可避免的有偏见一样。
北京的一位评论家对猫就有过偏见,但一件事改变了他,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在11月14日的《为您服务报》上。讲的是他家曾养过的一只猫。1992年,他家自前海恭王府附近的旧宅乔迁至亚运村以北的新居,那只猫却表现了焦躁不安,后来失踪了——评论家夫妇仿佛丢了朝夕相处的儿子。一年后,评论家原来的邻居打来电话:说那只白鼻子虎纹猫近日出现了,她带了一只和她一模一样的小猫(显然是她的儿子)来瞻仰故居。那大猫跳上已废弃的评论家的儿子的小木床,趴了好一会儿。那不谙世事的小猫在地上仰着脸好奇地看着。大约一刻钟后,一大一小两只猫走了。评论家夫妇急急地叮嘱:“再见到它们务必先把它们留住,并来电话相告。”但那两只猫再没出现。评论家感叹那只留恋故园的猫要走至少7公里的路,其间还要避开无数风险,而且它出走时正是北京滴水成冰的冬季。
另一个故事是我不久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是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的狗千里寻主的故事:波黑那家人逃难时忘了带上狗,那狗历尽艰辛爪子磨出血,终于寻到难民营,主人一家感动得涕泪横流,发誓再也不和它分开。
请注意这两个故事的不同之处:狗是忠诚的,无论如何要和主人在一起,当然也只有追随主人才体现狗的价值。猫却自有主张,有时就会作出放弃和主人“共荣”而甘当流浪猫的不可思议的事。我绝不贬低狗,只是觉得它的忠诚盖住了它的智慧。我对猫则不得不敬——听说在老虎也可以被驯服的马戏团,猫却很少见,即使有也是最不听话的——只能这么说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东西聪明且本领高强。“不驯服”——猫便得罪了很多人。
我并不想让狗和猫分出高下。我的本意是透过“狗性”、“猫性”看看我们自己。想象一下,现今的人大多奉行投人以木桃收之以琼瑶的“实用利己哲学”,怎么可能花钱和心血养一只在自己眼皮底下自行其事的猫!更多的男人,还有一些女人(比如女强人、富婆)在电视上大谈喜欢狗,并且样子越凶越好——这样的狗可以让他们达成一种平衡,他们那颗有极强统治欲的心“虚荣”且“虚弱”。现在正是冬季,他们可能正一边吃狗肉“补虚”,一边大谈狗的优秀品格呢!
这让我想起克林顿,不管该总统政治上多么幼稚,它敢力排众议把猫(而不是狗)带进白宫,说明他还挺真实可爱的,这在风云莫测的政界更罕见。
为此,不久前我在Internet上看望了克氏那只叫“白袜子”的猫。
各活各的吧
楚人
同事中一后生,整天吸坐电脑前不思茶饭,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其情状犹如农夫之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众人不解。说起来小伙子模样周正,性情温和,年龄虽从事业上说还年轻,从爱情上看已不小了。也曾有众女子频送秋波,无奈他沉迷于电脑,心无旁骛,使得热心善良的同事们十分焦虑。
一日,一位大姐开恩似地告诉他:“我一定要给你介绍女朋友,那样就不必成天跟这枯躁的机器打交道了。”不料一向沉默似金的小伙子双目横挑:“姑娘哪有电脑好玩?你怎么就不明白,人们去恋爱多是因为不懂电脑?”义正言辞地说完,一埋头又回电脑,留下大姐愣了半晌。
这话说得稀奇。它那么轻易地就否定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认为可以不争的事实:“谈恋爱是远比电脑更有意义更必须做的事情。”看来,即使真理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被一些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人和人是那么不一样,对同一问题,结论竟天壤之别。怎么办呢?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就是了。就恋爱和电脑而言,谁更好玩更值得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喜欢爱情的人去爱姑娘,让喜欢机器的人去爱电脑,没事儿的。
生活中许多矛盾貌似对立,实则不沾边,理应共存,完全没必要弄得不共戴天。我们常听到做学问的人鄙视赚钱的商人,说他们利欲熏心,奢华无聊;我们也常听到有钱的人嘲笑读书人,说他们不识烟火,枯躁乏味;其实在我看来,作为生活方式,读书和经商实在各有各不可替代的乐趣,只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罢了,没必要相互攻讦。说到底,赚钱和读书都只是手段,对真正优秀的人来说,不管干什么,剥去这些职业的外衣,他们的幸福感肯定会在一个更深处汇合。
由此我们看到,生活中许多矛盾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对立。许多争论和指责其实源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或无知。一个人对世事的容纳,跟自身的丰富程度很有关系。道理是这样的,以人性看,一个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容忍往往比对别人要来得容易。我们经常对别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被默认。于是,一个人自己越丰富,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层面越多,他对别样的人事接纳就越容易,对世界的眼光就越宽厚。
所以说,我们应该习惯观念和选择的分歧甚至对立,相互不懂没关系,只要相互容忍;哪怕相互不睬,也不要相互操心。“理解万岁”固然好,不理解呢?各活各的罢。
交流的乐趣
布丁
我有一件遗憾的事。那是上大学时,我在食堂吃饭,一个姑娘端着饭盒走到我面前,她向我鞠了一下躬,才坐到我对面的位子上,我反应过来,那是个日本姑娘,我很想跟她说话,可我不会说日语,于是就闷坐着吃饭。我遗憾的是我没有想到用汉语跟她说话。
交流能够有乐趣,但要交流就要依靠语言。对于我这样一个外语不好的人来说,跟洋人交流的乐趣并不大。
实际上,同讲一种语言的人彼此交流起来会有更大的误会。这一点,我在近几年的生活中屡有感触。你如果说你不喜欢钱,我肯定不这么看,而认为你其实是很喜欢钱,只不过混得不好。你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肉,我也不一定这么认为,觉得你装蒜,假装是个“素食主义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我最近的一次交流大有乐趣。那是一个星期日,我回父母家,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岁,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他是个哑巴,以前我见到他只会对他笑,他也只能对我笑,现在不同了,我学过一段手语。
我跟他说,我要回家睡觉,他听了后很高兴,跟我说了几句话,可惜他比划得太快,我看不懂,这时我犯了个错误,习惯性地把脑袋探过去,那是听不清别人讲话时特有的反应,但我立刻笑话自己,这样脑袋贴得再近也还是“听”不清,他看见我的反应后又沉默了。我于是再问他是不是结婚了,他的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告诉我他早就结婚了,而且有了个孩子,理所当然,我该问是儿子还是女儿,可惜又忘了该怎么表示,便随手做了个下流的手势,他见了脸上笑容灿烂,使劲点头。我明白他已经有了个儿子。
事后想起有些后怕,万一他见了我那手势,竟以为我在骂他,岂不糟糕?但他却是那么开心,看来,这样简单的交流不会有误会。
然而,一说话就会有误会。我跟哑巴聊完天,下车时掏钱买票,告诉售票员“一张票”,售票员竟然有些惊讶,她看到我们聊天,把我当成了哑巴。
跟哑巴聊完天,我好长时间都很高兴,这世上没有那个会说话的人能通过一次交流而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我甚至认为,好几年来那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一次交流。
不要以为我因为表现了一点儿“爱心”才沾沾自喜,我对我那朋友唯一的不满是他不能跟自己的儿子说话。我认为跟自己的儿子说话是最有乐趣的交流,而是否能听懂别人的话,是否能让别人听懂你的话都并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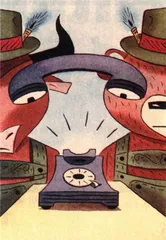
这世界对男孩不再安全
阿肯
8岁的外甥有一天放学回家,兴致勃勃地教我唱歌:“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要炸学校/天天不迟到/一拉弦,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炸飞了……”教师出身的姥姥大喝一声:“你在胡唱些什么!”小外甥置若罔闻,一边忙着在地上摆玩具,一边继续大声唱。姥姥无可奈何,问孩子他妈:“这孩子是不是患了多动症?”
男孩终归是男孩。他们热衷于玩富有刺激性的游戏(哪个男孩不爱枪呢),经常打碎东西并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他们会吹牛皮、说大话,爱撒谎,不愿做作业,还把脏衣服随随便便丢在卫生间里。但如果他们摔倒在地,他们不会喊痛、不会流泪,而是坚强地重新站起来。他们勇敢且富于冒险精神。
然而到了今天,这世界对男孩来说已不再安全。如果一个男孩稍微表现得有点过份坐立不安、好冲动、富于破坏性或易烦躁的话,他就会处于家长、老师和儿童心理咨询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
也许他是患了多动症,这种病是时下的多发症,也是医生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种儿童行为失调现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个女孩被指认患了多动症)。与做作业相比,他更喜欢玩电脑游戏或闲逛吗?那么他可能患有诵读困难症。我曾经认为,对男孩的行为失调,许多家长仅在口头笼统说说而已,并不放在心上,后来我才发现,领着男孩上医院看心理门诊的现象并不鲜见。
为什么人们乐于将疾病泛化呢?过去许多行为被认为是男孩的正常表现,现在却被看作病态行为。我常常想,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芬如果在世,是否会被诊断为多动症患者,甚至被扣上神经错乱的大帽子?
为避免有人不熟悉外国作品中的男孩形象,我竭力想找出一个中国文学中的对应人物来代替索耶和芬,可惜的是,实在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