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宋成 巴哈 陈大超 刘恪 王东 陈雯 熊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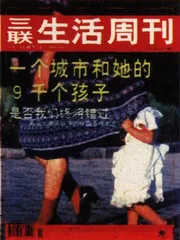
前后两篇文章,对科学研究的现状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而细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更为深刻——冷淡与浮躁,正好说明了我们缺乏真正的科学意识。
沈阳 宋成
纯洁心灵上的投影
《生活周刊》编辑同志:
我是前门西街中学初一年级的老师,刚开学,我布置学生们每人交一篇作文,写写自己的家、爸爸妈妈和他们的生活。
收上来的作文让我十分震惊。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看似天真未凿无忧无虑,他们对生活的体验直觉与希望却值得我们做大人的深思细想。
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爸爸妈妈“下岗”了,“下岗就是没班上了”,“每个月家里只有200多块钱的生活费,爸爸妈妈为节省每一分钱而努力,甚至电视都很少看了”,“爸爸想跟人家做买卖,可是因为没有本钱,人家不让他入伙,妈妈无事可做,出去找工作,也总是一无所获。每天放学回家,看到闷坐在屋里的爸爸妈妈,我真想帮帮他们”,孩子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爸爸妈妈从来就不迟到早退,兢兢业业地工作,却没工作了呢?还有邻居不少叔叔阿姨?”孩子希望:“爸爸妈妈找到工作,全家人像以前一样快快乐乐。”
“我已经换了三个妈妈”。写这篇作文的小姑娘是我们班最好看最安静的一个,成绩也最糟糕。“我没什么可写的,我记不清亲妈妈什么样了,她死的时候我才两岁。后来,在我7岁的时候,爸爸领来一个阿姨,让我叫妈妈。阿姨妈妈长得很好看,烫着头发,冬天也穿裙子。爸爸每天和阿姨在一块,不大理我了。再后来,就是去年,阿姨妈妈和爸爸大吵一架,就没再回来。今年夏天,又来了一个阿姨,没有那个好看,还带了一个小弟弟,爸爸不让我叫妈妈,让我叫‘阿姨’。爸爸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孩子在最后写道,“我不是不爱学习,我是老担心,哪天又冒出第四个妈妈”。
类似让人心酸动容的作文还很多,不少孩子提到“下岗”,而另一些孩子则抱怨,“爸爸妈妈整天在外面忙,他们不讲信用,去植物园的事一推再推,真希望有一天他们被开除了,在家陪我或者出去玩。”
孩子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样天真烂漫,他们这些“成人的烦恼”到底归罪于谁呢?成人世界在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上投下什么样的影子呢?
北京 巴哈
甘心挨宰吗?
编辑同志:
现在若进得一个外表装璜得颇像那么回事的餐馆,往往一点菜,就有苍蝇飞拢来。看一看那菜的份量,尝尝味道,离那外面装璜的距离,真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于是我们就会惊呼,:唉,上了装璜的当。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城市一下子就兴起装璜来。那装璜材料和档次,一天比一天富丽堂皇——这使我们不得不感叹:原来是生意不好换柜台,现在则是生意不好怪装璜了。
其实生意真正好起来的,倒是那些看准了装璜业必然会越来越兴旺的精明人。搞装璜的发了,指望着靠装璜来打开局面的人,自然也要靠装璜的出奇制胜发了。只要把好钢用在了装璜上,那宰人的刀刃,也就不愁它不锋利。所以大凡在装璜上超凡脱俗的地方,宰起人来,也就特别游刃有余,锋利无比。好在当今的许多人,是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用装璜来宰他的。因为崇尚装璜的人越来越多了,洗头要上装璜最漂亮的发廊;请客要上装璜最豪华的酒楼;购物要上装璜最红火的商场;唱歌跳舞要上装璜得最迷人的歌厅舞厅;就是开会,也要找一个装璜得最显规格的会议厅——在崇尚装璜的人眼里,最好的装璜就是最大的派头、最高的品位、最令人向往的富贵和尊严。
为了派头和品位,为了富贵和尊严,被装璜宰一宰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装璜面前有上当吃亏感的人,只不过是我们这些摆不起派头享不起富贵的平头百姓罢了。平头百姓中其实也有以挨装璜的宰为荣的,因为他们看不透,那耀人眼目的装璜,其实只是一块高级的遮羞布。这算不算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湖北孝感 陈大超
样板戏是样板吗?
编辑同志:
随着文革中的样板戏一个一个地重排与重演,社会上有些人对样板戏似乎又显示出空前的热情。记得样板戏刚开始重演时,传媒曾以回到这些作品的本来形态,纠正江青对其进行的篡改为前提。而目前有些人的说法又一改常态,大有样板戏就是样板的倾向。
我想,从怀旧或者一种特定的倾向出发来重看这些作品,生发出一些对已过去的时代的怀恋,这无可非议。每一部样板戏就是一部具体作品,脱掉其附着的政治色彩,回到审美和观赏一部具体作品,每人也都应该有自己的见地。但听到目前有人以艺术的角度来评价这些作品,认为无论其构思、音乐、舞美、设计都是最现代的,总觉得里面隐藏着另一种倾向。样板戏不管如何也是当年“三突出”产物,这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曾扼杀了多少遵循艺术本身规律,从生活中创作的优秀作品的生命?要是现在再认为这种创作是样板,那么我们的艺术创作需要再进行“三突出”的熔炼吗?
怀旧并不是坏事,只不过我们不应在怀旧中忘却了当年给我们留下的烙印才好。
北京 刘恪
担扰心理咨询
编辑同志:
随着秋云等一些身残志坚的青年开办心理咨询,媒介大肆渲染,再加上人们本身认可这种新鲜的无偿服务,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一时出现了心理咨询热。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咨询业中,正规机构极少,绝大多数是半路出家的拼凑组织与私人筹办的热线。在整个咨询业中,有1/3的咨询员的综合素质都难胜任本职需要,有的没有一点心理学基础,有的缺少人生丰富阅历,大多仅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心理咨询是一门涉及到多学科的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更需要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生活的能力,如此才能回答咨询者的各种咨询。事实上,目前许多咨询员回答咨询时难圆其说,极易偏废之词。
这种情况下的咨询,如何能较好地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障碍呢?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担任心理咨询,咨询员应该具备严格的专业条件,可是谁来审核咨询员,又谁来管理咨询员?这些都值得人追究。
南京 王东
大童装:大空档
编辑同志:
日前,我的一个朋友带着15岁的儿子找遍本市大小商场的童装部,想买件得体的大童装给儿子,最终还是失望而归。坐下闲扯起来,有此遭遇者为数甚多。大童装、大空档,这一状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老大难”了。
据业内人士分析,少年装断档难买,原因是多方面的。8-12岁的孩子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无论是身材或心理都处在变化之中,其发育之快,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许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审美观,但到底穿什么好,连孩子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设计工作者说,由于大孩子审美观不成熟,要掌握他们的心态设计出使他们满意的款式非常难,甚至比设计女时装还难。生产者说,五六十年代初少年儿童一般身高1.55米左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个头普遍长高,十四五岁的孩子能长到1.6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7米,做他们衣服,耗料与成人差不多少,有些可能还要多,但价格却卖不上去,一套成人装能卖二、三百元,同样价格的少年装就不好卖。厂家反映,生产少年装几乎无利可图,童装厂基本不生产,即使捎带生产一些,款式也十分单调。商业单位看中的进不到货,看不中的又不愿进,生怕砸在自己手上。而消费者讲究的既漂亮又实惠,很多人认为花几百元给孩子买套衣服,只一年半载就不能穿了,又无人接替,不值。
目前,各地市场上高、中、低档男女少年装都缺,因此出现这样的现象:1.3米以下的小个子儿童仍买小童装穿;长得高大些的少年就买小号成人衣凑合,甚至女孩子穿妈妈的,男孩子穿爸爸的这类不伦不类的现象随处可见。近几年时兴校服,春秋季少年们的学校装与生活装几乎全部由校服所代替,至于农村少年只好更替凑合了。中国少年穿衣已凑合了一代又一代,这个空档谁来填补?
江苏盐城 陈雯
“囚”,何以成“宾”
编辑同志: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一些屡教不改的刑满释放分子和不法分子在一些地方倍受青睐,他们不仅被捧为“座上客”,而且还成了紧俏人才,出尽风头。在一些城镇,这些人频频出入于餐馆及其他公共场所、个体私营企业,表面上看从事着保卫、保镖、经济警察等职业,但实际上却少干事或不干事,只是偶尔在雇主遇到什么麻烦时出面吆喝吆喝,唬唬人,将事情摆平。其月薪以名声为标准,谁的名声响,谁的工资就高。在这里,他们俨然是“镇店之宝”。
在部分乡村,这些人也十分紧俏。目前一些农村的治安比较混乱,民事纠纷多,这些人就有了用“武”之地。某村在处理一件因子女不孝而引起的纠纷时,村主任要当事人向老人道歉,说了多遍对方也无动于衷。幸好这位村主任带着一位因流氓滋事坐牢后“刚出来”的小伙子,只见他拿来扁担,一声不响就朝当事人的双腿扫去,只听得“啪”的一声,当事人就跪下来了。这位“刚出来”的后来就成了村里的联防队员。
在少数地方,这些人甚至被请进了国家机关。江西省樟树市就有2个街道办事处的财政所于今年4月聘请了6名劳改释放人员收税。他们在被正式聘请后趾高气扬,打着为政府收税的牌子强行拦车、任意扣车、野蛮收钱,整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在其他地方,一些工商、税务部门聘请不法分子来管理市场和收税也屡见不鲜。
昔日的“阶下囚”和一些逍遥法外的不法分子为何在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座上客”?这样一种怪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湖北松滋 熊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