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晓明 荆歌 戴佳臻 昃人 刘建言 图冬泉 解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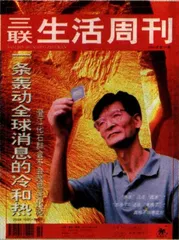
贵刊提出的全民科学意识值得讨论。当基础学科普遍向应用型靠拢后,我们目前的资源丧失可能会相当长时间地影响未来的发展。为什么全社会都对此麻木不仁?
北京 李晓明
新衣与旧衣
编辑同志:
拜读了贵刊今年第17期《人民币的破旧与公民意识》一文,感慨良多。人民币破损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它不仅有损“国”的尊严,对于持币者来说,也会显得很没面子和教养。
究其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似乎还并不是公民爱护人民币的意识淡薄,因为在货币上写字、将其乱塞乱折,大多是建立在人民币本来破旧的基础上的。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每月工资都是单位当天从银行领出的钱,发到我们手上,已如街头乞丐之衣,叫人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把它“平整地放人钱包”?
当然,公民爱护人民币的意识确实有待提高,但只有把回收旧币工作做好做实,才能使流通进入良性循环。此事与城市卫生面貌酷类,谁都不能说新加坡市民是全球文明素质最好的公民吧?
如果我们的决策者,我们的银行,真正想让人民币成为国家一件体面的衣服,就应该及时而切实地洗涤与更换这件衣服。我们不难了解到,人民币中比例极小的崭新部分,被人们宝贝似地珍藏了起来。由此可见,人们其实是非常喜爱挺括清洁的人民币的,只是它在流通中很少见到。物以稀为贵,而旧衣服比比皆是!一个尚不更事的顽童,在穿上一件新衣后,也会自觉收敛他的行动。中国人难道比外国人多一种糟蹋货币的天性么?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与此同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难道说,中国人大量涌入德国的话,德国的钱币君子状就会土崩瓦解?我真为文中提及的那个德国人担心,要是这老兄永远生活在中国,他就不再需要他那高贵的钱包了。我十分赞赏他将破钱施舍予人的举动,只是,他无疑将变得一文不名。
江苏吴江 荆歌
莫为“红包”解嘲
编辑先生:
贵刊第17期发表的《不必难以启齿的红包》和《抽薪止沸》两文,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以为陈思和先生对今日“红包”现象的现实缺乏准确的把握。“红包”确实已由“人情现象变成社会现象”,但是陈先生却未看到“红包”已由一种奖励、一种小恩小惠、一种施舍的形式,发展为一种礼品、一种企求、感谢、回报的方式,最终成为一种行贿的手段、一种社会的腐蚀剂。今日收取“红包”的对象,已不再完全是搬运行李的、端茶送水的以及长辈的晚辈们,也不止如陈先生所说的“记者、编辑、医师、小公务员和被拖去充当花瓶的名流们”,而是“红包”到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你要办事嘛,拿“红包”来!某人为达某目的,而向某关节人物送礼行贿,再不是过去拎几十斤土特产品了,而是一个“红包”,里面装着什么,只有你知我知。不显山不显水,千儿八百,一个存折,一个信用卡。“红包”已大大超越了昔日的人情界限。施予者与获取者大都已从昔日的位置各自走向其反面。
紧接着看第二个问题,就是“红包”现象之所以如此,原因何在?我以为应当是分配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越来越不“公”,竞争不是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之上,分配自然也就不公。岂不见,在一些企业、工厂,往往是企业亏损,工人只能领到生活费,而经理、厂长却发了大财。一个只领生活费的工人,家里人生病需要动手术,四处借债,筹集了一点钱,给开刀医师送个“红包”,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企求和善良的愿望,而我们的医师能把它作为一种心安理得的“经济补偿”么?!
即使如陈先生所引萨特的《苍蝇》一剧为例,我仍然以为必须首先痛斥鞭笞“篡权者”,同时,也不应同情并为获取“红包”者解嘲。
江西高安 戴佳臻
心里有没有老百姓
编辑先生: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设计就是这个世纪极为重要的领域,现代的产品、建筑、环境都赖以优秀的设计。有人提出,21世纪是设计的世纪,此言甚是。
国庆佳节,因孩子有写天安门作文任务,携子到天安门广场,有幸走了一趟前门的地下通道,从北向南,到前门西侧,先下梯过街,出来仅是广场西端;往南又得下去上来,才到“肯德基”门口。为了往东搭车,再次下通道,再出来,仍然只到前门的大车站;要越过东侧马路,还得下去上来。虽然孩子依旧欢蹦乱跳,本人亦非步履蹒跚,但如此上上下下,实在让人烦扰。假如是一位老者,或一残疾者(尚无残疾轮椅过道),怎么奈何这般折腾?
由此可见该工程设计的问题:不管是领导或设计者,连起码的疏导人流、方便群众的想法都没有。望着节日期间天安门熙攘、拥挤的人流,我想,其中一半就是由于这具体的设计造成的。城市公共设施是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不知这项工程的设计师或领导心里到底有没有老百姓?
(附带提一句,建议贵刊对北京此类市政设计水准之低劣,主要指设计意念、超前、实用性方面,作一专项讨论)
北京 昃人
“承诺”是不是恩惠?
编辑先生:
时下,“承诺”一词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上使用的频率极高。不少部门和单位也竟相效仿,公开向社会作出种种承诺,其内容少则七八项,多则十几项。条条承诺,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措施,乍看,确实给人以春风拂面,甚至受宠若惊之感。但细细推敲,却又激动不起来。如某商场推出早开门、迟关门、中午不停业、笑脸迎顾客;视顾客为上帝,不和顾客争吵;本店无假货,见一罚十的承诺。某医院作出视病人为亲人、保证24小时为病人服务、不收红包、不出售假药的承诺,某政府部门承诺,不无故推诿、不以权谋私……难道这就是承诺么?说句不大客气的话,不太像,倒像是多少年前就已制订的规章制度——再说白一些,一个极普通、平时工作中必须要遵守的规章。试问,你作为一个商场的营业人员,难道就应该冷冰冰地对待顾客和经营假货吗?你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时候,就应该收取红包吗?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应该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谋私吗?如果不是,就不应该把原本应该做到的事,好像给人以多大恩惠似的拿出来“承诺”。
推行承诺制,毋庸多言,是一件大好事。好则好矣,许多单位实行时标准未免太低了点。更使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不少部门、单位在向社会作出承诺的同时,却仍在搞以权谋私、收受红包,卖假种子、假农药等种种不良现象仍在发生。
为什么一些单位会把种种低标准、低层次的东西也拿出来承诺呢?说穿了,就是赶时髦、图形式、出风头、捞政绩。承诺是什么?解释很简单,就是对某项事务答应明办。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手段,应该建立在高水平服务的基础上,不能赶风头,图形式。否则,承诺制便会变成不是过眼烟云就是形式主义的又一代名词。
江苏射阳 刘建言
人才高消费消费了什么
编辑先生:
时下人才高消费。据统计,只招收硕士生以上的单位占72%,招收本科生以上的单位占89%以上,而招收专科生的则寥寥无几。而实际上,用人单位招聘的人才,却往往很难有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
就我所知,现就职于上海某化工公司的张某,毕业于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上海某化工公司提供给他的工作机会是充当质检员。刘小姐,外国语大学毕业,也是硕士学位,应聘于一家合资企业,说好了当翻译,实际却成为公关小姐。像他们这种现状绝非个别。河南一家机械厂近年在人才市场招收了近千名大学生到一线充当机器操作工人;上海某商厦也招收多名本科生站柜台。去年,某地竟有把女大学生安排去充当公厕收费员的事发生。人才高消费在用人单位的招聘意图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一公司总裁对主管人事的部门负责人表态:聘用人才尽可能一步到位——如同消费市场上的购物一样,很多家庭明知某些家电功能对自己只是一种摆设,可他们仍然要追求最高档次的。许多单位的老总直言不讳:高学历人才越多,对外说话腰杆越硬,有利于企业形象,也有利于营销——高学历成为摆设的需要,作摆设而并不使用。因为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知识和才华其实并不实用,这种怪现象,贵刊是否应该关注?
南京 图冬泉
重奖奥运冠军该不该?
编辑先生:
奥运冠军将获得巨奖,许多老百姓认为应该。但也有的认为奖励是应该,奖多了就不应该。这种看法,在下层群众中特别流行。
这次十几位奥运冠军,每人的奖金加实物都在百万元以上。国家体委给每人8万元,另加热心体育的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和曾宪梓合起来给每个冠军奖励110万元左右,按国家体委有关规定,每位冠军可得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再加上当地政府以及企业家、商家奖励的住房、汽车等等,加起来足有百万以上,真是令人羡慕极了,也令得了“红眼病”的嫉妒极了。
笔者认为,重奖奥运冠军是完全应该的。
我国有12亿多人口,这次出了十几位奥运冠军,近亿人口中才出一个,实在很少。再说,运动健儿虽然只“瞬间”就成了世界冠军,但他们成为冠军之前,几乎每人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训练,付出的心血,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以往工资都不高,现在的奖金完全是他们十几年血汗换来的回报。
现在,第三世界各国愈来愈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体育就是他们手中的“敲门砖”。凡有点条件,都尽力重奖奥运冠军。而我们给我国奥运冠军的奖金同他们比起来,不过小巫见大巫。例如,这次泰国拳击冠军甘辛就可以得奖金3200万铢(约合128万美元),而印尼这次也给金牌获得者奖了42.2万美元。我们的冠军仅获12万美元左右,和他们一比较,确实不算多。
认为给奥运冠军奖重了的人说,我国还很穷,连城市人平月收入也只有367元,且不说七千万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再说,我国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又有谁一下子得过百万元以上的奖金?还有的说,美国和日本等国比我国富得多,他们给奥运冠军就比我国给的少。美国两个体育组织合起来还只给一个冠军6.5万美元,而日本更小气,只给3万美元。他们的国情和我国不同,著名运动员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一个人光一年的广告收入就有几百几千万美元,而我国冠军却没有这样丰厚的“外快”。
我认为,不在于给不给重奖,关键应“重”得适当,“重”得公正。
湖南湘潭 解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