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林家雄 龙在田 王毅 王大平 张星南 王学权 郭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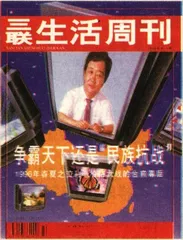
商战为何描绘成抗战?民族抗战在商业争霸中的价值,是一种典型心态的写照。跨国资本紧逼下保护民族工业确实重要,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样也应该警惕。
重庆 林家雄
奥运转播的多与少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这次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派出阵容庞大的记者团,租用独用的卫星线路,设立象样的直播室,全程转播奥运赛事,着实让体育迷狂喜。正是电视工作者付出了辛劳,才使这个闷热的夏天不那么难熬。
但是,转播中似乎无穷无尽的广告,对欣赏比赛、关注赛事新闻而言,实在是有点煞风景。每当我听到主持人说“下面请看有关报导”后,一下子涌出了感觉上绵绵不绝的广告,心里就别扭。如果我的记忆不错,中央电视台在体育传播中不做任何说明就插播广告,似乎是第一次。特别是晚上黄金时间的专题节目,不足一小时的节目中插播3次以上广告,有点过份。电视转播费用大,需要广告费支持,这容易理解。但能否在技术上作些处理,使之不让人难受?
与广告的多相反,我们对其他国家优秀选手的赛事反映得好像少了。奥运会4年一次,各国选手无不精心备战,力争赛出好成绩,各种运动的星级人物也群雄毕至,在赛场上一争高下。看奥运会,主要就是欣赏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比赛;不仅要看最后的结果,也要看之所以有那种结果的过程;不仅要看中国选手的优异表现,也要看其他国家和地区选手的精采表演。这样,也许我们才能说,我欣赏到了1996年的奥运会。
北京 龙在田
奥运会怎么啦?
编辑先生:
贵刊第12期封面故事,犀利地剖析了奥运会的现状。亚特兰大至今赛事已结束了大半,确实越看越觉得奥运精神正在变味。
时值奥运百年,在选择雅典还是亚特兰大的最初决定中,就可以清晰看到商业利益是在怎样战胜经典的体育精神。据说,在亚特兰大申办奥运的过程中,可口可乐的公关大师们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既然奥运会成了一桩大生意,所以一切以经济标准来衡量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亚特兰大可以在场馆建设、奥运村运动员宿舍的食宿条件等方面凑凑乎乎,能省钱就省钱;开幕式的场面因为要卖钱,就能够投入。能生钱的和不能生钱的部分,在此次亚特兰大被界定得特别鲜明。
应该说,此次奥运会作为一个大生意场,已膨胀到了极点。亚特兰大这样一个小城,交通堵塞,后勤保障到处都跟不上,炸弹爆炸,运动员无法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可商人们却在肆无忌惮大把大把地捞钱。本来,体育这样一种超越种族、国别,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运动,是一种平等、和平、人类进步的象征。奥运会这样的体坛盛会的100岁生日所出现的这样一种景象,不能不令人深思:奥运会怎么啦?
我觉得国际奥委会目前扮演了太高、太大的角色,给人感觉奥运会官员似乎已经是一位位频繁来往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家”,其作用与地位经常给人以超过了联合国官员的感觉。亚特兰大的奥运会100年,是不是能促使国际奥委会对自己的角色重新进行思考呢?
北京 王毅
他们应该这么累吗?
《生活周刊》编辑部:
我的孩子今年初中毕业。两天前她刚刚接到被一所普通高中录取的通知书,使悬了近两个月心的孩子和我们做家长的总算松了一口气。
回忆起孩子3年来的学习生活,个中滋味大约只有经过奋力拼博的他们和我们这些初中生家长及孩子的老师心中清楚。我的孩子从初一开始,学习就非常刻苦,每天除了完成老师留的作业,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早晨6点起床,7点多一点到校,晚上10点以后才休息。到了初三,每天晚12点才休息,而且他们班每个好学生都是这么晚才睡觉。孩子的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休息过,星期六学校有课,星期日上午去辅导班,下午晚上写作业,做一周总复习。
初三最后一学期,孩子更被上满了弦:早7点到校后参加晨跑,7:20至11:50上课;12:00午饭,12:20听力训练,1:20至4:30上课;后面还有一小时“统练”,做老师给出的篇子,大约6点左右老师还要分别对优秀生和差生进行小班辅导。8点左右回家,吃点饭稍微休息一下,即赶快做作业,到晚10点钟,我们陪孩子下楼,进行体育锻炼,因为“中考”要加30分体育成绩,老师、学生、家长谁也不能掉以轻心。半小后回到家里,孩子又继续写作业,直到12点左右,孩子才算做完了一天该做的事情。每天周而复始,整整一个学期都这样坚持着。为了中考取得好成绩,不仅是我的孩子,所有争强好胜的初中生,都是这样刻苦学习、拼命锻炼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辛劳中渡过了他们的花季。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我作为一名家长,希望能尽快改变这样将踏入中学大门十多岁的孩子,就给予强大的竞争意识,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趣,像一架不堪重负的机器,在进行超负荷的运转。
北京农业部 王大平
谁干扰谁?
《三联生活周刊》:
我注意到贵刊似乎非常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的确是很有必要的。有一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简单的、具体的、个别的,但是,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都有着深刻的原因。
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虽说事不大,但我总觉得问题并不简单,所以写信求解:我家住在北京的一个最普通的居民小区,前不久的一天,在我家旁边的一栋楼门前摆起了一排桌子,过往的居民从此经过时都显得很狼狈,因为本不宽敞的路被那些桌子占去了一部分,这已经是对大家的侵扰了。到了晚上,大约《新闻联播》刚结束的时候,突然响声大作,唢呐声鼓声咿咿呀呀,像来了一支送葬队,吵得人在自己家里说话都得大声嚎。我被吵得到了好奇的地步,非得看看这闹声来自什么地方不可,于是从6楼跑到楼下,原来的确是一个支送葬队!四五个和尚和几个不是和尚的人围坐在那一排桌子旁,吹吹打打,大约闹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干人停了一会,紧接着带上家什,排着队,吹着打着,在死者的亲属带领下竟堂而皇之地上了楼!一前一后闹了近3个小时。
如何送葬,这当然是个人的事。居住在都市里的人有各式各样,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习惯,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想,城市生活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准则,那就是互不干扰。但是,面对悲痛的死者亲属,谁能说得出口?可是,悲痛不能构成干扰别人的理由啊。如果你干扰了别人,就等于强行让别人进入你的生活方式,强行让别人屈从你的生活习惯。这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我这样想:或我真的去指责了,人家是不是也说我干扰别人呢?这里肯定有探讨的余地,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城市生活的社会学问题,是关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展。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因此,澄清并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显得越来越迫切。
北京芙蓉里 张星南
南京人,别糟蹋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
在国内众多大中城市里,“秦淮佳丽地,金陵霸王洲”,营造出“东边那个美人儿西边黄河流”完美境界的南京。
然而,随着沉睡了几十年的古城墙在市场经济和国际文化的急潮中猛然惊醒,一向温和朴素、沉静从容的南京人好像被“下床气”阻住了心窍,行事实在有点尴尬。先是庄严肃穆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差一点办起了狗展;接着,人们发现渡口战役胜利纪念碑的碑身上涂满了“××到此一游”,碑前的台阶被人毁坏;不久,又有人将雪白沈酽的牛奶倒进澡盆,引得众口大哗。这还没完,今年6月26日,南京市中心一家豪华商厦举办首届香水节,将据称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香水,用洒水车洒在市内主干道上。
孤立地看,这些怪事无非是个别企业或个人的商业行为,然而,世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事情,它总有一定的原因、过程和预期目的,并且由于这个“行为链”的存在而产生不仅仅局限在商业范畴内的影响,还有特定的社会效应和道德评价。显然,这些怪事不仅让一向口碑不错的南京人贻笑大方,而且不能不说很丢南京的份子,无异于自毁形象,自砸碑子,实乃商业之大忌,文明城市之大忌。
南京人,别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
南京扬州路 王学权
姓名重复的忧虑
编辑先生:我是贵刊的一名读者,最近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向你们提出来,看它们是不是有些典型性,值不值得呼吁一下。
我国目前姓氏重复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人名字在一个地区成百上千的拥有已不足为奇。据报载,天津叫李小刚的有9000人。在学校里一个班上有一二个同名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它们给工作、学习、生活引起的不便已有目共睹,它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些报刊还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避免使用频率极高的人名常用字,也许算是一条有效的办法。本着这个原则,我给我的小孩起了一个名字:郭冰琤。寓意是享有生命之水,心灵之玉。没想到里面一个“琤”字,给他引起了麻烦。这个麻烦是计算机引起的。因为里面没有这个字。照说这个“琤”字是我在最普通的《新华字典》里找到的,微机字库里应该能够收入,可是里面就是没有收入。而现在日常生活中,微机使用又很普遍,跟它的接触越来越多,麻烦也不断地出现。每当用微机造他名字的时候,“琤”这个字就是一个空档,要么打成“峥”“铮”或别的什么。我的孩子现在还小,想到他长大以后,“身份证”、“准考证”、“报销单”等各种档案文件也这般混乱,不但使我用心给他取的名字失去了意义,还会给他带来多少不便呵!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计算机的错?是我应该马上给孩子改名?还是计算机中文字库应该丰富和改进?我认为,不能让先进的设备变得这么简单和滞后。
避免姓名重复现象,进行姓名改革,需要全社会的齐抓共管。各个方面应该有所准备,为此创造一些良好的环境吧!
武汉税务局 郭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