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纯顺和探险精神四人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邱磊 吴胜钟 尚昌平 黄维群)

1955年5月6日,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胜利到达北极点。这是科考队员们用浮冰搭桥通过冰层裂缝
邱磊:原《中国旅游报》记者,摄影师
吴胜钟:中央电视台专题部记者
尚昌平:《中国青年报刊世界》记者
黄维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余纯顺给予了我们一种精神,但探险是不是冒险?
邱磊:余纯顺的遇难给我们带来钦佩伤悲之情,也引发我们思考:探险到底应该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好比登山是一种协作性很强的运动,登到峰顶的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为胜利者默默无闻地做后勤工作。成功的探险,往往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余纯顺这次徒步罗布泊,其实配备了质量很高的随行给养队伍,其中包括93年“保驾”中央联合探险队成功横穿“死亡之海”、号称为活地图的楼兰地质专家赵子允。大家都清楚,有赵子允“保驾”,穿越塔克拉玛干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余纯顺拒绝“保驾”,弃给养点食物不动,仅拿了两瓶水。一个成熟的探险家应当明白,在沙漠中放弃了水就等于放弃了生命。或许余纯顺如果当时很好地利用集体支持力量,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为,成熟的探险者不应该以激情代替理智,以情感代替科学。每一步都应伴以周密计划和科学态度。余纯顺要打破6月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是激情有余;缺乏缜密的日程安排,甚至全面的身体心理准备,多少又有些理智不足。
吴胜钟:余纯顺徒步罗布泊虽然是悲剧,但我以为应当鼓励,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精神。我们目前最缺乏一种理想主义——连宗教都只剩下财神了。而且余纯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实实在在、一步一步地在走,不像现在好多事情都有了替代品。我觉得探险这事儿,计划、理智、目的太多太明确就没劲了。现在大伙儿活得太在意了,没必要的珍惜和谨慎。像日本这样登山运动发达的国家,一方面是有钱撑腰(一根绳子就几千美金)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民族始终保持着那么一种精神。日本登山界有个最典型的品质,就是哪儿死人多往哪儿去——梅里雪山死了许多人,第二年就会有更多的登山队去那里。以雪山下埋葬的生命祭祀梅里,使得雪峰终于云开雾散。在世纪末的气氛中,是不是应该有些人站出来以他们的行为告诉大家:再勇敢些,我们还行。
邱磊:像探险这样一种高投入的行为,必然有很强的目的性。历史上很多探险家都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探险,比如斯坦因是为考古为挖宝。地理学家是为测绘。我以为当代的探险者可分两种,一种带有理性目的,比如徐利群考察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则是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寄托而只有在山川自然中才能找回自我的。相比之下,后一种人的探险感情因素更多些,有必要进行引导。这就涉及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中国目前缺乏一个组织、引导探险者的机构。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能量得以发挥,那些所谓“漫无目的”仅在“走一圈”的行为,我以为是一种对能量的浪费。
吴胜钟:你所说的科学态度可能是对职业探险家的要求,而我觉得余纯顺的探险行为更多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余纯顺曾对我讲过他在冬夜走在漠河雪原上的感觉,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有,而这种体验是都市生活不能满足我们的。我们不一定要培养那么多职业的探险家,但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有些向往,都肯拿出积蓄,勇敢地,到我们不熟悉的地方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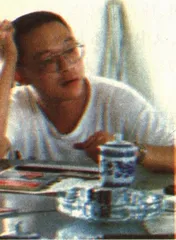
吴胜钟
从本真和寻梦到明确的目的性、功利性,余纯顺要想征服自然
尚昌平:7月15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余纯顺的摄影作品,朋友打电话来说规模是开馆以来最大的一次,很多郊县的人不辞辛苦都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参观。我却以为,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余纯顺同情,或者说,更多的是对他的经历和家境的同情。余纯顺6岁时母亲疯了,9岁时姐姐又疯了,老余从童年时起就生活在孤独和封闭之中。坐在屋顶上,遥望远天,他曾对我说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走向远方。1988年,妻离子夭,他在寻梦似的茫然中出走,而且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很不好。1994年我第一次和他通电话,连续3个小时,他要我节约电话费挂掉,我问他是以什么姿式和我说话的,他说是站着,因为他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铁柜子。后来,他订了80个探险计划,要考察56个民族。他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有益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名和利我都要。老余从1988年起徒步走中国,现在到了他探险计划的最后两年,他肯定希望有个漂亮的收场,这对他将来出书出画册都会有利。国内其它探险者从风光到落魄的前车之鉴也提醒他抓紧最后机会。我想,这也可能是老余打破原计划急不可待6月进入罗布泊的原因。
邱磊:余纯顺8年的探险生涯从最初的茫然出走到最后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我认为顺理成章,而且无可厚非。一个没有功利心的探险家,肯定是没出息的探险家。探险区别于一段旅游就在于它有功利色彩。这种功利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团或社会的。老余不是输在功利心,而是输在功利心冲晕了科学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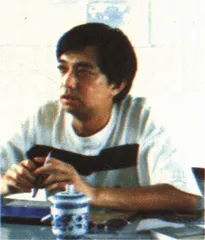
邱磊
尚昌平:他是很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1993年走青藏公路的时候,他突发了阑尾炎,仍然坚持不上车,一直忍痛走到医院。因为他知道,脚一离开大地就有一种虚假感。我个人很钦佩余纯顺的精神,余纯顺作为一个探险家的走和我的走,情况非常不一样,我1993年大学毕业后,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会一个人往外走,我没有任务和目的性,在走的过程中觉得视野越来越开阔,心情也越走越好。这几年,我不管走到哪儿,不论敲开那一家的门,他们不会问你是谁,来干什么,首先让你吃饱,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还总是说:吃饱不想家。记得我去宁夏的时候,到了一个很小的村子里,借住在一个当地农民家。他们家7个孩子,以7个小木头槽子当碗,每天吃的都千篇一律——土豆。我吃了20来天,体重减了好多。有一天男主人和女主人用当地话商量了好半天,第二天一大早男主人就挑着两筐土豆走了,第三天晚上背着一小袋米回来,给我蒸了一碗米饭。饭好的时候,我颤微微地端着,真想马上把一碗饭全吃下去,可7个孩子都爬了起来,我是含着泪把一碗米饭分到7个小槽子里。他们是那么朴实善良。
都说外面治安不好,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好像从来没碰着危险。就有一回,在四川大凉山,正走在半山腰上,一个人突然闪出来,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要我把钱拿出来。我当时非常怕,说钱全在上衣口袋里,还有像机,你都拿走吧。你要人吗?要的话,我可以到你家去给你做饭。说着就哭了,我盯着他的眼晴,因为我觉得很委屈,我说我走这么老远来,你们却用这种方式迎接我。他听了,拿钱的手开始哆嗦,后来把钱放回口袋,掉头就走。
我觉得,我是以一种争取接近自然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在广西时,我乘竹筏漂流。刚漂的时候,山清水秀,特别有诗意,后来突然变天,狂风暴雨,一个人在竹筏上变得非常恐怖,全身上下都被树枝划破,你会觉得在自然面前人实在非常渺小。人是无法征服自然的,可是余纯顺总有一种要征服自然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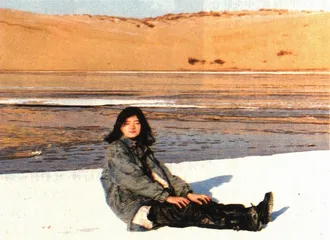
独走天下的尚昌平

1986年12月,中国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在征服长江时翻船落水的惊险场面
商业介入使探险的背景日益复杂,余纯顺太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了
邱磊:近几年探险热,据说像余纯顺这样的就有二三百人。我觉得这其中也有新闻媒介的“功劳”。媒介报道“曝炒”的后果很难料想。比如有关余纯顺的报道。《南方周末》曾引用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强荧的一句评价,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古典式的殉道者”。我怀疑这么炒下去,效尤纷纷,余肯定不是最后一位。
黄维群:而且我怀疑余纯顺事件作为纯粹的个人行为,如摆在整个社会坐标中,它的价值大吗?有些事情如没有媒介的一窝蜂似地爆炒,倒会更单纯更美好一些。我去年在青藏公路上碰到一位从北京跋涉到西藏的画家,他变卖家什出游,就是为了圆老师周游四方的梦,压根就没想到什么新闻什么报道。另有一点值得注意,探险报道多而滥,但大多囿于事件本身,精神方面的报道少而又少。
邱磊:许多记者抱着探秘心理,关心的是离奇事件中的离奇场景,从而粗糙地描述了这种场景。甚至夸张、杜撰、篡改的内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记者没能身临现场,难以关注到探险中那种真正值得关注的精神。
黄维群:即使是记者亲临现场,也往往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真正做为一个旁观者,客观真实冷静地报道。亲临现场的记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探险队的一员,那么探险的成败,探险深入程度就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荣辱得失,这样的记者就会关注自身报道的轰动性、日后影展的效果。
邱磊:记者的这种“晕”和媒介的“迷失”也有商业资本介入的“功劳”。外国很多大资本家都热衷于赞助探险,主要也是出于商业目的,比如黄金时间插播广告。媒介和赞助商的利益原则使探险和探险报道的背景越来越复杂——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也确实给探险者本身带来许多复杂的关系。
尚昌平:余纯顺这次走罗布泊,有外商给投资了20万人民币,上海电视台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次应该说是条件最好的一次。到最后,他似乎已经有一种预感,觉得这样走下去会使这次探险本身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所以他要摆脱掉记者,自己走一段。
邱磊:他太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了,为这个价值可以视生命而不顾。这种行为,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意志,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悲剧性的启示。
(刘天时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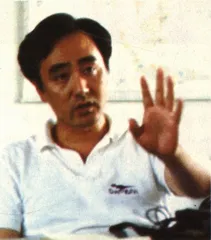
黄维群 黄维群邱磊余纯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