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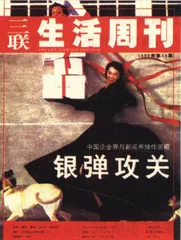
“有偿新闻”既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该深入追究它所生长的土壤。新闻界自然应该自律,但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当一切都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交易的时候,银弹攻关自然威力无比。
北京 王向荣
职称有必要再这样评吗?
《生活周刊》编辑部:
社会性的职称评定工作,在我国已搞了有十多年了。学历稍微高一点的或者与技术业务工作多少沾点边的人,都想弄顶职称的帽子戴戴。尽管所谓的职称已如BP机一样满街都是,谁也不会因为有个什么职称就受到别人的特别重视,但由于现在职称已与工资、住房乃至医疗保健、出差补贴都不可思议地联系到了一起,且又带有终身制的意味,一朝获得,持久享用,故而许多人还是愿意,至少也是不得不愿意沿着职称的台阶一级一级往上攀登。
据说我国现有的职称分为十多个系列,有近百种名称。除有教授、研究员及其代表的系列外,还有诸如译审、编审、研究馆员、高级经济师等让圈外人难以明了的种种称谓,甚至搞政工,搞商业,搞贸易的,也都有相应的职称。这真有点“泛职称化”的倾向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调查过目前这种评定职称的方式能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产生多少积极的推动作用。既然有专门的机构(职称办)和专门的人在年复一年地从事这项工作,归纳出一些重要意义,总不会是太困难的。然而当我看到那些已经出版过数本专著的中年人,为了谋求一个职称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而去死背外语单词;当我听说有些单位里朝夕相处的同事为了争得一个名额而明里暗里地斗来斗去;当我想到德高望重的评委们要面对着一堆表格来决定那些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前途时……,总觉得这出戏的舞台背景和演出效果,实在有些过于大了。我常常想,除了高校和科研单位,有必要在那么多的系统里开展那么多名称的职称评定工作吗?
社会性的职称评定工作,发轫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严格地说,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务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已相继出台,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技能考评方式都应该而且必将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变化。现行的职称评定方法,把本应由社会或业务单位解决的事情归由行政部门来承担,管理职责的错位,造成评审机制的僵化,这不仅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而且也增加了很多无效的劳动和无谓的纷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业务单位或者企业,似乎不需要由行政部门来为自己的干部和员工的技能一一进行评审并确定其相应的各种待遇。
以上是我看到周围一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称而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并不想做、对社会也不会带来什么贡献的事情之后所产生的一点想法。贵刊素以深入报道社会新闻和焦点问题见长,我非常希望看到《生活周刊》能刊载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以解我之疑惑。
北京西单 吴捷文
一场文化战争已拉开帷幕
编辑先生:
当前世界,以发展经济为载体,以文化渗透为手段,一场文化战争已悄然拉开帷幕,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把文化的入侵与反入侵说成文化战争,似乎有些故弄玄虚,可事实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二战后,美国靠着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支持,拼命地向全世界推行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可口可乐、麦当劳和肯德鸡。在好莱坞的抢滩下,当前美国影片已在世界电影市场上占了59%的份额,而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只守住了30%的份额。法国人一直以其文化高雅而自居,可架不住麦当劳在全法国已遍地开花,全法国已开了380多家,单巴黎地区就有120家。
西方有一位哲人早就说过,“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数年来,日美两国在汽车进出口问题上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就是以各自的文化输出作为前导。日商凭着其经济实力进军好莱坞,结果由于美国的反渗透,正面临分崩离析。韩国在限制日本方面,也颇有火药味。当前,韩国对除儿童动画片、教学录像带和传统日本艺术之外的日本文化产品采取禁止进口态度,但大量的日本影片、录像带、杂志、音带仍偷偷走私进口。另一方面,韩国已注意到日本儿童片进口已对韩国产生了文化入侵危机。韩国文化部统计说,在1993年获准发行的132盘儿童动画片中,62%是日本的,去年韩国出版的连环漫画书中,也有70%译自日本。儿童教育部发言人因此提醒说,“对少年儿童来说,看这些日本连环漫画是危险的,因为其中充满了暴力和性解放。”
应该说,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已是当前各国最关注的问题,许多先进国家都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不被外来文化吞噬或消灭。我们应对这场新的不见硝烟的战争有足够的警惕,希望贵刊能深入关注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
上海四平路 王战华
不可轻视的污染
《生活周刊》:
三四月间,南京各大医院收治了数十例儿童肿瘤病患者,在记者的话筒前,医生们作出的诊断书出乎600万南京人的意料:儿童患上肿瘤,与城市的空气、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最大的病因,在于环境污染。一位肿瘤专家的话更令人深思:“成人破坏了环境,报复落在了后代身上!是我们成人害了孩子!”
我又想到淮河污染问题,当淮河上游的污水下泄之后,下游沿岸数百万群众明知水中有毒也不得不饮用,成千上万的人患上肠道、皮肤和肝、伤寒等疾病,我猜想这几百万人口中的几十万儿童(至少有几十万)并没有生理上的特异功能,可以消除污水里的有机元素的戕害,相反,由于他们自身抵抗力的相对脆弱,他们肯定更容易患病,即使现在尚未发现,那么也只能说正处在潜在的威胁之中,也许在他们20岁、30岁、40岁的某个时候,就会发作,只是到那时已经找不到冤头债主了。
生老病死人之难免,倘若肿瘤长在大人身上,我们便不会诧异,正因为那种比肉硬比骨头软的劳什子长在了本不该长的孩子身上,才让人们有所警惕。其实,这种警惕我们早就该有的,多少年来,环境专家关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呐喊不绝于耳,只是我们不愿意听或假装没听见罢了;环境受破坏的恶果,我们也不是没看到过,只是我们总是闭上眼睛“让它不存在”或者压根儿不把它当回事,我们就这样一次次地放纵自己,欺骗自己。每念及此,一种对人类本身和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悲悯情绪便漫漶全身,不能自己。
电视画面里,患病的孩子像温驯可怜的羔羊偎在父母的怀里,懵懂无知的眼睛面对着摄像机镜头。经历了这一次人生劫难之后,他们或许对由父母、医生、家人、记者以及其他职业者所组成的成人世界还会多一份感恩,因为他们在患病时得到了成人社会的关爱和救助,但是,作为成人社会的一员,我却有一种异常真切的心虚感——那位肿瘤专家的话是对的:
“成人破坏了环境,报复落在了后代身上!是我们成人害了孩子!”
但愿每个成人都有这样的愧疚,并从自己做起,履行保护我们生存环境的责任。
南京扬州路 王学权
“安乐死”何时安乐
编辑先生:
“安乐死”作为一个争论热点在我国已持续了近十年。关于安乐死争论的焦点聚集在法学、道德评估、医疗观念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围绕这些人们见仁见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有人认为,人既无治愈希望又无价值地活着毫无意义,不实行安乐死,只能无端地增加患者及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和物质负担,也无谓地增加社会负担,实行安乐死,让家属得以解脱,于社会则终止了毫无意义的抢救治疗所造成的极大浪费。
但从法律角度讲,安乐死于法不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只要未犯死罪,就不该令其死亡;从道德角度讲,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为地结束患者的生命不符合保障人的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是极不人道的;从医学角度讲,碰到疑难杂症就放弃医疗上的努力与探索,既影响医疗技术的提高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也违背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从患者角度讲,实行安乐死即放弃了继续生存的机会,现实中不乏身患绝症却又起死回生的奇迹。
据对川东某地区从事各种职业近万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其中91%以上赞成安乐死,85%以上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近80%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川东某市医学院有人对92名临终病人的家属进行了调查,除6名没有明确表态外,其中56人对安乐死持赞同态度,占总人数的68%。
某重危病人说:“我卧床不起已久,跑了很多家医院都没用,自己痛苦不说,内疚的是单位白花了大量医药费,若是自费医疗,就是倾家荡产都不够,心痛的是连累子女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再这样下去子女也快累倒了。”
一位患者家属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对父母愿奉献孝心,但力不从心,服侍不好不说,主要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亲人被病魔折磨的样子,亲骨肉心连心啊,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一位医生说:“癌症晚期的‘恶病质’使病人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们不得不承受难以忍耐的剧痛,所有的止痛药在肆虐的癌症面前都显得势单力薄,时常听到阵阵痛苦不堪的呻吟,令人心惊胆寒,真是活受罪!”
据一家医院对患癌症或老年病的800例患者的调查统计,不堪忍受痛苦而要求死亡者高达30%,有的人求死不能便采取跳楼,自缢或服药等惨不忍睹的方法。
作为一位临床医师,我认为,实施安乐死的前提必须是出于患者本人的真正要求,认定患者的意愿是否真诚,可参照我国遗嘱的有关法律,患者必须是在不受任何限制和干扰的前提下,按自己的意愿,清楚地、反复提出这一要求,即以法定的形式作为其意思表达合法化的根据。任何隐瞒真实病情,诱使患者错误请求,以及运用种种手段软硬兼施,胁迫患者安乐死的做法都是违法的。其次,实施时间必须是患者自患绝症的最后日期,这里的条件:一是绝症,即现代医学认为不可救药,现有医疗技术无法治愈;二是痛苦难忍,在患有不治之症的同时须伴有严重的、持续的、无法忍受的痛苦;三是最后期限,即应是绝症晚期、濒临死亡的时期,不能在病发初期和中期施行。
总之,目前无论是于国家、社会、患者、家属或者是医生而言,安乐死都具有其立法意义,可见我国已到了面对现实,考虑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时候了!
四川达川 欧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