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让人脸红又脸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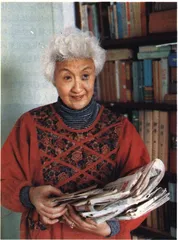
著名作家黄宗英,她60年代开始创作时稿酬标准每千字10元(杨飞 摄)文稿成了商品
几年前,一位记者给我算过一笔帐:只要一篇文章的稿酬,能与采访时打车请饭的花销持平,就心理平衡了。那年月,稿酬每千字30元,低了。
如今,这位记者已成名记者,他说:“如果千字挣不到300元,就算白忙活。”这位记者也坦言,如此高的要价,吓退不少约稿人。这位记者现在已拥有私车,他碰到税务局的朋友说,车是凭稿酬挣来的,人家不信。
今年1月,国家税务局召开一次内部会议,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对文人稿酬征缴个人所得税,争论一上午没个结果。不是没有办法,只因有一道坎儿,国税局迈不过去。目前通行的做法是约稿单位代扣代缴,可是税务局无法稽查,文章字数明摆着,可稿酬标准却是混乱的,不是几乘几就能算出来的。如此这般,抽查什么?全凭自觉吧。这年头什么都在变
这年头什么都在变。千字30元、40元,多年来一直是各家报社、出版社延用的稿费标准,可如今一些记者、作家的稿费早已突破这个界限,稿酬标准越涨越高,价码已随行就市,文稿已成为一种商品可以待价而沽。
目前新闻界稿费的行情大体是这样的:一般记者、作者采写的报道可能获得千字60—100元稿酬;较有名气的记者、作者可获得千字300—400元左右稿酬,有时可以达到1个字1元钱;而针对一些独家新闻、特别报道,报社有可能出重金买断,稿酬数以千计、万计。
因此,有了好稿子,就有了讨价还价的可能,稿酬高低和该新闻单位影响力大小已成为作者并重考虑的两个因素。南方一家大报编辑说:“我组稿时第一句话就是:‘给我写稿吧,给你千字x百。”’
与此同时,各报刊竞价也十分激烈。一位北京记者采写的一篇万余字的报道在本报难以发表,南方一家报社当即表示出5000元买下,香港一杂志闻讯立刻开价1万元港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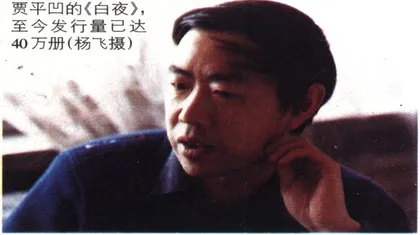 在出版界,作家对稿酬的选择性更强。贾平凹的《白夜》脱稿后,一家老牌出版社许以保底印数5万册索稿,而一家新兴出版社则开出10%的高版税率,最终贾平凹将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至今发行量已达40万册。
在出版界,作家对稿酬的选择性更强。贾平凹的《白夜》脱稿后,一家老牌出版社许以保底印数5万册索稿,而一家新兴出版社则开出10%的高版税率,最终贾平凹将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至今发行量已达40万册。
现在的作家不仅能判断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能清楚意识到自己作品蕴含的经济价值。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国内一度畅销,1987年以来译者一直拿千字20—30元的翻译稿酬,然而三四年后译者提出将翻译稿酬改为版税制,也就是说,每发行一本,就多拿一本的翻译费。
50年代,人们生活水准普遍都低。1个局级干部最多1个月也就拿200多元,有一定稿费收入的人就很知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老先生说:“我念大学时写的1篇豆腐块发表了,得了5块钱稿费,立刻请全宿舍同学吃西瓜。5块钱买了好多好多西瓜。”
那年月,一谈到钱还会遭殃。丁玲曾因“一本书主义”而被树为个人主义的典型受到批评。因为她声称:每年都要写一本书,挣一本书的钱。
如今人们的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文人由于身价不同导致稿费高低不同,标准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稿酬标准源于列宁
谈起稿酬标准制定,一位老出版家深有感触地说:“制定统一标准是一件相当繁琐艰难的工作,许多出版家耗费了大量心血。”
建国初期,没有现成的稿费标准可以使用。解放前国统区的做法一是抽版税,二是卖稿子。当时的稿酬相当低,书价却很高,被人称为“红烧读者肉,清炖作家脑。”在延安、山东、华北晋察冀解放区的新闻出版单位基本无稿费。干部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一位老革命家清楚地记得他给广播站一次投稿的报酬是一碗羊杂碎汤。那时的作品也大多是翻译马列主义著作,新闻出版业远未成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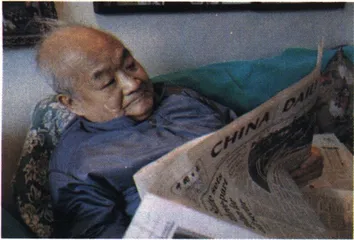 因而要不要给稿费在建国后还存在颇多看法。当时的作家大都有固定工作单位,有人说,同样是国家干部,都一天上班8小时,作家除拿工资外,凭什么还给自己挣钱?经过反复研究,列宁的一句话成为确立稿酬标准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要比工人生活得好一点。
因而要不要给稿费在建国后还存在颇多看法。当时的作家大都有固定工作单位,有人说,同样是国家干部,都一天上班8小时,作家除拿工资外,凭什么还给自己挣钱?经过反复研究,列宁的一句话成为确立稿酬标准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要比工人生活得好一点。
1950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形成向前苏联借鉴后的稿酬标准,即印数定额制。将作品的性质、质量、字数、印数与著作人报酬结合起来。学术著作,国家规定原则上印数1万册为一个定额,如1册10万字,作家稿酬按千字10元计算,应得1000元。也就是说,每次印数达到1万册,作者就拿1000元稿费。文学作品是3万册为一个定额,也就是说,每次印数达到3万册,才拿一笔稿费。通俗读物则是5万册才是一个定额。这样使得既获得稿费又不致拿得太多,具体多少册为一个定额由出版社灵活掌握。
定额制取代版税制,改变了一些私营出版社出书只顾利润、不顾质量的状况,体现了对学术著作的尊重和照顾,平衡了各方面收入差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
然而此办法操作起来却有相当难度。印数定额极难掌握,出版社在制定定额时往往高也不是、低也不是,左右为难,索性取个中间,皆大欢喜,反而助长了平均主义。与此同时,一些受时代影响巨大的书籍如《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销量惊人。一位老编辑说:“当时走红的作家都有买房子的。”饿的饿瘪、胀的胀昏,定额制难以维持。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1958年文化部出版局决定制定统一的稿酬办法,即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相结合,此办法一直延用至今。作者除获得千字付酬之外,每重印1万还可获得基本稿酬总额的8%。适用范围固定在文学类和社科类书籍,自然科学除外。老出版家王仿子说:“如果都放在一起,1958年也制不下来。“当时力求稿酬的标准能使作家的生活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在物价平稳的情况下,大家都比较满意。可以说,在同类干部中,作家的收入是最好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十年内乱一开始,稿费取消。
“文革”结束后,稿酬制度恢复,但又把印数稿酬改为以万册为计算单位,这样一来,学术著作重印再版获得稿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991年《版权法》施行,允许各出版社可以和作者自行签约付酬。新闻出版署后来又制定了一个最低限,千字不得低于10元。至此,稿酬标准完全放开。
如今的出版社都采用两种办法付酬,一种是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一种是版税制。版税制调动了出版社和作者的积极性,但由此也引发出方方面面的问题。书籍是商品,可又不是一般的商品,出版社是企业,可又不同于其它企业。新闻出版署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原想把文学、音乐、美术等作品放在一起搞一套统一的标准,可现在根本没这个信心。”高稿酬造就自由人
稿酬标准放开使文化人身价客观增长了,但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标准提高总趋势却不是随质量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年度随物价看涨。它最直接引发的是产生了一大批以稿酬维生的文化人。
对于大多数撰稿人来说,他们生活可能是相当清苦和忙碌的。彭先生是一位热衷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在广州打工4年,还是醉心于写作。如今,他独居在北京圆明园南侧,每月花150元租了一间小屋潜心创作,给一些报纸杂志写散文随笔,靠每月几百元稿费维持生活。熟识他的编辑说:“他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稿子发了吗?第二句话就是稿费呢?”
彭的小屋简陋、静谧,没有电视机、收音机。彭先生打算找一份工作支撑生活,他期待有一天能写出一部旷世之作。
也有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成为文化圈里的“腕”级人物,甚至已成为百万富翁。陈先生被誉为影视圈里第一“写手”。他早先是一家地方报刊编辑,后辞去公职,以专业采写娱乐新闻赚取稿费为生。陈先生说:“当时人们最关心影视圈,要生存就要瞄准市场,我要是恐龙,早就灭绝了。”
陈先生非常勤奋、努力,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从不肯浪费每一个采访机会。他说:“我的每一分钟都要靠钱来计算。”如今他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拥有自己的电脑、传真机,但他对自己的未来仍充满紧迫感。他说:“以后向哪个方向发展还是要看市场需求。”
有了自由的文化人,就有了自由的文化经纪人。一位作家出名后就当了文化经纪人,他一次性买断作家,再高价卖给出版社。但由于不熟悉出版业,他的要价往往使出版社知难而退,令作家作品难以面世,知名度下降。
据了解,国外的文化经纪人的素质是相当高的,他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鉴别力和很强的经济头脑。在美国,文化经纪人的收入仅次于医生,他的收入来源是靠和作家分享版税提成,因而作家作品的收入就是文化经济人的生命线。
目前,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也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很多撰稿人不是靠作品的质量取胜,而是靠写一本又一本质量低劣、制作粗糙、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书赚取稿费。同时,对大多数报刊杂志来说,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最让编辑犯难,有一些作者为谋取私利不惜剽窃他人作品或生编硬造。令编辑头疼的还有撰稿人大量“一稿多投”的现象,叫人无从判定手头的稿子到底有多大价值。
实际上,“一稿多投”是所有自由撰稿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陈先生每天就给全国200多家报刊投相同的稿件。彭先生每一篇稿子都发表过2—3遍。他们问:“新华社能发通稿,我为什么不能?”
从目前通行的稿酬标准来看,每篇稿件发表一次,所获一笔稿酬实在难以抵消一个严肃作者为此所付出的艰辛。一位记者算过这样一笔帐:“每采写1000字大约需要3天的劳动时间,如果打算成就一篇精品文,加上构思及背景资料搜集,约需要一周。如果按千字100元算,每月只获得400元,也就仅够维持交通费用。”
因而,要获得较多收入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稿子搀水,二是一稿多投,目前现状是,作者出于名誉角度考虑,稿子搀水还不致于急剧膨胀,而地方性报刊稿费高,作者完全可以在不同区域提高知名度。一稿多投可以名利双收。
因而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按现在通行的稿费办法,报社获得的只是发表权,付给我的只是发表费,如果要获得版权,就应重金买断。名与利谁主沉浮
稿酬高低的反差使更多的作者渴望获得满意的收入,但这一愿望实现的前提是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于报刊杂志来说,发行量越大,广告收入就越多,经济实力越强,支付稿酬越高才能吸引更多的好稿。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机制原因使很多报社、杂志社远未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一家中央级大报头版头条的稿酬标准才千字50元,如此低廉的稿费难以吸引更多的作者。这家报社的编辑们觉得近两年作者来稿的质量越来越差,挑不出什么好稿子。而且,由于本报稿酬过低,记者还会给外报写稿,出现本报记者不给本报写稿的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机制灵活的地方报、行业报却越办越火爆,发行数量、广告数量与日俱增,势头直逼同类大报。从去年11月至今年初,《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首次以公开标价形式向社会征集稿件。形式是由编辑命题、读者采写,稿酬定在干字300元—450元不等。活动开展以来,每一个题目都几乎收到数十篇稿件,超过历次征文数量,使编辑们尽情地优中选优。在这批作者队伍中,有相当一批是外报专职记者。北青报总编辑肖培说:“新闻资源是开放的,整个稿源市场是开放的,那么我们的作者队伍也应该是开放的。它将导致稿源的合理化流动、配置。越有影响力、有经济实力的媒体就越具竞争力。”
对于出版社和作家来说,采用版税制对双方都有利。版税制的计酬方式是:图书定价×图书发行数×版税率。由此可以看出图书发行数和作者所获得稿酬收入有密切联系。
采用版税制从理论上讲,一本书销量越大,出版社和作者也就获利越多,而我国出版和发行历来是两条腿走路,出版和发行彻底分家是从1950年开始,当时出发点是基于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是为了“消除出版发行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为人民供给所需的各种出版物。”从那时起,出版社只管出版,新华书店只管发行。至今出版界流传的一句话是:全国只有两个系统是完全直属单位,一个是铁路,只要是铁路,一定归铁道部管,一个是书店,只要是新华书店,一定归总店管。
出版与发行的分工,使得出版社迅猛发展,使中央各部门的专业出版社纷纷建立,建国初期北京只有10多家出版社,全国1年出书1万多种,至今北京中央级出版社就有近220家,1994年出书60亿册。众多的图书品种和庞大的发行量,已经超越了单一发行渠道所能承受的限度。
发行统得过死影响了出版社的活力,束缚了它的发展。80年代,国家出版局发文允许出版社自办发行,补充书店发行力量的不足。从那时起到现在,出版社“二渠道”发行量越来越大。起初“二渠道”发行和新华书店发行量约占30%和70%,现在是倒过来。
是企业,就必然存在盈利目的,相当多的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市场,多出畅销书、热门书、高档书,版税制应运而生。一些历史短、地方性强和专业性强的出版社更是以高版税率吸引名作家和名作品。在作者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要稿酬,找地方;要影响,找中央。
前一段,很多出版社采取了出书利润和奖金挂钩的办法。如初级职称编辑,每年完成毛利润6万元,中级职称编辑每年完成7万元,副高级职称编辑8万元,正高级职称编辑9万元。超额部分按8%提成。这样一来,编辑们从原来的只关心书稿,转化为对一本书选题、策划、构思、包装、文字、印制、推销全方位的关注,争取书一出就立刻产生轰动效应。华夏出版社一位老编辑说:“我现在一半是编辑、一半是商人,有一半目的是为了赚钱。”
这种向市场化商业化靠拢的举措,激活了一些出版社经营的活力,但也导致了一些出版社因盲目追求利润而放任媚俗、格调低下的读物出现,而把一些真正有价值而销量不大的学术书籍拒之门外。当然,时下已有越来越多成熟的出版社认为,盲目追求利润,不顾产品品质,最终肯定是一种自杀行为。一位老资格的出版社领导说:“出版社最终是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一原则应贯穿出书始终。出版格调低下的东西最终会砸自己的牌子。”
据了解,西方国家出版学术著作是不付稿酬的,学者在确定研究意向后,实行“匿名审查制度”,隐去作者姓名,将可行性计划书提交同样不具名的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由专门的学术慈善机构提供资金,一般都由能够获得补贴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印数少,但制作精良,书价高昂。
我们的现实是:出版社要利润,文人需要好收益,但两者利益的最终实现只有一个,文稿必须是社会公认的精品。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均衡。 作家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