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印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廖一梅

《理智与情感》 《理查德三世》《太阳有耳》
今年的柏林白雪飘飞,异乎寻常的寒冷。而每年一度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依然保持着它的热烈氛围与高度热情。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部影片同时在数十家影院全天放映。记者和观众们每天奔忙于影院之间,每家影院门口几乎都排着购票的长龙,即使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导演的名不见经传的影片也是观者如潮。柏林人对电影、对艺术的热忱一向闻名于世。
一走近电影节中心座落的库荡(音译)大街。满眼便充斥着巨大的电影海报,几乎全部是参展的美国电影与德国电影。据说,美国的几大电影公司买断了主要街区和会场的海报张贴权,别的影片根本无法插足其中为自己宣传,显示出财大气粗的美国电影雄霸欧洲与世界影坛的野心。这一次,他们一连抛出了《理智与情感》(李安导演)、《尼克松》(奥立佛·斯通导演)、《假日该回家了》(朱迪·福斯特导演)等多部影片,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以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理智与情感》夺得金熊大奖。(李安成为柏林电影节46年历史上两次获得此项荣誉的第一人。3年前,他执导的《喜宴》曾获此项奖。)虽然对此结果,有些人士表示不满,认为此项奖本应授予一部不太为人所知的影片,而《情》一片已获得美金球奖及奥斯卡奖的多项提名。但评审团主席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解释说:“我知道,我们无法使每一个人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的决定是一致的,我希望你们的不满不久将过去。”李安的成功,会使华裔及外籍影人在好莱坞受到更大的重视,这一定也使作为这一届电影节评委之一的陈冲感到欣喜。
虽然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获奖有此不满,但观众对美国电影的钟爱和普遍关注显而易见。我去观看一部仅是参加电影节的另一系列Panorama展映的美国片《眼对眼》(Eve for an Eve)时,畅通无阻的电影节记者证竟然受阻。因观众太多,只允许13名记者入场。不知是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亚洲人的关照,我侥幸混入。影片由美国女明星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主演。像许多典型的好莱坞电影一样,结构完整、细节丰富、情节紧凑、人物心理细腻入微,但总的来说,毫无新意与独创性可言。好莱坞电影的这些特征,甚至也体现在一部迪斯尼耗费巨资拍摄的卡通片《玩具故事》中,这是我在电影节中看到的最为轻松愉快,充满人情味的电影,赢得的掌声甚至比许多获大奖的影片还热烈。 美国老牌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 Stone)导演,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lcins)主演的影片《尼克松》(Nixon),追述了尼克松总统的一生,与斯通以往的影片《生于7月4日》、《肯尼迪》等相似,充满说教与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反思。形式上延用了一些他上部引起轰动的影片《天生杀人犯》的速剪及黑白彩色混用的技巧,制作精良,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各。此次只是参展,并不参赛。我因为有语言障碍,不能充分理解影片的内涵,看得有些无聊,记起《北京杂种》的编剧唐大年说过“斯通是美国的团委书记”,甚觉有理。
美国老牌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 Stone)导演,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lcins)主演的影片《尼克松》(Nixon),追述了尼克松总统的一生,与斯通以往的影片《生于7月4日》、《肯尼迪》等相似,充满说教与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反思。形式上延用了一些他上部引起轰动的影片《天生杀人犯》的速剪及黑白彩色混用的技巧,制作精良,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各。此次只是参展,并不参赛。我因为有语言障碍,不能充分理解影片的内涵,看得有些无聊,记起《北京杂种》的编剧唐大年说过“斯通是美国的团委书记”,甚觉有理。
唯一能在舆论宣传上与美国抗衡的是德国电影。这一次首推的王牌是德国与瑞士合拍的影片《寂静的夜晚》(Slient Night)。满街皆可见到那张女人腹部特写的招贴,但此片只与另外两部电影(何平的《日光峡谷》、杨德昌的《麻将》)一起获得特别提名奖。宣读此奖时,新闻发布会上还响起不满的嘘声。我因为迟到两天,未能看到该片,但据一位在德研究电影的同行讲,确实太过沉闷,这大概与德国总是阴沉沉的天气不无关系。
中国电影与柏林电影节的渊源颇深。自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梁》一举夺得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频频在这里展露锋芒,《本命年》、《晚钟》、《香魂女》、《红粉》等等,柏林的狗熊仿佛十分偏爱风格独特的中国电影。今年,由张瑜投资、主演,严浩执导的《太阳有耳》以及何平执导的《日光峡谷》经过与240部影片的角逐,入围参赛并最终不负众望。严浩获得最佳导演银熊奖。何平的《日光峡谷》与台湾导演杨德昌的《麻将》一起,获得特别提名奖。(据悉,此项奖说明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偏爱。)
虽然很为中国电影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凭心而论,我更加欣赏杨德昌的《麻将》。因为中国电影没有令我有耳目一新之感。《日光峡谷》依然是中国西部片风格的文化武侠片,虽然很不错,但与何平自《双旗镇刀客》以来的电影风格相比变化不大。而《太阳有耳》描写了一位20年代的美丽村妇在军阀混战时代的遭遇,张瑜扮演的油油被无能的丈夫送给一位当地的土匪头子,与其发生了爱情,最后大义灭亲。此类情节,我在多部小说中都曾读到(当然对欧洲观众来说十分新鲜陌生)。也许是莫言编剧的原因,影片格调与《红高粱》同出一格,还缺少了一份质朴的力度,许多地方有矫揉造作之感。赵非(《大红灯笼高高挂》主摄)的摄影我也不喜欢,说他一向以善于布光著称,但片中几乎每一个有灯光效果的镜头都放烟,经常黑地里毫无来由地亮起一束蓝光,太过生硬。当然,严浩作为香港资深导演,处理上有其独道之处,但总的来说没有创见。比较之下,我更欣赏他的旧作《似水流年》的自然、清新。或者,也许是我对《太阳有耳》这种风格题材的影片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免有失公允。但看来,柏林电影节确实对此种类型的中国电影有所偏爱,而欧洲人对那些离他们十分遥远的氛围与遭遇中的中国人更感兴趣。
台湾导演杨德昌的《麻将》描写了城市中4个渴望成熟长大,渴望掌握世界的少年的心路历程、感情世界与最后的幻灭;充满了现代都市的混乱与骚动,置身其中的人们的麻木不仁、随波逐流,以及痛苦绝望,最后在残酷的幻灭后留给观众一点温情的希望。这是整个电影节中最令我动容的一部电影。
柏林电影节除了正式的参展参赛影片,还有另外几部分的展映。最主要的是Forum(可译作“论坛”、“新生论坛”或“青年论坛”)和Panorama(可译作“电影全貌”或“电影之窗”)。入选Forum展映的是各种新人新作,或有争议性有独到之处的电影,Panorama则是各类电影的荟萃。
今年参加Forum展映的一部中国影片是由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章明执导的《巫山云雨》。影片结构及风格独特,悠缓冷静,略带人情味地讲述了巫山小城里几个普通人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得到了评论的肯定和好评。这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影片由一直提携年轻人的田壮壮帮助,获得北影厂的支持,得以送往柏林。
还有一部我不得不提起的电影,它完全可以说是我这些年看到的最差劲的电影之一——由张旗和崔燕执导的影片《落鸟》(英文名(Chinesl Chocolate)。我很为我自己没能当面这么告诉两位导演感到遗憾。由于这对连演带导的夫妻已定居加拿大,此片作为加拿大电影参加Panorama的展映。该片讲述了两个到加拿大后的中国女人的坎坷经历,基本可以说是与各种各样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经历。我并不是道学家,获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奖的阿努克·格林贝格(Anouk Grinberg)在法国影片《我的男人》(Mon Homme)中饰演妓女,片中由始至终充满了更为暴露、直接的性场面,但表演细腻,视角独特,引人思考人类的真正需求。而《落鸟》那种拼命想暴露的遮遮掩掩,拼命想开放的假模假式令人难以忍受。此片令许多中国留学生愤慨不已,在讨论会上当面谴斥它的不真实败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我想“不真实”不能作为评论一部电影的真正标准,但就这部电影本身而言,毫无影片的内在逻辑与细节可言,人物更是莫名其妙,却还要故作深沉。我所看的是此影片放映的最后一场,因为前两场已引来议论纷纷,所以观众如潮。结束时却基本没有掌声(德国人是很有礼貌的)。一位华裔德国人用德语骂了一句:“Scheisse Flim!”可以译为“狗屎电影”(德语没有脏话)。但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此片竞获得了Panorama评委会给予的据称最好发行的艺术片奖,因为它“敏感而勇敢地讲述了两个中国女人在异邦的经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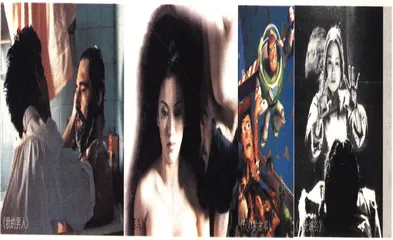 另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电影,据称获得特别评委会银熊奖的《美好的青春》(瑞典、丹麦合拍),非常优美动人,当时夺魁呼声最高。它描写了一位少年与他的女老师的爱情。影片的导演、演员由一个家庭组成,父亲是导演,儿子和他的继母饰演男女主角。颁奖典礼上,当该片导演走上领奖台时,全场响起了最为热烈的掌声。肖恩·佩恩(Sean Penn)因在美国影片《行走的死囚》(Dead Man Walking)中扮演死囚获得最佳男演员银熊奖。与导演《太阳有耳》的严浩分享最佳导演奖的是导演《理查德三世》(RichardⅢ)的理查德·朗克兰(Richard Loncraine)。执导《神圣的一周》(The Holy Week)的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Andrzei Wajda)因他终身对“电影艺术所做的贡献”也获得了一尊银熊。
另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电影,据称获得特别评委会银熊奖的《美好的青春》(瑞典、丹麦合拍),非常优美动人,当时夺魁呼声最高。它描写了一位少年与他的女老师的爱情。影片的导演、演员由一个家庭组成,父亲是导演,儿子和他的继母饰演男女主角。颁奖典礼上,当该片导演走上领奖台时,全场响起了最为热烈的掌声。肖恩·佩恩(Sean Penn)因在美国影片《行走的死囚》(Dead Man Walking)中扮演死囚获得最佳男演员银熊奖。与导演《太阳有耳》的严浩分享最佳导演奖的是导演《理查德三世》(RichardⅢ)的理查德·朗克兰(Richard Loncraine)。执导《神圣的一周》(The Holy Week)的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Andrzei Wajda)因他终身对“电影艺术所做的贡献”也获得了一尊银熊。
电影节2月15日开幕,26日结束。尽管德国人生性严肃,在最后的颁奖典礼上还是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当《理智与情感》的制片人上台领完金熊,把它交回给一位评委暂拿,到麦克风前讲话时,那群穿着礼服、德高望重的评委们,把那只金熊从台中央偷偷由背后传到了台侧,使致完谢辞的制片人一时找不到了他的宝贝熊。我用傻瓜机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
还有两件遗憾的事,据说黄建新的新片《打轮,向右转》的拷贝在运往柏林审片途中丢失,因此耽误了时间,未能及时使评委们看到。而叶大鹰执导的《红樱桃》参加Panorama的展映,第一次放映时拷贝不慎被毁,未能在电影节结束的前一天重映,使许多观众失望而回。
在柏林耽搁了几天,回到北京时,报纸纷纷登出柏林电影节的种种评论和消息。我想,无论对影片,还是对其它的艺术,都没有唯一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所说的只是我所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 柏林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