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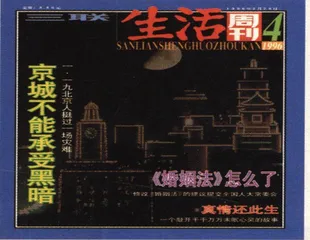
一辆吊车偶然撞断高压输电线,导致半个北京城停电,全部恢复供电用了两个半小时,可见我们的城市应急能力水平太低。“1·19”没发生骚乱及伤亡,仰仗的是老百姓的觉悟,但有关方面有何措施使“1·19”不再重演呢?
北京 李广志
净化风气刻不容缓
编辑先生:
朋友的孩子从幼儿园回来,给妈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幼儿园的老师对小朋友们说:小朋友们,春节快到了,你们部给老师准备什么礼物啦?小朋友们纷纷把爸爸妈妈精心为老师准备的礼物拿了出来。一个小男孩把自己画的一张画作为礼物送给了老师。回到家后,小男孩哭丧着脸对爸爸妈妈说:别的小朋友都有高级的礼物送给老师,只有我的礼物不如他们的高级,老师以后就不喜欢我了。爸爸妈妈一听,哪有不心疼的,忙拿出一个100元的红包,对孩子说:没关系,去把这个送给老师,老师就高兴了。
像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着,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教育的真谛在于心灵的触动,精神的提升,这绝不是靠“拉拢感情”的“智力投资”所能完成的。如果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和含辛茹苦的园丁都有意无意地给吃喝风送礼风赌博风推波助澜的话,怎么能够指望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心地正直、目标高尚、品格坚毅,具有真才实学的英才和栋梁呢?不管一个幼儿艺术团的小明星有多少,不管一个学校的升学率有多高,如果忽视了“做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是违背了教育的初衷的。一种违背了教育初衷的教育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是不言自明的吧。
零点公司做过一项调查,子女教育问题是目前北京市民关心的首要问题。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冲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基础教育的各个环节:小学,中学,甚至幼儿园,都不能免于不良风气的侵害。净化社会风气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希望贵刊能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我们共同的人文环境,为子将来,救救孩子!
北京 燕于飞
懒得拜年
编辑同志:
今年在北京过年,只觉得出奇地安静。大年三十晚上,从楼上阳台望下去,马路上空空荡荡,很少见到行人。初一初二两天,出门的人也少。往年,大家都要串串门,拜个年,今年上门拜年的似乎也越来越少,除非非要上门,一般都是打个电话,更方便的,通过BP机拜一拜算完完。
贵刊曾发表关于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自己的节的讨论,对自己节日的寻找有一定道理,但细想一想,没有了过去那种热闹,平平常常、平平静静地过年也并非不是好事。辛苦了一年,过年成为一种阶段性的休息,大家在宁静中睡睡懒觉,松松筋骨,也为过了年更好地进入新的一年的劳作。
人免不了都要寻找记忆中过节那种热闹与红火,但那毕竟已成为过去。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人们传达情感的方式其实都在变化,生活的意味其实是在这变化之中,而不应停留在对翻过去的一页的玩味上。《生活周刊》应该寻找这种正在变化中的感觉。
北京 陈志强
无谓的人情游戏
编辑先生:
春节一过,压岁钱又成了热门话题,压岁钱名为给小孩压岁,实则是大人之间一种无谓的人情游戏:你给我给大家给,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就得给你(的孩子)多少。给的和得的,甜酸苦辣滋味各异。
邻居两口子是“丁克家庭”,平时日子还算宽裕,可一到过年就暗自叫苦,自称是压岁钱文化的受害者,哥哥姐姐都有孩子,这几份压岁钱是绝对不能省的。过年期间亲友来往不断,都带着孩子来拜年,小孩叫一声就得给一份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一年的奖金全捐给了“希望工程”。两口子说得幽默:平时过得挺滋润,过年方知没儿苦,别人好歹弄个收支相抵,只有我们光出不入。
不过最苦的还是那些爷爷奶奶们,有的老人儿孙众多,平时从微薄的退休金中省吃俭用“抠”出来的钱,全拿出来也不够给孙儿孙女们每人一份压岁钱。没得到钱的晚辈心怀不满,老人无奈不得不借钱补上,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孙儿嫌靠糊纸盒为生的奶奶给的20块钱压岁太少而摔脸子,奶奶被孙儿当着众亲友的面披头盖脸一顿数落,亲生儿子在旁不闻不问,奶奶一气之下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经医院抢救2个多小时才脱离生命危险,真是乐了孩子,苦了老人。
近年来,压岁钱行情看涨,50元拿不出手,一二百元才勉强“不跌面儿”,听说有些地方一个班的小学生春节得的压岁钱达数万元之多,人均1000元。行情涨到这种地步,这压岁钱实在也成了一种社会问题。
我认为,压岁钱这种贺岁方式也应作一些改革,应该提倡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简单、健康的贺年方式,比如送些可以启迪孩子心智的小礼物或学习用品,说上几句勉励的话等等,能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北京 萧怡
生活的感觉不那么简单
《生活周刊》编辑:
年前去北京出差,照例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社科书店、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逛了一圈,最后跑到了三联,朝内大街166号,到那儿一楞,三联没了,赶忙打听,才在人民出版社的门市部里找到了三联的几个书架,临出门时,发现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大致一翻,便觉很对品味,又问管开票的一位女士是否可以代订,答曰办不了,让我到楼里的三联邮购部问问。邮购部的女士又指点我直接找净土胡同15号。没时间了,得赶火车,我又折回书店,嚅嚅地问管开票的那位女士可否把杂志里夹的那页订单给我,她很爽快,“您拿去吧!”,心里一阵欢喜,小心地把订单折好,忙着赶奔火车站而去。
坐在火车上,倒有一丝歉意,心想被我拿走订单的那本杂志,若被哪位小姐先生买了去,发见少了那么一点,岂不……回来后,立马将订单填好,算出七折的钱数,跑到邮局如数寄出,心里踏实了,只等着她了。
三联的《读书》杂志我已经订了五、六年了,以前在学校里就常看。三联出的书也十分耐读,像罗伯特·路戚(Robert H Lowie)的《文明与野蛮》,杨绛的《洗澡》等等。这本生活周刊又是另一番品味,首先这装帧,这印刷、版式,看上去已具备了生活周刊的意思。几天前,我订的杂志终于寄来了,1─3期,读完以后,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联的风格。
然而略微回味一下,却又觉得留在记忆里的怎么大半都是些沉甸甸的感觉。比如戮杀动物啦,AIDS啦,沙暴啦,失业啦,通货膨胀啦,腐败啦,尤其是那幅拄着双拐的波黑儿童的背影(96年2期P6),让我的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痛。
生活周刊的感觉通过57克的进口轻涂纸、精致的图片或许不难找到,然而生活的感觉就不那么简单。
太原 段永朝
回家过年行路难
编辑同志,您好!
今提笔给你们写信,是想谈谈回家过年行路难的感受。2月17日廿九那天我掐着差10分钟就要开车的点,勿勿来到北京西客站候车室。没成想,也许是沾上了闰年不顺的晦气,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由于大雪封路,好几趟列车全都晚点。晚点多少时辰,车站服务员答曰:不得而知。三四个小时过去后,急于要回家过年的旅客几次三番寻问,得到的回答仍旧是不知道。无奈,我只能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告诉他们不要接站了,可号称亚洲最大的北京西客站,竟然连一部长途电话也没有,有限的几台市内电话旁也都挤满了人。这还不算,软席候车室里的空调也将冷气当热气给开了,服务员又不知如何转换,候车旅客的处境可想而知。真是一流的硬件、最差的服务。问题不在于列车晚不晚点,而在于你服务到位不到位。但我总算还是幸运的,尽管列车晚点39个小时,总还在年三十前赶回了家。而另一些车次的旅客因为晚点推迟乘车时间,有的则在列车上渡过了除夕。
可这还并不是行路难的终点,大年过后,去邯郸火车站买返京的车票,早晨6点钟去排队才开上一张卧铺票单,凭着票单去另外一窗口取票,又是寸步难进,原因是熟人、警察全在前面充当了夹塞的角色。第2天上车之后,我又发现,这卧铺车厢已挤满了没有卧铺票的乘客……
出门行路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说是人为造成的。列车晚点,本是无法抗拒的“天灾”造成的,但如果你服务跟上,广播里不停地进行解释,并在积极寻问列车方位的同时播放一些轻松音乐,本可缓解一下旅客们焦灼不安的情绪,但没有做到。
买票要两道工序,而且还要对付熟门熟路的人。如果都按秩序去排队,减少中间环节,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可这也没有做到。
上车后对号入座,互不侵犯,互不拥挤,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是没有做到。怪谁呢?
北京 云子健
是否有这样的好奇心
《生活周刊》的编辑、记者们:
你们好!
2月14日我到北京站送一个朋友上火车,晚6时左右,我们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乘务员用火车上用的那种白色被单裹着两个孩子走上滚梯。上前询问,那位女乘务员的名字叫张冰洁,是大连开往北京的230次列车的车长。她说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带着他们在秦皇岛上车,到了唐山父亲就不见了,孩子被扔在了车上。原因看来很简单,这两个孩子是痴呆加残疾,双腿发育不全。她说作为过路列车,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北京站处理。北京站的工作人员们表示,以前这种事也有,处理办法是第二天送往孤儿院。
两个孩子被抱进车站的值班室,靠着暖气坐下,值班室里没有床,也没有任何软一点可以垫靠的东西。两个孩子除了一条小裤子,一人一身脏衣服外一天所有,只好把一个孩子放进一个临时找来的硬纸箱,一个孩子放在小裤子上。
两个男孩三四岁的样子,一望而知是双胞胎。坐在裤子上的尚有知觉,不停地嚎哭;放在纸箱里的则神情呆滞,目光散乱,一看就是头脑有毛病。他们细弱的双腿和身子不成比例,甚至无法好好坐着,不一会就会滑下来,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把饼干塞到他们手里,哭的孩子立刻不哭了,两个孩子都忙着把饼干往嘴里塞。他们很饿,但放在他们面前的饼干,他们不知道去拿,必须塞到他们手中。太可怜了。
周围人的反映,有同情、有好奇,有冷漠也有的很“科学”——“是近亲结婚吧”。我不理解、也不原谅这样的父母,他们可以不把孩子生下来,但制造两个生命后,为何这样对待他们?我不知道《生活周刊》的编辑、记者们,是否有这样的好奇心——那些遗弃了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在想些什么?那些遭到遗弃的孩子成了什么样子,在想些什么?特别是那些弱智院里的孩子,是否都有人悉心照料?是否能在阳光下安静地渡过一生?
北京 赵岚
Olesra已经上市
编辑先生:
我在贵刊上读到有关P&G公司试制的Olestra的文章,而后在Internet上又读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这种减肥脂肪的讨论。很多人对Olestra非常抵触,认为它是公众健康的定时炸弹,因为它会引起很多疾病,如上期文章所说,它可能引起轻到腹泻,重到癌病、失明等。还有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它提出批评,如英国的帕米拉·布鲁克说:“Olestra提出了一个道义上的问题: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挨饿的时候,我们竟然还要变着法儿地大肆饕餮。”澳大利亚的朗姆斯托亚说:“耗资上亿美元研制Olestra,只为了让人们在食用垃圾时感觉良好,再花上更多的钱来医治由此产生的疾病,这真是经典的愚蠢。”荷兰的马克·邦泽认为:“Olestra这种不能由生物分解的化合物一旦上市,就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当Olestra顺着我们的肠胃和排污管流进湖泊后,它将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油膜并改变水中氧份的比例。”
尽管有这么多批评,但还是有很多胖子欢迎Olestra。加拿大的悉尼·马可是个胖子,他说“我深感这个世界太需要减肥脂肪了。”顺便又问了一句:“P&G公司能不能再行行好,为我们研制一种无尼古丁香烟。”美国的布鲁斯·查普曼说:“当人们对Olestra提出那么多难以证实的批评时,为什么竞看不到它将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好处?由于有了减肥脂肪,个别毫无节制的人也许会吃更多的炸薯条或甜点,因而变得更胖,但多数人必定会从高脂肪食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波多黎各的维尔施对批评者说:“没有人强迫你消费这种东西,如果你怕它引起疾病。对于那些明知其有负作用又乐于享用它的人来说,满足他们的欲望又有何妨?”
在人们对此争执不休时,美国政府的食品与药物委员会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终于宣布批准减肥脂肪Olestra上市,但却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在快餐中使用。
我想问一句,我们的快餐店里是否有添加OLestra的食品,我也想试试。
上海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