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与EQ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刘怀昭 图·王焱

水果糖测未来
中国有句俗话叫“一岁看大,三岁看老”。脑科学家最近为这话找到了根据。
他们用4岁的小孩子们做过这样的试验:将他们分别领进屋,屋里放一块水果糖。测试者说:我要出去一下,你可以先吃这块糖。不过,你要是能等我回来再吃的话,我会再给你一块。
测试者离开后,有的小孩抓起糖就吃了;有的坚持了几分钟后才吃。但也有些孩子决意要等,结果等到了那第二块来之不易的水果糖。科学研究就把这些孩子的材料归档,静等着他们长大,看看他们的未来和对水果糖的态度有没有关系。
待孩子们上到高中时,一些显著的分别就凸现出来了。对这些孩子的家长和教师的调查表明,那些有毅力等到第二块糖的孩子在长大后一般都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更受人欢迎、更具冒险精神、更自信更可靠。那些在糖果面前经受不住诱惑而轻易动摇的孩子多倾向于孤僻、脆弱、固执,承受不住压力和挑战。两组孩子在长大后接受“学术态度测试”(美国学生报考大学时进行的一项调查)时,更显出量化的区别:小时候吃到了第二块水果糖的那些人的平均成绩高出另外那些人210分。
水果糖测试法所传达的信息是:一个人在情绪方面的控制和领悟能力有高下之分,而这是智商IQ所测不出来的。
关于情绪悟力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将人脑和思维分别尊崇为机器的硬件和软件,而把心灵的种种力量留给诗人去摆弄。然而,认知理论并不能解释那些经常让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天生就会过日子;为什么班里最聪明的孩子将来未必最有成就;为什么我们对有些人光是看一眼就能产生好感,而对另一些人仅凭一面之交就难于信任;在同样的挫折面前,为什么有人经受住了而有人一蹶不振——是思维还是心灵的哪些品质决定一个人的成功?
5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萨勒维(Peter 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John Mayer)提出了情绪悟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说法,以此来描述一个人对自己感受的了解、对他人感受的共鸣,以及“为增强生活品质而对情绪作出的规定”。他们的论点很快便成为美国人的话题,一本题为《情绪悟力》的新书也应运而生。该书作者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eman)是哈佛心理系博士出身的《纽约时报》科学栏目专栏作家,此书总结了10年来行为科学在思维与感受方面的研究成果。丹尼尔·高曼指出,他旨在对聪明的内涵重新进行定义。他的理论是:在预测一个人的成就方面,智商所标明的脑力水平不如一向被看作“性格”的心灵素质更说明问题。
丹尼尔·高曼在此书中还提出,要把他的理论具体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如,公司如何决定雇员的录用、夫妻如何判断婚姻能否持久、家长如何培养孩子、学校如何教育学生。街头暴力、校园纠纷、半数以上婚姻的破裂、孩子遭受到的伤害甚至杀害(在美国,夭折儿童多死于父母或继父母之手,他们多声称是管教孩子时失手所致)……凡此种种都是高曼苦心孤诣要通过情绪教育来解决的。
但情绪悟力理论到底该如何诉诸具体应用呢?情绪是否像智力一样可以量化为商数来进行测定?这正是产生争议的地方。专家们一方面希望情绪因素得到人们适当的重视,一方面又担心情绪商数(EQ)的引进会被误用。高曼也承认,量化人的性情和量化人的智力一样,具有危险性;因此他在书中从不用EQ的提法。但他还是在《今日美国》上发表了“非科学的”EQ测试法,以期帮助读者“把握人际关系。判断无法言说的感受”。
IQ与EQ
EQ(情绪商数)与IQ(智商)并不是绝然对立的。有的人两者俱佳,有的人则哪方面都欠缺。专家们试图研究出情绪与智力之间的互补关系,比如,一个人处理生活压力的能力是怎样影响到智慧的施展的。在“成功”的组成成分中,专家们目前普遍认为IQ成分约占20%,其余的部分则与社会、与运气、与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limbic和neocortex两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程度相关。
破解了这些大脑沟回的是美国纽约大学的约瑟夫·莱窦克斯(Joseph LeDoux)。他发现了人脑的一处短的回路,它使情绪在智力得以介入之前就驱动人的行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揭示了人脑neo-cortex系统和limbic系统之间的相辅相成对人的正常生活的意味。如果大脑受到某种损伤导致两种系统间失去联系,人的生活就会乱套:人可以照样聪明伶俐,但却失去了采取决定的能力,因为他们拿不准自己对各种决定的反应。这种情形下的人亦无法对他人的警告或愤怒作出反映。若是这种人犯了某个错误,比如说错误地作出一项投资,他们会麻木地一再重蹈覆辙。
自我认识与从众能力
因此,自我认识就成了情绪悟力的基石:一个人应当十分聪明地知道自己的感觉。据高曼的分析,自我认识可说是一种至为关键的能力,因为它使人体验到对自己的控制。自我控制的意思并非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要作出有意识的调整。亚里斯多德在谈到人的意愿时曾说:“任何人都会动怒——这很容易”;而高曼则说:“但是要找对动怒的对象、动到恰到好处、为了确定的目的、通过正确的途径——这并不容易”。
所谓自我认识就是帮助人发展出应付情绪的机制。比如,郁闷和沮丧属于“低调”情绪,而作推销员要总是处于高昂的情绪状态才能在街上游说,因此推销员的适当性格类型应属愤怒、焦躁等高调型。总之,自我认识的理论就是要抓主导情绪,从被动安排中解脱出来,找到相应的施展方向。
大概最可见的情绪技能当属“从众能力”了,这也就是产生共鸣、左右逢源的能力。研究专家们认为90%的情绪交流是无需语言的。美国哈佛心理学家罗柏特·罗森叟(Robert Rosenthal)发展了“非语言感应力描述”(PONS)测验,来判断个人解读情绪提示的能力。他放映一部以情绪表达为题材的电影,测验受试者对各种情绪提示的理解能力。这种实验再次说明:PONS得分高的人在工作和人际关系方面更为成功;PONS得分高的孩子,在学校更受欢迎、各方面表现多出色,哪怕IQ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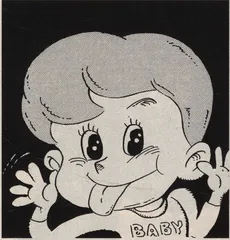
从以上的几种测试中不难得出一些明显的启示,比如,如果对情绪悟力有足够重视并加以诱导,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取得更大成功?在美国,这越来越成为人才教育方面的一个关注点。比如,从事人事工作的人员开始产生这样的意识,在一个协作的社会中,IQ决定你能否被雇用,而EQ决定你是否能得到升迁。
在美国,关于情绪悟力的话题尤其集中在学校教育方面。高曼说,针对吸毒、暴力、早孕……等青少年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情绪悟力提示了预防教育的途径。纽约市第75公立学校在5年前就开设了情绪认知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愤怒、挫折、孤独感,五年来卓有成效。
这使得美国的许多学校管理部门开始对传统的课程和考试模式进行彻底的再思考。独立学校国家协会(NAIS)的会长彼得·瑞利克就认为,长期袭用的SAT考试就属当废之列。他大力推崇EQ测验:“否则即意味着我们对成就的定义十分狭隘,意味着在人的潜力方面的极大损失”。
EQ:困扰与怪圈
教育者对情绪悟力理论的趋之若鹜反倒给一些科学家带来了困扰。情绪悟力理论的鼻祖,耶鲁心理学家萨勒维说,一方面,他很高兴看到人们渴望通过教育来了解更丰富的情绪生活,从而帮助自己对成就的获取。但另一方面:“我要反对的是对社会期待(social expectations)的趋同性培养。其危险在于把人教育成统一的机械的情绪模式,比如教给孩子如何为‘正确’的情绪——聚会上笑、葬礼上哭、教堂里坐着不动。”
还有些心理学家更对情绪技能训练的正规化设想表示通盘的怀疑。前面提到的霍布金斯大学的学者麦克哈夫尖锐地反对高曼将其理论推广到儿童基础教育中去的主张:“是个可恶的想法”,因为“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成人该怎么进行情绪教育呢”。他从高曼书中举了个例子:当两个小学生发生争论时,老师插话打断争论。对其中一个小学生说:“我欣赏你在谈话时的果断决然。你没有采取攻击性”。麦克哈夫批评道:“你当真以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懂得果断决然和攻击侵犯之间的区别吗?”
问题的实质可能在于忽略了某种理论的必要成分。情绪技能与智力一样是中性的,正如同一个天才既可以将其智慧用于救治癌病也可以用于发明病毒。在发掘人的能量时,如果没有一个道德指南针来指向,情绪悟力同样可以导向善或恶不同方向。发明了水果糖测试法的心理学家沃特·米斯切尔观察到,吃到第二块水果糖的孩子所具备的那种延迟享受的天赋既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成就斐然的好公民,也可以使他成为一个精明透顶的罪犯。
EQ话题引发的热烈争论甚至还涉及到对美国国内道德指导方针的再评价。高曼为此重又著书,集中讨论如何避免将情绪技能的培养搞成一种价值体系的灌输。当然,这并没有息事宁人,相反,争论正在更宽的层面上铺开来。
EQ话题先是激活人们对生活观念的再思考,接着就把人们带进了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怪圈里,使得追求完美生活形态的现代人们多少有点怅然若失。此时便有好事者拿EQ做起更广泛的实践来,比如,用EQ测美国历届总统的情绪悟力,结果实验者说:克林顿脑袋虽然聪明,“可控制冲动的能力简直糟透了。”最终未来生活的和谐更求助于心还是更相信脑呢,这还仍然是个问题。 智商测试iq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