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披头士”
作者:舒可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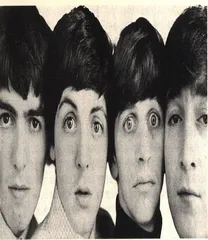
60年代引诱人们走向永远的“草莓地”的“披头士”,左二为列侬
“披头士”复活
在英美,披头士(Beatles)这个乐队的名字与60年代整整一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你问一个与“披头士”同时代的人:“肯尼迪被害时你在哪儿?”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问:“‘披头士’在演唱《艾蒂·沙利文》时你在哪儿?”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同样的地方——电视机前。“披头士”乐队自1970年解散,1980年列侬在纽约被一个歌迷枪杀后,人们当然以为再也听不到“披头士”在一起演唱了。从1970年到1995年,这25年间,等待“披头士”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事件。现在,请听吧!
ABC电视台1995年11月中旬在美国播放了一组长达6小时的纪录片,同时播放的还有一部音乐片《像鸟一样自由》。11月20日,EMI唱片公司终于将传奇的Abbey Road档案室的大门猛然洞开,并开始发行“披头士”当年录制而未播送的歌曲。唯一获准进入过Abbey Road档案室的局外人Mark Hertsgaard说,被封存在Abbey Road档案室里的“披头士”资料录音长达400小时,其中有音乐、有歌曲,有他们工作时的有趣谈话及争论。
1995年是“披头士”复活的好时机,对于“披头士”如此,对于听众也是如此。
去年,“披头士”成员麦卡尼,哈里森、斯达尔在麦卡尼的录音室聚首,着手完成列侬当年未完成的一首歌:《象鸟一样自由》(Free as a bird),这是一首动人的、优美的有关家庭情感的歌曲。为了使3人都作好心理准备来完成这首15年前的歌,麦卡尼要求大家要假戏真做。他说:“当年我们演唱‘Sgt·Pepper’时,我们曾假装我们是别人,这样做有时能在我们心里注入一些启示。所以,现在我们假装列侬打来电话说:‘我要去西班牙度假。这儿有一首小曲我很喜欢,给我把它做完。我信任你们’”。他们复制了列农演唱这首歌的单曲磁带,列侬高亢颤抖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机中响着:“Free as a bind/It’s the next bestthing to be/Free as a bird/home,homeland dry/Like a homing bird I’ll fly.”尽管列侬的儿子斯恩曾警告过麦卡尼,“听一个死人的领唱肯定有点古怪。”但是,事实上听到列侬从遥远彼岸飘然而至的声音是令人舒畅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在歌唱。
当年“披头士”用他们的歌曲,如“A Day in the Life”,把流行歌曲提升为艺术后,25年间,听众们面对的各种乐队又退回到流行歌曲里。音乐电视像一个自动唱机,在粗劣的赞歌般的噪音下面,总会有一首4分钟的流行歌曲诱你上钩。“披头士”的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说:“音乐是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是变糟了,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不讲究”。流行音乐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马丁伤心地说:“完全是糊弄事。”只有“披头士”能使人们回想起那个感觉敏锐丰富的时代。在英美,很多人对60年代的记忆都将永远与对“披头士”的记忆联在一起。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生活像这个乐队的音乐一样,从清纯到辛酸。去年EMI公司用一珍贵的汇编“生活在BBC”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调查“披头士”听众基础。这张汇编唱片是去年卖得最快的唱片。唱片一上市,在美国排第三,在英国排第一。这表明“披头士”的热爱者依然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60年代的一种象征?
1963年4个小伙子从利物浦进入整个世界,他们的现场演出引起的是震惊。1964年2月24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标题上写着:“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这是女孩子们在现场的尖叫声。古典音乐作曲家、评论家WilfridMellers评论道:“‘披头士’是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一样的又一天才。”
既感动了尖叫者又折服了乐评人的因素是“披头士”音乐的个性表现出的绝对新鲜感。他们早年的代表作“Please,Please me”,“I Want To Hold YourHand”“Love Me Do”,是如此的清纯,生活在60年代的英美人除了“披头士”的歌声中再也找不到至真至纯的人性,它讲述的情爱是简单的、透明的、直率的,没有缠绵消沉的情绪。这些歌声猛烈地敲击着人们耳鼓以及灵魂,同时又总是给人某种无所着落的伤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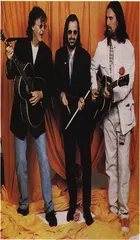
重新走到一起的保罗·麦卡尼(左)、灵郭·斯达尔(中)、乔治·哈里森(右)
“披头士”似乎有一种魔力,它能使每个听者都成为“披头士”。他们的很多歌,像是一些微型歌剧,唤醒一系列情感反应。“Yesterday”是对逝去时光的礼赞;“Panny Lane”里有一个陌生的乌托邦;“Strawberrry Fields Forever”则告诉人们,人们总是误解一切,如果闭起眼睛,生活才显得容易一些。列侬要去那永远的草莓地,他让人们也一起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值得挂怀的。“A Day in the Life”是“披头士”顶峰之作,列侬忧伤无望地唱着:“噢小子,我今天读了新闻……”新闻的题目就是老样子:意外死亡,战争、荒谬的愚事,而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老样子,喝咖啡,起床、穿衣服,赶汽车,所有这一切在列农的歌声中全部被重新解释。
“A Day in the Life”通过与新闻题目中“真实世界”的潜在对抗获得了一种超越,谁不想超越“真实世界”里那些令人厌恶、令人恐惧的事?正是这点使它如此动人。
渴望永恒的价值
在一种极度琐碎的“文明”生活中,“披头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角度。自1970年“披头土”解散至今的25年间,它曾承担过的社会角色一直没有被忘记。至今仍然有一些地方能带人再次进入那种特殊的气氛中,Abbey Road的第二录音室就是其中之一,Beatles曾在将近10年时间里于这里录音,这个录音室被精心保存着,人们能走进去重新呼吸“披头士”的空气。甲壳虫们(“披头士”的英文Beatles意为“甲壳虫”)从这里飞出多年了,但一切都生动地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比这还要多。“披头士”的3个成员新近重组织《披头士歌选》,也许能够满足这种需要。
去年,麦卡尼、哈里森、斯达尔就已汇集在一起,录制“Free As a Bird”时,就已显露了重组的迹象。唱片制作人Jeff Lynne说:“那天录音室的气氛很兴奋,他们还都是老样子。他们当中某个人会大笑着说:‘你怎么了,你这没用的家伙!’”他们合作在这首歌里增加了一些和声、贝司、吉他及一部分新写的钢琴段落。列侬当年在这首歌后面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诗节:“在我们曾经熟知的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里森和麦卡尼完成了它,并在10年里轮流唱过:“我们如何失去了联系,这意味复杂,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而独自生活吗”。所有这些声音现在又汇聚到了一起。当斯达尔站在录音室的控制台听到“Free as aBird”时,他不能抑制地激动,他说:“这听起来就象流着鲜血的甲壳虫。”
“披头士”的时代已过去多年了,人们对一些永恒价值的渴望却没有减弱,像鸟一样自由永远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披头士乐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