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记录故宫博物院
作者:王恺(文 / 王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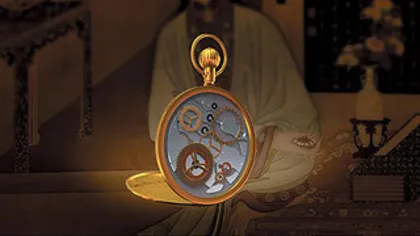 ( 利用电脑技术处理的画面 )
( 利用电脑技术处理的画面 )
花费两年的时间去记录故宫博物院,对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工作,习惯于快速新闻节奏的编导周兵和他的同事们,是一次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奢侈的经历,也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快乐是因为他们在一群意图拍摄者的竞争中胜出,最终得到了被故宫博物院称为“空前”的拍摄机会;痛苦的则是整个拍摄过程都充满了挑战:从总编导到普通摄影,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必须解决的难题;而从小心翼翼地拍摄珍贵的文物到拍摄组的上厕所问题,细节过程也没有一件省心的事情。
两年的漫长拍摄使得这群人最终爱上了故宫,“像和它有了亲戚关系似的”。也有很多人说两年的拍摄生活使他们的心情变得非常宁静。
经过大致剪辑的10集的专题片《故宫》将在近期内在中央一套播出,被总编导周兵称为“精编版”、“大片”,而整个选编出来的2000多分钟的素材片将再花费一年时间被剪辑为100集,每集约10分钟,将在最细节的层面展现故宫。这些尚未完成的片集已经被多家没有拍摄机会的境外电视机构视为必得之物。
缘起:周兵的运气和央视的机会
周兵说自己在拍摄《故宫》前一直做的是“受命文学”,到拍摄故宫时,才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以往的“受命文学”拍摄也使他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早年在《东方时空》工作的他一直喜欢传统文化,因此拍摄了一系列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如《周恩来》,和利用真实再现手法拍摄的抗战系列影片。“那些利用演员和场景再现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学术界一直不看好,觉得违反了纪录片的原则。”
 ( “在最真实的场地用最真实的器物还原了历史” )
( “在最真实的场地用最真实的器物还原了历史” )
但这次他也把这项技术利用到《故宫》的拍摄中,“在最真实的场地用最真实的器物还原了历史”。除此以外,他还利用一系列拍摄大片的技巧来拍摄故宫:摄影指导赵晓丁是影片《英雄》的摄影师,“场面很宏大”;利用电脑技术来处理画面,其中一幕做到了“甲光蔽天”的效果,“把我在史书中看来的明成祖在故宫阅兵的感觉拍出来了”。作曲者是张广天和苏聪等人,也是奔大片那个套路去的。
谈起这部“大片”具体的技术处理,壮实的西北人周兵是快乐的。但是更让他激动的,还是当初如何争取到拍摄故宫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于沉迷于历史文化的他一直是梦想。
“大概是2001年,和一个在故宫工作的朋友聊天,觉得要是能有个机会拍摄故宫就好了。”但是,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当时不是他一个人在争取,而是各家机构都在竞争的一场艰难的比赛。
在周兵他们拍摄前,只有3家机构获得过记录故宫的机会:NHK拍摄的《故宫的至宝》,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紫禁城》,和DISCOVERY频道拍摄的90分钟的《故宫》,“这些都是在较早的年份拍摄的,近年故宫早就对各个机构关上了大门”。就他所知,当时已有若干家境外机构一直在联系拍摄《故宫》事宜,都无功而返。
2003年的冬天,在故宫漱芳斋,央视新闻评论部和故宫博物院正式签订拍摄合作协议,并在故宫太和殿上举行开拍仪式。签约完的那个傍晚也成了周兵最美好的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场面大,来的人多。应该说我对于那些是见惯了。”那是个冬天的傍晚,参加签约的人都散尽了,北京下午5点多钟的夕阳照在太和殿的檐角上,整个宫殿金碧辉煌。“我觉得特别有震撼力。”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观念都因为这两年的工作而改变。
过程:薄如蝉翼的“三秋杯”和 卫生的盒饭
由于采取的是拍摄电影的方式,现场拍摄器材远比一般拍摄复杂。当摄影师把长长的摇臂对准某件难得一见的文物时,现场并没有想象中的一片“屏住呼吸”的宁静,而是一片尖叫,这些尖叫声是现场的故宫文物保护部工作人员发出的,在巨大的摇臂面前,那小小的文物显得非常脆弱,他们是害怕距离还有半米远的机器散发的热量损害了脆薄的器皿。
周兵的助手,一直在现场进行拍摄工作的曲晨曦还记得每件文物的拍摄难度。不是说协议签好了故宫就可以随便进出拍摄了,进出哪个院落拍摄都要提前打报告,每个拍摄现场都层层把守,当然,这样的报告相比起拍摄文物而言,还是要简单很多。
许多珍贵的故宫文物基本没有展览,现在提供拍摄要经过故宫层层部门的审批,“盖十七八个章是常事”。比如明成化斗彩三秋杯,高只有两寸,胎釉号称薄如蝉翼,世界上仅存两件,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件文物仅拍摄报告就审批了一个月。“经常在觉得不可能的时候,报告批下来了。”
而提取文物到拍摄现场的过程也极尽复杂之能事。“每个宫殿的大小门口都有故宫工作人员在监督,好像古代帝王传膳时一样。”这些人员是保安部门的,而器物部工作人员则大规模出动,极其小心地将珍贵文物提出库房。一次拿一件瓷器,由于冬天寒冷,工作人员害怕从库房直接提取出来就拍摄会损坏瓷器,“拿到拍摄现场一直让它醒醒,一个多小时不敢动它。”也就是那些场合,让周兵他们觉得,这些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在呼吸中。
还有清宫秘玩“珐琅彩”的拍摄,当年此物就价值十万两白银,在民国前,民间一直传闻有此物而难得一见。到了拍摄那天,“现场上大家都紧张地发抖,害怕有所损害”。一个故宫专家到了门口而不进去,诚惶诚恐的他觉得“受不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摄影师李建明很少受到故宫文物的“精神压力”,却碰到自己难得的技术困惑,他一直在拍摄整个专题的公共镜头,也就是说以建筑物为主,“拍到四个月时,痛苦不堪,觉得该拍的全拍完了,没得拍了”。他那时候的感觉是恐怖,觉得再拍下去自己就要生病了,也真有同事离开——受不了那种茫然的感觉。摄影师李少白告诉他,可以放弃常规手法,拍摄“看不见的故宫”,他借来400倍的长焦镜头和微距镜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宫,得意作品有“一个水滴里倒映出来的宫殿”,再就是拍摄工作即将结束时的一个大雪天,在角楼上偶尔拍摄的故宫,像水墨画一样。
更多的时候,周兵没有抒情的机会,作为总编导,他要为种种始料不及的情况作出努力。“拍摄总是在早晚游人散尽后开始,开始拍摄了,和保安、文物部门打好招呼了,发现没和管厕所的行政部门打好招呼,结果几十人没地方上厕所。”
故宫很少电源插座,“开始想准备200米电线差不多,后来发现2000米都不够,又得去找专业电线”。因为是电影的拍摄方式,最少的拍摄场合甚至都有30多人,常常一个镜头需要六七个摄影师,周兵形容自己的日常工作场景是这样的。“大家都在拍摄某件难得的玉器时,我在台阶上发愁,愁今天要到哪里去定一批卫生的盒饭,千万不能出事啊。”也因为忙于当后勤总管,很多难得的器物他都只是在镜头上看见,对于喜欢收藏的他来说,“真是难受”。
结束:和故宫结成了亲戚
事实上,正是日常的琐屑和突然的激动组成了整个拍摄过程。曲晨曦形容自己看见清宫档案上雍正的一段批示时的心情:“一直在想象那段历史,可是没想到这段历史会那么清晰地跳到眼前来。”突然之间接近了历史。
作为总编导的周兵觉得记录故宫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觉得自己的机缘真好——在读艺术史博士生的他看见了不少自己导师根本没法看见的东西。可是他还是后悔,因为尽管调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但很多文物,只是一次性的短暂的取出进行拍摄,“拍完了才觉得,要是能再从那个角度拍拍就好了”。
还有一点遗憾,此次拍摄中,最少涉及的就是书画,“那些书画拿出来一次就损坏一次。”因此很少要求拍摄这些。“心中有一种敬畏的感觉。”有点缺憾更觉得机缘的珍贵。
配合拍摄的故宫工作人员一直用“空前”来形容这次拍摄,每场拍摄中他们都付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努力。但是拍摄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的那段历史的陈丽却宁愿用更满的词“空前绝后”来形容自己的拍摄工作。她负责的部分是由故宫博物院建院前后到抗战前的这段历史,和各集内容不同,需要大量的活着的人物的采访。而这些人物的出现肯定是“绝后的”。
“我想做一段口述历史,通过那段时间和故宫有关系的人的采访,把军阀混战时代的故宫和北京的命运讲清楚。”但是做起来才发现很难,没有学者专门研究故宫的这段历史,当事人更是少有。“只有单士元老先生一人还活着,开始阶段焦虑得不得了。”
她研究了半年的资料,找到了启功先生,既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陈垣的学生,也是首批故宫参观者的启功先生在病榻上回答了她的问题。“太难得了。”她还想通过派出所查找一批当年故宫开放时参观过的老人。开始在皇城根的居民区那里找,结果杳无音信,后来还是通过自己从前做节目时曾经访问过的一批老人牵线寻找,找了几个当年在故宫刚开放时参观过的老北京居民。很多老人开始回忆故宫内外的北京城,“他们能清晰地描绘故宫开放时的场面,还能说出北京城当时被军阀占领时,士兵站在车身上的场景”。
找到研究者,则能勾勒出清室善后委员会怎么和当时北京的占领者张作霖、段祺瑞他们周旋的过程。做完30多个亲历者、研究者的访谈时,她觉得心中有了把握,整个故事在她心里成形了,短短的一段历史,有悬念,有起伏,更多的是其中的气节。“拍出来后,觉得真是为他们拍摄的,怀念那些在军阀混战年代保卫故宫的先人们。”■ 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