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诒前:为了梦中的田园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姗)

邢诒前总喜欢回忆童年的那个场景:他到村里的池塘边放牛,牛在一旁悠然吃草,小邢诒前躺在大树下,看着周围成群结队的白鹭欢叫着飞上蓝天,没多久便酣然入梦。虽然穷困,但留在记忆里的,却是田园牧歌般的宁静与美丽。
当邢诒前12年前以一个成功的香港商人身份,衣锦还乡般地重回故里时,却颇为伤感地发现,童年的记忆早就荡然无存,昔日美丽的池塘湖泊周围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茂密的大树也不见了,代之以农民开荒种的木薯等作物,那些欢乐的鸟儿们也沓无踪迹。
“我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靠自己的努力把它(生态)重新恢复起来。当时手里正好有钱。”谈起1993年回家乡投身环保的初衷,邢诒前说得很坦率。
1956年农历七月初七,邢诒前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的东路镇。文昌是有名的侨乡,而侨乡也大多因贫穷而起。饥饿,是邢诒前中学4年关于青春期的惟一记忆。“如果钢笔掉到地上,我不敢马上弯腰去捡。”他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叫我的名字,我只能慢慢地转过头去看。不然,一下子就会眼冒金星。”
1979年,像这个村很多漂泊海外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23岁的邢诒前带着一腔梦想,赴香港投奔父亲。从建筑工地的搬运工开始,他开始了艰难的个人奋斗。第二年,邢诒前往返广州和香港,做起了“进出口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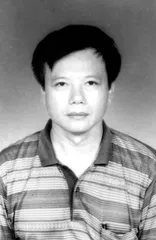
“‘小财在己,大财在天’。”邢诒前说,“很多东西既是头脑,也是运气。”1982年,为了生意方便,邢诒前在深圳花了14万港币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3年后已涨到40多万。邢诒前果断出手,净赚30万港元。想做大事业的邢诒前把这些钱带回海南,在琼山县开了一家服装厂,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90年代初,30多岁的邢诒前成了拥有200万港元资产的商人。
邢诒前的机会好得令人嫉妒。1992年,为了建职工宿舍楼,邢诒前打报告给政府,申请4亩土地,结果员工误听成“10亩”,邢诒前不太情愿地花60万元买下了这10亩。那时正赶上海南经济发展最热的阶段,接下来的时间,邢诒前每天惊讶地看着手里的土地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噌噌地往上蹿。刚刚到手的10亩土地,几个月之内竟然最高涨了50倍之多。瞅准时机,邢诒前很快处理掉服装厂,投身房地产。1993年,邢诒前攀上了财富的巅峰,“钱,土地,我都有。我就买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汽车,最好的写字楼。我先开一辆皇冠2.8,又换成奔驰500,再买一辆凌志400”。
“那时我有一个左右手,他说,现在海南地产不太正常,你现在所有的资产,包括汽车、别墅、地产,折合起来价值不下两亿元。他劝我把这些东西卖掉,然后周游世界,选中一个世界名校进修5年,5年之后如果还对原来的东西感兴趣的话,可以再买回来,重新开始。”
而另一件事情也给邢诒前很大触动。当他返回家乡时,却发现家乡一如以前那样贫困,但生态却比以前更加恶劣。“父老乡亲说,很多树只开花不结果,水稻产量也很低,原来我的家乡是有名的荔枝之乡,现在荔枝也不结果了。”
很多年后,邢诒前才意识到,当时处在事业巅峰时刻的他,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的下一步作出选择的关键阶段。回家乡靠自己能力恢复生态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看到某香烟的那句广告语“想做就去做”,他也认为是命运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暗示。1995年,邢诒前有了个大胆的决定——利用18个自然村的自然景观,创办融自然鸟类保护区、高级旅游度假区、公司+农民高效农业开发、园林商住区等为一体的现代大农业特质的万亩乡村公园。
邢诒前坦承,当他终于决定自己人生的这个方向时,他的想法纯粹、简单得出乎外界想象:他要回到童年的那个田园。“我那时也算是事业亨通,还在外面赚钱,所以对这件事也没有精打细算,也不是带着商人投资的目的去做的。”
邢诒前的努力从买老树开始。他认为,树就是鸟儿的家,没了树,鸟儿难以展翅高飞;听说有人要砍树,他马上过去,商量价钱,把老树买回来;村民都觉得这个人大脑有问题,手下人也反对:把那么一棵大树费九牛二虎地挪走,既要运费还要修路,得不偿失。“起初我们没有经验,那些树很大,吊车又拉不出来,又没有路运出来,有时花了六七天才到了保护区,到那儿后也死了。”买树之后又买鸟。看到路边有人卖鸟,“他卖几只我买几只,他卖几笼我买几笼”,又在保护区成立了专业护鸟队,逢人就讲保护鸟的意义。慢慢地,周围农民的意识也有了转变。
邢诒前的一番苦心也逐渐显露出效果。一年、两年,保护区的鸟类渐渐多起来,多年不见的候鸟也多了。
邢诒前至今忘不掉那一幕。建保护区的第三年,某一晚,邢诒前住在岛上,晚上突然被一阵大而急促的鸟叫声惊醒。以为什么人闯进了山庄,他叫上看护工,带着两条狼狗,跑到树林里。“那天皓月当空,我们蹲下来一看,哇,怎么有那么多鸟!它们密密麻麻地停在树林里,高、中、低都有,最低的仿佛伸手就能捉到。那个夜晚好像是鸟类大集会。”邢诒前仍沉浸在那种感动中:“你想象不到,在这样一个年代,竟还会有那么多的鸟!可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个场景,我想我是多么幸运而幸福。”
但邢诒前的经济却越来越窘迫。对保护区来说,是只投入不产出,起初,邢诒前还靠着引进荔枝等赚的钱维持周转,但到后来,他却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靠其他生意赚的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为鸟类保护区投入的精力及金钱却越来越多,自身的“造血功能”严重不足,几年下来,邢诒前不光把原来的积蓄几乎消耗殆尽,甚至连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亿万富翁投身环保事业一贫如洗”,当有媒体把邢诒前的故事报道出来后,很多人将其比作堂吉诃德,邢诒前并不在意。“我更关心目前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评价,决定着我的保护区的前途,也反映了社会环保意识。社会对我的评价与我的事业是分不开的,对我的评价,就是对我的事业的评价。”
而媒体及公众对邢诒前及其事业的评价,则令他大为感动,“阳光下的力量”,邢诒前很诗意地形容他感觉到的支持。“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搞私人保护区,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私人保护区出现,并且运作得更加成功。”
很多人将邢诒前形容为“理想主义者”,邢诒前并不满足于这一定义,“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做一个成功的环保主义者,千万不能做‘反面典型’。”邢诒前笑呵呵地说,语气里满是自信与希望。■ 邢诒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