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杰作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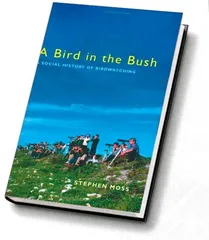
企鹅出版社9月份即将出版《纽约时报》的首席艺术评论员迈克尔·吉默曼(Michael Kimmelman)的一本书,《意外的杰作——生活的艺术和艺术地生活》(The Accidental Masterpiece—On the Art of Life,and Vice Versa)。该书有十章,记述他对艺术大师以及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收集了7.5万只灯泡的牙医和热衷于用数字画画的人的探访。他相信制作和享受艺术绝不是只能通过帆布和乏味的美术馆。艺术的乐趣可以在旅行、收藏和个人活动中被体会到。只要睁眼去看,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艺术。艺术是生命中最强烈的激情,说艺术家是特殊种类的人是一种谎言。“热情地活着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艺术创作的必需。大多数艺术家,像大多数人一样,一生中都会有一两个好的念头,这一两个念头支撑着他们度过一生。”
如果没有对艺术欣赏的正确认识,一个人往往在墙上挂满大师之作的博物馆里逛了半天却无动于衷。它们本来该令参观者产生或悲伤或兴高采烈的情绪,但是参观者却往往发生情感上的短路。艺术评论家说,这是因为参观者太过被动,因而没能抵达艺术家的作品的内核,欣赏者花费的工夫与艺术家创作伟大作品时的艰辛和紧张太不成正比了——艺术家在一块帆布上花费了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参观者瞄上几秒钟之后,很快就将它抛到了九霄云外。吉默曼说了一则逸事,说皮尔·波纳尔(Pierre Bonnard)曾经要求模特不要静静地坐着,而是在画室里走来走去,这是为了同时画出“在场者和不在场者,隐藏者和显现者”。
吉默曼的这本书清晰明了,写人时也很风趣。他参观了希克的“白炽灯博物馆”;连续数个下午从头至尾地观看艺术家在帆布上创作一幅作品的过程。他是一位细致的观察者,一个口齿伶俐的导游。经常还要表现出他的勇气来。他决定去看一看大地艺术家迈克尔·海泽1972年开始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秘密制作的玛雅遗址那么大的雕塑,便给这位艺术家打电话,希望能难得地被邀请前往。吉默曼跟海泽的交谈并不愉快,海泽在通话的时候放下话筒,朝头顶一架飞得很低的飞机开枪。不过吉默曼最终得以成行。“有的艺术不会主动送上门来,甚至也不该轻易地主动送上门来。有时你不得不迈步向前去会见它。”
《纽约观察家》的高级艺术编辑Choire Sicha在书评中说:“吉默曼性情温和,不像是个搞评论的,更像圣徒传作者。他好像无意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布道。”但他也有狂者的一面:批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都成了艺术品展销会,“博物馆为眼前利益而降低自己的原则,长远看来会招致公众的鄙视。”对大腕级艺术家的轻狂他也不无微辞。在跟海泽交谈时,他想,为什么这些艺术家都选择在西部的州搞创作,也许他们以为东部的小州不足以同时容纳他们。对此Choire说:“这话说得很有趣,但大地艺术家们的傲慢与银行家们的傲慢还是有区别的吧?”
吉默曼还写到一位顽固的、遁世的抽象画画家雷·约翰逊(Ray Johnson)。约翰逊曾经从雇用的直升机上往里克岛(纽约市的监狱的所在地)投放了一个60英尺长的热狗,坚持要他的艺术品经销商支付租直升机的钱。然而,他最著名的作品还是他的死亡。1995年1月13日,在长岛发现了他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后经调查得知,67岁的他是按照数字13去死的:13日,67岁(6+7=13),死之前他住在一家宾馆的247号房间(2+4+7=13),给一位老朋友William Wilson打过电话——他的名字一共13个字母。约翰逊的故事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它给了吉默曼一个机会,揭示西方艺术在过去的500年间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艺术家个人的感受性开始占首要位置。在中世纪,艺术跟宗教紧密相连,绘画越是跟艺术家的手勾画的笔触无关,越是珍贵——绘画就成了耶稣的印记,其价值来自一位不可见的艺术家。到世俗观念取代了神圣者之后,艺术家慢慢发现了他们只有一种东西可供出售,那就是他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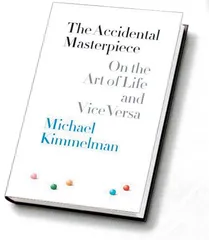
阐释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吉默曼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深刻的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经分析凡·高画的农夫的一双鞋子所包含的深远意味:“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双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之声的召唤,显耀着大地的成熟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现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意,这双鞋具浸透着对面包的可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个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喻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颤抖⋯⋯”相比之下,那七万五千只白炽灯泡倒显得很苍白。■
 ( 迈克尔·吉默曼 ) 杰作意外
( 迈克尔·吉默曼 ) 杰作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