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做梦超越死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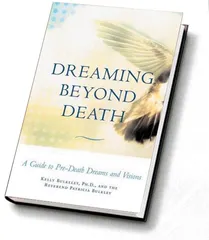
对于佛教中的得道高僧,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他们都能知道自己将在什么时候死去,会自己安静地找个地方坐定,悄悄地死去。就好比一些动物要下崽了,会自己去找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完成整个过程。其他宗教也有类似情况,“塔列朗在84岁那年,挑选了某个时辰签署他皈依天主教的声明,他不愿在有生之年收回前言,这一声明墨迹一干,他便咽气了”。
一般人接受自己生命终结的命运就没这么平静。比方一个人被诊断得了癌症之后,最初会觉得上天对自己太不公平,感到自己受到了欺负和不公平的对待,这种愤怒、失望和抱怨的情绪可以部分地驱赶对死亡的恐惧。此后他可能就会慢慢接受现实,只求多活两天,多得到一些东西。继而失去意识,陷入昏迷。
帕特里夏·布克莱(Patricia Bulkley)在一所养老院做了十年心理咨询师,目睹了很多老人临近死亡时的惊恐。八十多岁的退休商船船长拉斯穆森得了癌症,他一直都很害怕,直到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片宽广、黑暗、空荡荡的海面上航行,他再一次感觉到探险带来的兴奋和快乐。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对布克莱说:“奇怪的是,我再也不害怕死亡了。”死亡不再是一个终点,而成了一段旅途。在布克莱跟她儿子合著的新书《做梦超越死亡》中,很多人在他们的临终岁月都做了一些很特别的梦,他们的梦让他们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增进了他们跟亲人的关系。
布克莱女士在书中说,对于临终前做的对死亡有预感或者有所揭示的梦,历史上有不少记载,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古希腊。据《史记》记载,孔子去世前7天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夏朝人死后葬在主人之位,周朝人死后葬在客人之位,孔子梦见自己跟殷商人一样,死后葬在两柱之间——最尊贵的位置。心理学家荣格能跟他的学生交流的最后一个梦是,他梦见了一块大圆石,上面刻着一行字,“对你来说,这是表示单一和整体的符号”。荣格将这理解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完整。孔子至死也没有实现恢复周礼的理想,临死前还在用自己的梦来向学生交待后事,表达其重古薄今的思想。荣格好像是在说自己给后人留下了一套心理学理论,已经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孔子和荣格都能超出一己的小我,死亡对他们来说不足畏惧,临终时想着的也是经久的事业。
现代的凡人才是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人。做一场就能超越对死亡的畏惧显然是轻便的手段。临终前做的梦都比较急促,也更加生动,更能被记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艾伦·西格尔说:“一生之中,在危机关头或者关键时刻,做梦的需要都更加强烈。”事件越生动,做的梦也更加紧紧围绕着要解决的情感问题。弥留之际所做的梦会生动、强烈到让人误以为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们梦到的是死去的亲人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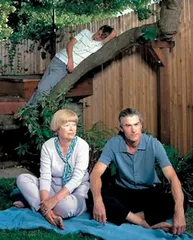 ( 布克莱跟她儿子合著的新书《做梦超越死亡》 )
( 布克莱跟她儿子合著的新书《做梦超越死亡》 )
这些梦比较突出的主题有,出门远行,与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看到了停摆的钟。一些意象非常简明直接,一个妇女梦到病房窗台的蜡烛突然熄灭,黑暗吞噬了她,然后蜡烛又自动被点燃。一个男人好像是发现了生命的真谛,他梦见自己在跳舞,舞伴留下了他们舞动的轨迹,就像用彩带摆出了一个图形。“真的是设计好了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对方。”也有很多人临终前做的是噩梦,梦见自己被无人驾驶的、飞驰的汽车追赶,或者被龙卷风卷跑。
布克莱认为,虽然这些梦很强烈,但是施与临终关怀的人并没有充分开掘其意义,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大损失。谈论弥留之际所做的梦对就要死去的人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开启话题的突破口。对将要死去的人来说,可以借助谈论自己的梦说清楚很复杂的感情。这些梦能让将逝者获得安慰,也同样能令其家属得到安慰,布克莱说:“这些故事在葬礼上被反复讲述,他们会成为家族传奇的一部分。”蒙田希望,按照恺撒“事物在远处往往比在近处显得更大”的逻辑,离死不远的时候人的恐惧已经不是最厉害的,照此,对临终者施与临终关怀是不必要的,只是安抚幸存者的灵魂罢了。
电影《野草莓》的开头令人过目不忘:空无一人的街道、颓败的建筑、失去了指针的钟表、艰难的滴答声,以及棺材里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导演用影像描述了一个老人的噩梦,接下来,导演还让他还在幻象中回忆了其童年、初恋、失败的婚姻和冷漠的兄弟姐妹们。
感到死亡的恐惧的人经常下意识地在梦中得到救赎。弥留之际,梦中充满意象和隐喻——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自传《魔灯》也是一个例证。对于一个自知来日无多的人来说,梦成了一种自我催眠,一种和世界达成和解的手段。在梦中,生和死、青春和晚年、过去和现在都逐渐失去了向度,趋向平和。如果没有像哲学家一样在五十岁的时候知天命的话,临终前做一个梦,或许还能跟哲人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