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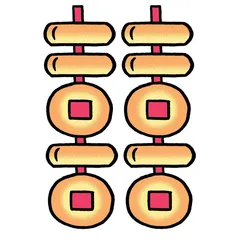
图◎陈曦
尼采说:“在最高哲学类型的事情中,一切已婚者都是可疑的。”强制婚前医学检查的倡导者说:“比一切已婚者还要可疑的,是一切企图办理结婚登记者。”
自2003年新《婚姻登记条例》将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变为自愿之后,重新恢复强制婚检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部分人大代表还把恢复强制婚检的议案带到了全国和地方的“两会”。现在,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黑龙江省上月颁布《母婴保健条例》,规定重新实行强制婚检制度,即“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就像强制婚检那么刚性─—新生儿缺陷率因取消强制婚检而不断攀升。黑龙江省颁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婚前医学检查率由强制时期的75.79%下降到目前的0.43%,该省每年约出生1.8万名缺陷儿。另外,近两年传染性疾病出现蔓延趋势,特别是乙型肝炎、梅毒等母婴传播性疾病显著增加,严重影响了孕产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
各地恢复强制婚检的依据都差不多。固然,这8万名缺陷儿跟强制婚检的废存之间是否果真存在必然的关联,婚前医学检查是否真能把婚后的缺陷儿扼杀在萌芽状态,强制婚检的复辟又是否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力的挤压——一切就像《新京报》社论所质疑的那样:“在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前提下,一个已经被取消的权力为何被轻而易举地恢复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生孩子、医学、遗传学、统计学以及政治伦理学等专业问题,我知之甚少,也就没有什么好深思的,倒是想起《言言斋性学札记》里的一段话来:“希腊地少人多,势难主张生育,所以宥恕自身妄用同性恋爱诸事,且不罪杀害婴孩者。犹(太)民尊崇上帝,《圣经》中令其繁殖,是以男子不娶为大耻也,多妻为常有之事;手淫者与同性爱者,为社会所不齿。此古时先知未临世以前事也。先知临世以后,始禁多妻之制,然仍赞成重婚重嫁,因国大民稀,非人口增加不可之故。合众(美国)性事,介于希犹之间,国法罚犯奸者。然纽约州1923〜1933年10年内,男女通奸之案共5万件,此外未告发者不知凡几,可见国人未能全守单夫独妻之主义。又重娶重嫁,不作奸淫论,故每岁离婚之案约50万件,而国中男女离婚者之全额,其数已达800万矣。余曰:国大粮多,律不注重贞操;人众粮少,律必严禁奸淫。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强制婚检之废存,一如性之伦理,莫非亦“一经济问题耳”?怀疑他人身上有病,实为自家囊中羞涩。强制婚检和中国的诸多弊端一样,都是因为穷。也就是说,强制婚检的全部意义都是经济学的,在于减少耗费在缺陷儿身上的社会成本。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右派认为此乃事关宗教、伦理的天赋权力和神圣职责;左派则相信这是人类所做的一桩蠢事,是资本家为了不断拥有可供剥削人口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自由主义者觉得,婚姻和民主一样,都算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生孩子就像一人一票的选举,可赞成,可反对,更可弃权。显而易见,恢复强制婚检无法得到上述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凡是左中右三方都不能认同之事,通常都可归类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即便强制婚检对预防缺陷儿出生确实有用。本来,生物学上不可避免的一定比例的缺陷儿人口,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生孩子,不论是为了延续种族还是扩大再生产而制造“工具”,只接受合格品而拒绝一定比例之“次品”,并无任何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可言。
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家庭一时都负担不了“等外”缺陷儿的“额外”开支,强制婚检认了也就认了。若坚信以强制婚检把一部分“可疑男女”挡在婚姻门外的做法一定可以减少社会成本,也许就会出现哈耶克所谓“当政府试图通过替人民做主实施社会控制(如人口政策)时”的那种“出人意料的后果”。我设身处地地为那些婚检不合格者想过,其面临的“不太出人意料”的个人前途,无非以下两种:
一、我国性别比例原本就严重失衡,据黑龙江省计生委统计,该省平均每年男婴出生数量要比女婴多1万人左右,恢复强制婚检,有可能在1万名理论上的男光棍之外为该省新增若干数量的强制性新光棍,男光棍之外,再添女光棍。自《光棍》一书问世以来,光棍多,麻烦大,已成一时之显学:“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
二、因强制婚检而终身不能嫁娶者,即便一辈子克己守法,保证不做恐怖分子,更没有任何非法性行为或性行为错乱,却不能保证自己绝不会因缺乏正常性生活而患病,主要包括前列腺及各种妇科疾病。届时,前来为这一部分社会成本(包括这一部分孤寡人口的养老开支)买单的,与当初拒绝付账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么? ■ 经济生孩子性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