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第二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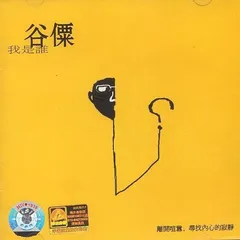
书非借不能读,唱片非买不能听。有时候,即便是买来的唱片,也未必就能听下去,物质贫乏的年代,什么都如获至宝,30年前,《桐柏英雄》这本小说我看了至少四遍,因为那是我能看到的惟一一部小说。现在,到处都是文字,到处都是物质,所以,对这些东西的消费越来越停留在占有的层面上,先拥有它,至于是否去阅读、观看、聆听、思考,似乎都不重要,拥有的过程远远比欣赏的过程有快感。时间是有限的,单位时间内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意味着你去欣赏某一样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
以听唱片为例,每周我能拥有的唱片大约有十余张,但是真正听下来的少之又少。跟一个喜欢电影的朋友聊天,才知道他看DVD的时候也基本上是按住快进键浏览。一张唱片,我基本上是听前三首,如果这三首歌还不能打动我,基本上我再也不会去碰这张唱片。我知道,现在做唱片的人都会把最好听或者他们认为最吸引人的歌曲放在前三首,如果这三首歌都不能听的话,那这张专辑就可以扔掉了。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也难怪,现在唱歌的人、做唱片的人心思都有点不对了。
有时候,要买一张全然不知道的唱片,是需要勇气的,但同样是被暗示的,因为封面去选择一张唱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谷僳的这张唱片《我是谁》大概就是封面让我动心买下的,管他爱谁谁。
听谷僳这张唱片,第一个判断是他肯定不是北京人,北京人玩摇滚都很复杂,生怕自己落下什么,他的音乐很简单,用一些很“专业”的媒体眼光来看,编曲还有点过时;第二个判断是他肯定是北方人,听上去不是太软。这张唱片我一口气听完,这是我半年来头一次把一张中文唱片从头到尾听下来。倒不是这张唱片有多么让人惊奇,而是它整体上的那种朴素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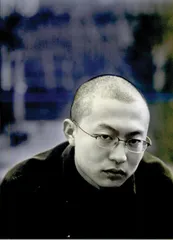
就像我越来越不喜欢崔健、罗大佑在他们的音乐里加入太多时髦的作料一样,有时候,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他们的强心针,来一次回光返照。对少年懵懂的音乐人来说,尝试一些新颖的手法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并常常迷失其中,自以为乐,这个很正常。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总是要兴奋的,总是要出点笑话的。但作为一些把音乐看得很透的音乐家来说,总跟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一样,说句好听的是锐意进取,不断创新,说句不好听的是对音乐失去话语权后的心理失衡。哪儿不行就补哪儿,有些时髦的东西未必就适合那些“过时”的音乐家,进补之后也不见得有效果。
依我的判断,谷僳的年纪大约在二十多岁,但是他并没有在他的音乐中弄出太多花哨的东西,好像跟现在流行的趋势不符,但这也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摇滚乐,这年头,想听到中规中矩的东西都很难。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的音乐做得很老练。
谷僳长得像窦唯,声音像朴树和许巍,甚至经历也和许巍类似,已经“星”相毕露,但他没有许巍的那种痛苦和绝望,也没有朴树的甜腻,至少,他是个有前途的歌手。
后来,从网上的一些介绍文字上才了解到,谷僳来自兰州,从小就喜欢摇滚乐,他说:“做音乐人要木讷一点,可以使自己在潮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还真是,现在做音乐的人都太聪明了,做音乐的商业目的性很明显,也就让音乐失去了味道。
那些时髦的音乐手法大可留给胡彦斌这类人玩,现在也不缺少这样的东西,平时刮进我们耳朵里的杂音太多,有时候,真需要这个歌坛出来一些朴实的声音。
说谷僳是许巍第二,倒不是说他的音乐与许巍有什么相似,而是许巍做了4张专辑,从一开始追逐摇滚的意义到现在那种无欲则刚的音乐境界,他花了10年的时间。而谷僳上来就有点后许巍的感觉,只是我不知道,这张专辑积累了8年的时间,他的下一张专辑会是什么样子,能不能把自己给后了?
西北人唱摇滚都有个特点,那就是能把歌写得很好听,比如郑钧、许巍,这大概跟西北地区比较闭塞有关,一方面最新型的音乐不会很快进入到那里,另一方面西北当地的民歌对他们的影响,郑钧和许巍都曾说过民歌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谷僳的歌曲写得也很好听,虽然在编配上时而民谣、时而布鲁斯,但是旋律的结构摆在那里。
说来也奇怪,以前说一个人靠谱那是对一个人的最基本要求,但现在成了做人的最高境界了;以前说一首歌好听那是对歌曲的最起码的要求,但现在要求歌曲好听已成了一个奢望。还好,谷僳歌曲还能让人听下去。■ 第二许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