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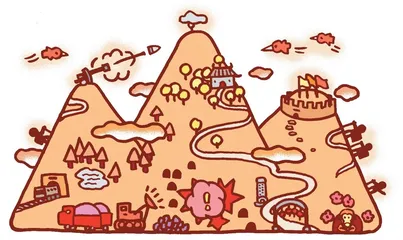
从前有座山,后来也有座山,事实上,一直都有山,当然还不止一座。但是,这种如山的事实却一直很难改变我于对山的观感,我的意思是说,从小,我就对山没有什么好感。
虽然我出生并长大的城市里并没有山,但是“厌山”的感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可能从山上滚下来,而是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官方话语方面,饱受“搬走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鼓舞;第二,民间话语方面,又屡遭“压在孙行者身上的五行大山”之恐吓。在以上两种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一个思想正派身体健康的青少年彼时如果对山这种象征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东西还会产生什么好感的话,思想庶几反动。奶头山,威虎山,许大马棒,座山雕,一座山就是一伙坏人,统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最后一个原因,与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一个思想正派身体健康的青少年的个人前途有关,我说的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上山下乡”。当然,如果有的选择,比较而言,我宁愿下乡,也绝不上山。
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坚信山这个东西的惟一功能就是坏人用来压在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对于这种又高又重又硬的东西,除了以“愚公移山”的坚忍革命精神移之而后快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相处之道。即便是爬到山的头顶之上去作威作福一番,政治上大致正确,终究缺了“移山”的快感。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虽然我幸运地逃避了上山下乡,亦不幸地没有参加过任何“移山”行动,不过,南方和北方的数座名山,后来都先后爬上去过,然后再爬下来,如此而已,无厘头之至。除此之外,惟一与山所发生的关系,算下来就只有登山棋了。登山棋,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今已不传(最起码“联众”上没有),是一种常见的掷骰子游戏。玩家以各自掷出的点数决定前进的格数,从大本营出发,以率先登上山顶者为胜。棋盘上布满了一次登山可能遭遇的绝大部分陷阱和挫折,雪崩、暴风雪、缺氧、缺食物等等。总之,一不小心踏错,轻者倒退数格,重的就得一猛子重返大本营,而今迈步从头越了。能否率先登顶,全凭手气。这个游戏虽然以1960年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革命英雄事迹为脚本,却散发着浓重的宿命论气息。
如今,到了“看山不是山”的年纪,对于“山”的看法,也一天天比登山棋还要宿命起来。“移山”比“登山”彻底,“入山”比“爬山”高明,无非都是一种此一时彼一时的策略,跟“靠山吃山”一样。比较中庸的境界,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停留在山脚下,悠然见南山,人和山命定的关系,本来如此。大山当前,你对着它振臂狂呼“我要上你”或者“我要入你”,都是非礼。在山的面前,人所能并所应采取的最自然、最环保的姿势,就是“仰止”,无论那座山是高是矮。你问他为什么要登山,喜欢登山的人总有一句能气死人的话等在那里:“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在你气绝身亡之前,不妨用尽最后一口气反问一声:没错,山就在那里,而且一直都在那里,但是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就不能left it along,让它“就在那里”好了呢?
爬到山的上面去,姿势上是父权社会的“传教士体位”,而“征服”则是一切登山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尼采在35岁上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迷上攀登阿尔卑斯山诸峰连续七个暑假之久。尽管他登上的最高峰科尔瓦奇峰海拔只有3451米,然而那种“巅峰体验”还是对他在这一期间完成《快乐的哲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偶像的黄昏》等主要著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换言之,至少在像阿兰·德波顿这种轻薄的作家看来,迷恋登山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超人”这种反动思想。
常识告诉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速度都有极限,这个极限在21世纪越来越临近于它的“绝顶”。极限之下,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远”,只好偷偷地打针吃药。事实上,与其说“见山就要爬,见海就想渡”是挑战自然并且自我挑战的人类永恒精神,不如说它更具有恋物癖的品质,即对于由长、宽、高构成的三维空间的难以自控的疯狂占有欲,麦克卢汉称之为“对疯狂的空间感觉着魔的形而上学的巫师”。
当然,隔行如隔山,以上观点在专业登山者看来,绝对是无稽之谈。我仅能发表的惟一看上去比较专业的意见,即在全球各峰皆已被人类相继征服之后,专业的登山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大概都只能以“人类的一小步,个人的一大步”视之。不过,这并不是说近日刚刚完成的那次攀登珠峰行动也同样没有意义,因为其目的乃是为了“重新丈量”。虽然丈量结果目前尚在等待中,但是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的是:那个数值一定会比原来的小,也就是说,当人的心气越来越高,珠峰肯定是越来越矮,最起码,登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一人一脚,就是踩也给生生踩矮了。■ 有座户外运动爬山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