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别人的母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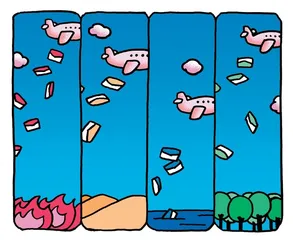
据英国《观察家》杂志指出,就“上瘾”行为而言,抽烟、喝酒、吸毒、赌博、购物等等,都已out了,生活方式变化和压力指数上升所催生的新潮品种,已扩展到上网、吃药、整容,甚至发短信上瘾。
总之,事态看起来十分严重,有报道说,去年5月,各国专家聚集新加坡,针对上述新瘾症的症状及出现原因召开了首届亚太戒瘾研讨会。
如果把“上瘾”简要描述为“严重地依赖或者迷恋一种事物,往往是心理不健全或者不健康的表现”,那么,不排除开会也是一种瘾,在某种意义上,它跟上述“新瘾”系列里的“发短信上瘾”十分相似。
《观察家》以25岁的伦敦女招待塔玛拉·克瑞里为例,说她不爱通电话,只爱发短信。平均每天要发短信175条,否则无法自遣。走着,坐着,躺着,路上,工作中,如厕时,都在狂发不止。惟一不发的那一刻是淋浴时。写短信也不用看屏幕,两分钟即刷满三屏。练就了“一指禅”的塔玛拉坚定地认为:“发短信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
更为变态的是,只要离开自己的手机须臾,塔玛拉就觉得不舒服。她不仅把手机称作“我的宝贝”,而且把手机插在乳罩里边,紧贴着肌肤,随时感应短信发来的声音和振动。用广东话讲,这不仅上瘾,而且还“上了身”。
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报告称发现“短信上瘾症”。临床上的描述大致是:“强迫症的一种,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总会产生短信出现的期待,如果到时没有出现,就感觉规律被打破,产生焦虑、不适应的情绪。”一句话,“全部生活都在一只手上”是一种病,得治。不过,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个人对此的看法相当悲观:其一,出于人性。和抽烟、喝酒、吃药、整容一样,食色性也之外,传播也是人类天性。短信上瘾,流氓成性,都不好办。再说,中国专家对防治短信成瘾提出的建议是:“控制短信聊天时间,正确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多参加集体活动。”这话听着特耳熟,跟“新婚必读”里防治性亢奋的对策差不多。
其二,出于切身经验。先报告一下我在母亲节这一天的“短信生活”。
公元两千零五年五月八日,“五一”长假刚过,母亲节追尾而至。我爱我妈,但她不在广州,遂打了个电话,致以亲切问候;我也爱我妈妈的妈,但她老人家不仅不在广州,而且也不在人世,阴阳相隔,手机或座机都联络不上,更发不了短信——很显然,元旦、春节、情人节、圣诞节的短信骚扰尽管惹不起,但是母亲节还是躲得起的,因为基本不关我的事,总不能楞充我的儿子或闺女,在短信里喊我一声娘亲吧。本以为可以清静一天,不料中午睡醒后一开手机,向我祝贺母亲节快乐的短信便如潮水般涌来,其中频率最高的是这条:
“今天是母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妈妈,祝她幸福、平安!更感谢她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说实话,阅读上述短信的时候,我的拇指发抖,鼻子发酸,顶上发指,几乎感动到想哭,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发信人的一片苦心:首先,今天和一年中的其余364天一样,他们实在是忍不住想用自己的手机向另一些手机发出一个问候短信;其次,他们是那么真诚、那么难以自控地想问候我一声,然而在母亲节这个苦于找不到给我发短信的任何理由的特殊日子里,仍然能挖空心思,煞费苦心地发出了那么一条。有条件要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发。
所以,借此机会,我要由衷地感谢所有给我发来短信的有心人(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曾见过她老人家一面),同时,更要特别感谢那些移动电话内容提供商(SP)们以及他们的那些不知名的短信写手(尽管他们中的所有人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当然,在此也一并问候他们所有人的母亲。
依依不舍地逐条删除这些短信时,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绝对是像我这样一天不发短信问候别人就浑身不自在却因某些日子的不方便而苦于找不到恰当理由的人的福音。我的意思是说,下个月父亲节那天,我会抢先发出这样的短信:“今天是父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父亲,祝他幸福,平安!更感谢他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举一反三:“今天是教师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历任老师,祝他们幸福,平安!更感谢他们教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今天是端午节,我用心灵之纸包成最美味的粽子,献给你的屈原,祝他幸福,平安!更感谢他从来没有养育你,从而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最为令人兴奋的是,一试身手最近的一个机会就在五月十七日:“今天是‘五一七’国际电信日,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套套,献给你的手机,祝它幸福,平安!更感谢你养育它,使它成为我手机的朋友!”
发短信,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吗? 母亲平安两性别人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