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天津市民文化
作者:舒可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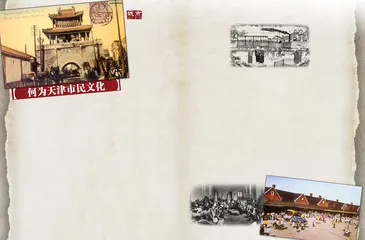
( 天津旧鼓楼,建于明朝,为天津三宝之一。古朴雄壮的鼓楼在1900年遭八国联军破坏(摄于1895年左右) 清末《铁道火轮车》年画,再现天津当年铁路运输的真实情景 1931年,东北人流落他乡,几百人挤在天津的一个大房子里 1935年左右,天津旧火车东站,其建筑仿北欧风格 天津旧维多利亚街上英国风格的建筑 造型独特的万国桥 民国时,在天津乘坐渡轮外出谋生的人们 )
五方杂处与300年的兵
历史上,天津因为有南运河、海河、子牙河的三岔河口而使它的漕运在北方经济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有人把天津的文化气质归结为码头文化。而天津史专家罗澍伟教授更强调,天津在不同时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主体,如果追溯到基础的市民文化,他主张说是一种“兵文化”——“因为当初天津虽然有繁忙的码头和大规模的漕运人口,但这里的码头不是在自然环境下由民间生长起来的,而是明朝的军事卫所制度的一部分。兵文化因此也只是今天天津文化的一个部分。”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他的四子朱棣镇守北京,朱元璋死后,1402年朱棣举兵打到南京做了皇帝。1404年,永乐二年,在直沽设立军事卫所,因为他当年举兵往南打的时候是从这里渡河,打了首战并取得胜利,如今他已经做了天子,所以这个卫所就取名“天子的渡口”,所谓天津也。在此之前,这里是大金的直沽镇、元朝的海津镇,这些设置都是军事据点。金元两代,这里的人口都是以军人为主。1988年罗教授参加一个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时,统计当时的官记,这个卫所有309户,其中40%是从安徽来的,60%来自江苏、山东、河北等15个省,之所以形成一个方言岛现象,就因为军事移民的原因。罗教授说,卫所制实行卫官世袭制度,天津现代望族梅贻琦的先祖就是天津的一个指挥使。因为世袭,这些军士以及后代都取得卫籍,成为永久居住者。建立卫城时的规划就是局部封闭,只管三岔河口一块高地上的卫城,总体开放,20%的士兵守城,80%在周围屯田,天津周围的大量地名都是“屯”,都是当年卫所屯田的痕迹。
设卫之后,朱棣为了解决北方边患,更是着力经营北京,1421年干脆迁都北京。随着北京对物资粮食需求量的扩大,天津漕运的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展。但明朝的漕运是军事化管理,专事漕运的军人称为运军,运军也是世袭的。运军得到官府的免税待遇,可以在漕运中携带特产南北倒卖,于是,天津渐渐吸引了很多为运军提供货源和销售货物的商人,天津东门外的海河码头由此才发展成了各路商人汇集的交易中心。
开始建卫所时,一个卫是5600人,后又建了天津左卫和右卫。明代后期,由于抗倭寇和防御后金,天津的军事功能有所增强,为加强防务,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卫所军人都有随营妻小,有的家庭规模甚至很大。非军事人口主要是那些往来于此的商人,但在有关天津人口统计的史料中,甚至很难找到非军事人口的记载。所以罗教授说,军队及军属是天津地域最早的基础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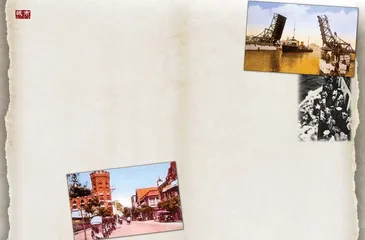 ( 天津旧鼓楼,建于明朝,为天津三宝之一。古朴雄壮的鼓楼在1900年遭八国联军破坏(摄于1895年左右)
清末《铁道火轮车》年画,再现天津当年铁路运输的真实情景
1931年,东北人流落他乡,几百人挤在天津的一个大房子里
1935年左右,天津旧火车东站,其建筑仿北欧风格
天津旧维多利亚街上英国风格的建筑
造型独特的万国桥
民国时,在天津乘坐渡轮外出谋生的人们 )
( 天津旧鼓楼,建于明朝,为天津三宝之一。古朴雄壮的鼓楼在1900年遭八国联军破坏(摄于1895年左右)
清末《铁道火轮车》年画,再现天津当年铁路运输的真实情景
1931年,东北人流落他乡,几百人挤在天津的一个大房子里
1935年左右,天津旧火车东站,其建筑仿北欧风格
天津旧维多利亚街上英国风格的建筑
造型独特的万国桥
民国时,在天津乘坐渡轮外出谋生的人们 )
卫所制在天津一直延续到雍正三年,因为这时的北方边患问题已经消失,天津的军事地位不再重要了。1725年,清雍正废卫设州,把军事建制改为地方行政。以此为线的话,天津600年历史中,有321年的时间是武卫之区,以军士为城市主体。清朝之后,不用卫所的军士了,原有的士兵部分改编为绿营,大部分则改变身份,专事屯田和漕运。或如罗教授说,很多军士占地为王,成为地痞性质的特殊集团,形成一时之风。
明代的卫城和县府的规制一样,网格状的街道走向,天津卫最初不过“城周九里”,不到5平方公里。从老地图上能看出这个卫所是个长方形的小城,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墙基上的四条马路,城墙早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被拆,这个城墙是中国第一个被拆的城墙。但这个城墙被拆不是出于经济和交通发展的需求,八国联军是把它当成军事工事拆除的。城墙被拆后,天津人感受到“肩挑负载可免阻隔绕越之艰”,“行人往来无拥塞泥泞之患”。城墙的被拆让天津人最早体验到了自尊与力量对比的失衡、中西之间的观念矛盾、传统与便捷之间的心理冲突。张利民由此把1900年八国联军的占领和义和团的失败看作是天津城市性格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清两代时,都有官员想开发天津的农业,开始时,用屯垦使驻守天津的军队自给自足。后来,不断有官员从江南请来农民传播水稻、番薯等,但都因为天津的地势与漕运关系而没有继续下来,依附漕运而活跃起来的商贸业到1860年开埠之前已经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有一份被研究者广为引证的《天津保甲图说》统计了当时天津的人口结构,开店铺的“铺户”、走街串巷的“负贩”和盐商等商业人口占到城市人口的54%,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佣作”、“应役”等服务业。天津图书馆天津民国史专家王向峰说,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当兵的后代留在天津的,他们一种是做小买卖,一种是当搬运工,一种是打把势卖艺,一种是在码头当把总,还有一种是拉帮结伙成混混。天津的混混分武混混、文混混、袍带混混,袁世凯的公子袁克定就算是文混混,他跑到上海时还曾被青帮尊为老大,后来他脱离青帮到天津做了寓公。罗教授认为,尽管天津有了这么多的商业人口,但兵文化对民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清政府对那种猛蛮之风毫无办法,一直到袁世凯“以杀治杀,杀杀人者”之后,混混作为集团才基本消失,但300多年堆积起天津的兵士民风不是能简单改变的。
近代工业忽起忽又落
如果说到1860年为止,天津的基础市民是以兵文化为基本气质的话,到了1860年天津开埠,城市的形态则变得复杂起来。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两国在天津划出各自的租界,后来数年,陆续有德国、俄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九国在天津划立租界,尽管随后各国租界里都开设了银行、商店、洋行等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但罗澍伟教授说,“天津租界其实是各国安插的政治观察所”。与上海的租界比较,上海是外国经济利益集中的地方,天津的经济腹地没有上海广阔,北方的经济活动也没有南方活跃,所以汇丰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天津只有分行。但天津是政治利益集中的地方,近代史上决定国家命运的诸多事变都在海河演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商人、专家建议在秦皇岛建立租界,因为天津港只是个内河港,它的大沽口很不好进船,而且还有每年的封冻期不能进行贸易。但当时英王维多利亚没有接受这些建议,选择天津,看中的就是天津作为北京门户的政治地理位置。虽然缺少经济环境,但政治上它可以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利益做保障。
最早的英、法租界划在海河西南岸的一块地势较高的狭长地带,1900年后的各国租界也都是沿海河的走向而建。采访罗澍伟教授时,约在当年英租界内的利顺德饭店。该饭店号称建于1863年,它的大堂里有一台闭路电视始终播放着一个记述它往日辉煌的短片,过道里有婉容在这里弹过的钢琴,溥仪用过的留声机,有美国总统胡佛在这里举行婚礼的照片,有赵四小姐在这里过24岁生日的照片,还留有孙中山住过的客房等等。此外还有黎元洪曾在这里设立过临时总统办公室,蔡锷、小凤仙在这里约会,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好像都曾汇聚与此。不过,现在正对台儿庄路的饭店大门和大堂都是近年加建的,穿过大堂走到木地板的地方才是原来建筑。原来的大门在相反的方向,对着大门是原来的维多利亚花园,为纪念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50周年而命名,现在叫解放北园,穿过花园就是市政府大楼,当年是英租界的市政厅。据罗教授考证,利顺德饭店建于1864年,1863年之说属于演义。1863年确实有一个英国传教士殷森德在附近建过一个“泥屋”饭店,只是个很简单的平房。利顺德饭店自认为泥屋饭店是自己的前身,其实不然。1888年的天津地图上明确标记着德商利顺德饭店。究竟为什么叫利顺德,有两个说法:一是现在饭店采用的,取孟子“利顺以德”之教诲;二是说,开埠后这里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西点店叫L·SH·D,饭店就用了这个音译,作为西点店音译为兰士颠。所谓德商,指的是德国人德璀琳,他是当时英租界的董事长。当时的各国租界都各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机构,英租界除中国人外向各国侨民开放,董事会是租界侨民直选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一个执行机构工部局,相当于市政厅。
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在管理上有一大区别,上海除了法租界,其余都是各国的公共租界,而天津的租界是各国独立的。罗教授说,这还是政治的原因:清末的直隶总督相当于影子内阁,当时的使馆与天津的租界里都设有领事馆和总领事,他们为避免直接和清政府打交道的诸多麻烦,直接和直隶总督或北洋大臣打交道。当时的外国人都知道,想办的任何事都得先见过李鸿章和德璀琳。曾经担任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是李鸿章最重要的政治顾问,他的利顺德饭店曾深入介入中国的政务,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是它的股东参与投资建立的,1886年从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也是饭店股东说服李鸿章修建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北洋水师的战舰“利顺号”,是利顺德捐赠的。德璀琳参与了兴办北洋海军等重要的国事,甚至被派去日本代表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被日本拒绝才没去成。
1912年中华民国时天津废府设县,而后的北洋政府所有总统总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出来的,4位总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天津于是成为一时的权力中心,也成为清末新政和洋务运动的中心。晚清时,官府在天津开办了很多工业,如开平煤矿,洋务运动中的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在采访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美云教授时,她比较了天津和上海两地的民族资本状况,“上海的外国资本势力大,民族资本是生存在外国资本的夹缝中,而天津的民族资本没有那样的压力。这又与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的不同功能有关,天津虽然有了租界,外国资本却不多,英国、美国虽然也有一些商业资本,但规模都不大,实业更不多。法国也同样,他们都经常办一些展览会,展示他们的最新产品,为的是向政府推荐,在中国范围推广”。
天津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城外,北门外是南运河的北码头,东门外天后宫处是海河的码头。1912~1927年间,天津的工商业集团已经形成,原来集中在老城区的东北角,北大关、估衣街的商业区,在这个期间沿和平路向南移动,移到了法租界内,以劝业场为最活跃的中心,劝业场内有卖场、戏园子、说书的,其中商人都是有一定实力的“门市”。
到1936年时,天津已经有89个同业商会,商会的兴办是1904年从上海开始的,天津从1918年开始有同业商会。1928年,国民党曾要求解散商会,成立有官方控制的商民协会,上海很顺利地成立了,天津虽然也成立了一个,但一直没有成气候,后来不了了之。问及原因,宋美云说,因为天津商会的势力很大,但这不说明天津的商业力量本身强大,是和天津商人的来源有关。天津的民族资本多属于高官资本,比如纺织业的六大纱厂都属于官僚资本,北洋政府的83个高官在天津投资办厂,所以这些商人是官商。即使在他们下野后,一方面还保留着深层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参加议政,很多人被推举为议员,他们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他们经营的近代工业使天津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大量的产业工人进入天津,人口一度超过北京。
30年代以后,天津的地位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1928年天津虽然废县立为市,表面上行政级别提高了,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北京移到了南京,江南财团的势力支持并左右着政府,黄埔军校的学生成为政府的基本力量。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量日本资本注入,控制了纺织业、面粉加工、煤矿业等,6年内,日本就兼并了原来的六大纱厂。宋美云教授说:“这给天津的中外投资者一个信号,日本的第二步将是占据天津,所以,很多投资者纷纷迁往上海或香港,剩下的工业、钢铁、电信很快就被纳入了日本的军事工业体系之中。1937年以后,日本在中国的总指挥机构设在天津,把天津作为整个侵华的基地,这进一步压抑了天津的发展。有很多大企业、大银行抵抗不住日本的压力都迁走了,如范旭东的化工集团,这是中国第一家化工企业,第一个化工研究所,日本人要兼并他,他抵不住,就搬到了重庆。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等也都相继迁往上海。所以说,天津的商业社会并没有真正发展成熟,就被日本压抑了。”
罗教授进一步认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天津定位为老工业城市,基本上是利用原来的资源,而没有新投入。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154个国家重点项目,北京有10个,天津一个也没有,原有的基础还有一部分支援了三线。1958年,天津改为河北省会,不再被认定为中心城市,一直到1968年才又改为直辖市。但天津已经从中国的第二大现代城市降下来,到今天也还在缓的过程中”。
寓公的乐与悲
天津是一个被迫承受了西方现代化的典型,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占有诸多第一,如1888年欧洲刚有的有轨电车,1906年天津就有了比利时商人铺设的有轨电车线路,把租界和老城连起来。有轨电车历史是中国第一,比上海早两年。照相馆、电影院也进了老城,德璀琳在李鸿章便宜批给他的一块200亩的地皮上建起了西式的赛马场。后来这个赛马场倒是有不少市民参与,但不是初建时的消闲,而是为了赌马。张利民说:“实际上,租界并没有让天津市民真正感受和接受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观念,因为租界和华界几乎不搭界,它和上海的租界不一样,上海中西交往比天津顺利,天津市民的抵抗情绪一直很重,为洋人代理商业活动的买办也多是广东和宁波人,所以天津尽管也有买办,但没有买办文化。一是因为这里的租界主要是政治功能,二是因为北京的政治势力给市民的影响力更大。”王向峰补充说:“兵文化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取媚洋人,即使是后来的商业、工业移民也多是燕赵之地的古朴农民。有一些表面上或物质上欧化的人也不洋气。”追究历史,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天津的三次沦陷——1860年的开埠就是英法联军攻入天津的结果。1900年的八国联军再次打进天津,统治两年,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八国联军毁了华界,义和团毁了租界,导致租界更大规模的扩建。1937年,日本又占领——这三次沦陷中,外国势力给天津人更多的是受辱的感受,抵制是最自然的情绪。而天津的另一个重要人群,清朝遗老,在天津的租界里做着寓公,在社会上做着坚守传统的榜样,清末重臣华世奎本是天津望族,虽然有祖屋大宅,后来也在租界置房,他在1927年组织崇化学会,请宿儒传授国学。而今天的读经运动又从天津发起,这与百年前的历史是否还有因果联系,有待专家论证。
开埠后的天津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层:洋人、高官巨商及百姓。租界开始时的范围就不小,后来又有三次扩大,开始是政治的结果,后来租界经营地产,他们私下购买大量土地,然后逼迫政府认可,面积远远超出了华界。洋人对租界内建筑物有严格规定,如五大道地区的住宅造价不能低于3000两银子,其中必须有不小于2500立方英尺的房间,10岁以上居民的居住空间不得小于400立方英尺,极为详细。他们给天津带来了很多西式的建筑和物质消费,但按上述原因,这些都没有真正改变天津的社会气质。真正给天津注入了别样风气的是在天津做寓公的下野高官。
王向峰带记者到原英租界的五大道,沿路数一个个小洋楼原来的主人,个个是在近代史有一笔细账的人物。王向峰收集了两千多张天津的老照片,在《快报》上开有介绍天津历史人物的专栏,他罗列出有北洋政府的5任总统,7个总理,40多个总长、次长及各地总兵之类的北洋高官、大小军阀都在天津置宅,还有不少在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如阎锡山、张作霖、马占山,顾维钧等。以溥仪、庆亲王为首的清朝贵族加遗老遗少也纷纷迁居在租界;还有次一级的,如袁世凯的警卫处长雷振春等等,抗战英雄吉鸿昌也曾住在这里。他们之所以选择到天津做寓公,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北洋政府的高官几乎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出来,或者留过洋的,与留学国有紧密联系,虽然下野,天津租界仍是他们政治生活的夹缝,他们的根基势力也在天津。
罗教授说,这些寓公90%受过传统教育,即使留过洋,也天然地屏蔽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他们的好恶影响了天津的文化气质,影响了天津的价值观。寓公的消遣是天津娱乐的主要动力,这些时期的寓公,或是在政治漩涡周旋中败下来的政客,或是失去往日威风的遗老,他们都支持了消闲俗文化的繁盛,而那种轻松、讽刺的说唱也适合陆续涌入的下层劳工的口味。80年代曾出版过一本《荣庆日记》,荣庆是清朝的一个王爷,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在天津做寓公的生活,每天的一般活动就是听戏、听梆子,看杂耍、看电影,他代表了天津广大的专业听众,既有闲又有钱捧角。30年代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就是天津的《三六九画报》和《立言画刊》评出的。他们虽住在租界,但消闲却常常往华界去,这也刺激了租界内华人经营的场所发展本土的消闲娱乐,而没有欧化。
历史上政治活动的舞台虽不在天津,但从它最初的设立到后来的种种动荡或发展都是那个前台的结果,或是为前台的活动做准备。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建立始自天津,严复翻译《天演论》是在天津,他主编的《国文报》也在天津,其中有很多激烈的维新言论,但这些领风气之先的事情对其他城市的影响似乎要超过对天津本地的影响。天津,一直缺少本地的利益,本身的力量很难体现出来,地方的独立意识明显弱于上海。加入了那些特殊身份的寓公后,天津造就了一种享乐、旁观和评说的风气。寓公身上遗留的官气和下层百姓的兵气都不支持传统文人精雕细琢的趣味,也对新鲜的事物缺乏敏感。有人说,兵文化是排斥变化和动荡的,而失意高官本身就是动荡的结果,他们对变化总是自然地排斥。
王向峰感叹说,“谁是天津的主人?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是个借地方,所以没有很强的责任感,时间长了,变成一种很特殊的忧郁”。■ 中国近代史清朝市民南京饭店王向峰日本政治何为文化天津历史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