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头去尾的好莱坞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有人说历史总是要由获胜者来写,这话是对的,除非要写的是好莱坞的历史。哪里没有失败者,哪里就没有历史。小说家菲兹杰拉德曾经身揣一支钢笔闯荡好莱坞,但是颇为不顺,他在其未竟之作《最后一个大亨》中像是在为自己不成功的剧作家经历辩解:“你要么像我一样对好莱坞想当然,要么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横加鄙夷。好莱坞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能是雾里看花,浮光掠影。只有不超过半打的人在头脑中能将等式的两端都装下。”大卫·汤姆森拿他的“等式两端”作书名,写了一本《等式两端:好莱坞的历史》,“等式两端指的是电影所包含的艺术跟金钱的数学、美学跟吸引观众的算术,甚至包括能解释电影如何指引观众的想象和梦想的神秘公式。他试图以一本书的篇幅,向读者呈现一部历史,一场魔术表演,以及形形色色的骗子、俗人和无赖,谋杀和权势,商业成就和无数被感动的观众,艺术和庄严”。
写好莱坞历史的作者就得是大卫·汤姆森这样出生于英国、住在洛杉矶、写过十来部书的评论家,跟他的写作主题的距离适中,足够熟悉又不会陷入其中。他要探究电影到底是商业还是艺术,还是两者都不是:美国电影会不会像是大卫·塞茨尼克的《飘》,一切商业活动都受制于其制片人的偏执?还是像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一切艺术的推动力来自导演的偏执?商业跟艺术的冲突令汤姆森为之着迷。他认为,商业是你爱去憎恶的东西,你也憎恶爱商业的人,但是你又不得不爱商业,因为好电影往往都是由贪婪、残酷、愚蠢的激情催生出来的。
在汤姆森看来,电影是有魔力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曾经将电影称为“墙上的狂乱”,汤姆森则视之为甜蜜的非理性,疯狂将我们吸引至银幕中表现我们隐藏的欲望和恐惧的玄想世界,他说电影的把戏与其说是艺术,还不如说是蛊惑我们大脑的妖术。电影不仅是讲故事:“它是一场木偶戏,或者一片药,让我们得以分享逼真的他者生活。虽然他们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不是我们本来就能够得到的。”在书中,他要研究初期的电影制作人像葛里菲斯和卓别林怎样建立了电影的基本原理,声音和色彩如何改变了电影的活动空间和感知,电影怎样影响了我们对爱情、战争乃至室内装修的理解,一些著名电影如何包含或者被包含在我们对社会更深广的关切中。
对于这样一本主题及其庞杂的著作,容纳哪些、舍弃哪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个人趣味和写作惯性。汤姆森对好莱坞历史的处理可以说是掐头去尾,他认定,最初的跟最新的电影都无足观。“作者在写作该书开头部分时一直在等待着声音的问世。”以往的电影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都在称颂电影默片,认为那才是像芭蕾一样的、纯粹的电影,对话让形式支离破碎。连那些默片跟有声电影都拍的很好的导演也这么认为,比如希区柯克。对此汤姆森揭竿而起,弹落了几代人的成见:“如果说默片中有艺术的话,这么点艺术也太依赖于做作的舞蹈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戏剧风格了。从最伟大的默片中我感觉到的也只是解放的前景,一种囫囵的媒介即将圆满。”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电影让汤姆森不得不为电影致上挽歌,他认为对特技的强调和特许经营的电影使得主流电影,那些表现人类的情感和向民族进言的电影日益边缘化,好莱坞日益以票房收入来衡量电影是否成功。他感叹美国电影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1947年,美国人口不到1500万,电影院每周卖出1000万张票。如今美国的人口是2700万,每周售出250万张票,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10的美国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 《等式两端:好莱坞的历史》 )
( 《等式两端:好莱坞的历史》 )
在他看来,在电视、电子游戏和电脑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不会被电影感动,他们更喜欢动作、奇观、新奇,只愿意看到超出现实的电影画面。而他们当年猫在电影院的父辈所看的则是,无论经过多少虚幻、放大,都还可以从中感知到、辨认出真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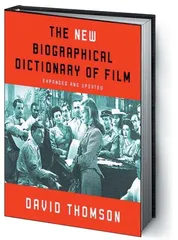 ( 上右: 《新电影人物辞典》 ) 好莱坞掐头去尾汤姆森
( 上右: 《新电影人物辞典》 ) 好莱坞掐头去尾汤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