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建房:一次房地产开发模式的理想主义实验
作者:贾冬婷(文 / 贾冬婷)
 ( 于凌罡 )
( 于凌罡 )
一群理想主义者的盖房梦想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见到合作建房的发起人于凌罡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信心满满,“这个‘东风’,就是土地”。此时,距离于凌罡在网上他的描绘“合作建房”蓝图已经一年多了,梦想正一步步变得触手可及。
2003年12月1日,联想工程师于凌罡以“蓝城木鱼”的ID在网易、新浪、搜狐、绿野等十几家网站发出帖子,号召说,我们大家可以组织起来,集资盖楼,让开发商靠边站。
于凌罡计划招募资金500份,每份合作资金15万元,利用这15万元,每个业主可以从银行贷到22.5万元,用来支付买地和建房的费用。参与者共同出钱注册一家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然后聘请设计部门、施工部门、物业提供者等专业团队,自己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楼。楼建好后,因楼房的底商和附属商业设施也属于业主们,可以用从中获得的租金收入来冲抵那笔银行贷款。
这栋梦想中的楼已经有了大概的模样:地处北四环或东四环,板式跃层小户型住宅楼,500多户居民,地下2层公共设备层,地上12到15层。每户层高高于4.8米,可增建跃层,成为复式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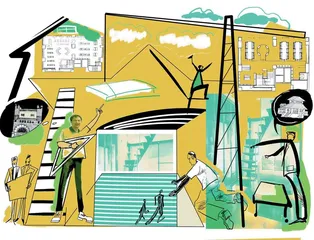
从第一个回帖者开始,于凌罡的支持队伍日益壮大。目前,报名者已经达到了预设的500人,其中包括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房地产开发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他们组建了四个小组,行政组、财务组、法律组及工程组,1月15日,由200人组成的联盟正式成立。于凌罡说,如果明年5月能顺利拿下土地,房子有望在2006年入住。
于凌罡的家已经成了“合作建房”的公共办公室,每天咨询的电话、人流络绎不绝,他说,这事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给淹没了,周末都没时间背包出去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穿着一件“绿野”户外俱乐部的T恤,上面印有“自助、友爱、生活”字样。或许,绿野绕开旅行社、自己设计路线背包出行的“自助”精神,正与合作建房的思想暗合。事实上,绿野的众多“驴友”后来也成了合作建房的“铁杆”。
为合作建房专设的“蓝城”网站上,有个著名的ID“李大福”,就是这么一位“铁杆”。李先生是位城市规划设计师,他说,合作建房更大的意义在于给政府做个试验,让政府调整目前不合理的房地产制度设计。
对众多支持者来说,这个方案最显而易见的吸引,就是省钱。于凌罡算了一笔账:由于是非营利集资建房,这个项目可以省掉购买普通商品房时需要承担的四笔费用——开发商利润、广告销售费用、机构维持费用和项目贷款利息。这样算下来,自己盖的房子比买地产开发商的房子大约便宜20%~40%。而且,于凌罡认为,一个房子的价值不是它的房价本身,它应该是“房价+物业+底商”三者价值的诠释。而现实是,物业和底商收益传统上是由开发商占有的,“房产中2/3的价值无形地流失掉了”。合作建房的住户同时又是出资人,将享受物业和底商收益。
“之前,一旦我选了当中一个楼盘,我就被套住了,开发商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就要无条件遵守他的条件,这是我买房当中最大的一个苦恼。”正如顼文瑞先生所说,合作建房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和DIY的乐趣,也是吸引很多人加入的重要原因,“我可以自己设计,自己装修,我喜欢研究户型,喜欢研究结构,喜欢研究色彩……”
乌托邦的现实困境
一套可以节省20%以上投资的房子,地段、户型,甚至邻居都可以自己选择,一个让购房者决定一切的新模式,看上去很美。但当这个理想离地面越来越近,现实的风险却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将这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放到现实社会中,它将面临与开发商同样的拿地和融资的风险,在地根银根日益趋紧的环境下,于凌罡拿什么去跟深谙水性的开发商们竞争呢?
土地,被于凌罡形容为需要借力的“东风”,他承认,这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一环节不仅涉及到土地的地段和价格问题,还要和房地产开发商一起参与土地竞标。不过,他觉得自己在价格上还是有竞争力的,因为开发商的前期投入全面要靠自己,而合作建房,前期的钱是每户按规定数额累计起来的。
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舒可心对此表示怀疑,“土地市场中除了有公平市场竞争,谁有钱谁拿地以外,还有大量黑幕交易。在资金的优势上,或许于凌罡不亚于开发商,但在一个任何事情靠关系推动的不完善市场上,于凌罡就更不具备优势了。”
与这些外部风险相比,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在一个500人组成的“公有制”乌托邦里,如何保证整个系统的透明而高效的运转。于凌罡计划民主选举50人作为公司股东来托管500人,在系统内部,他制订出一套人事权、行事权、审核权“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代表全体合作者的股东大会是决定机构,行政权交给股东聘请的工作人员,另外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负责财务监督”。于凌罡精心设定了各项细则,“比如说提案制。有任何建议,都要在网上以规范格式提出,然后经过审核、公示,决议是否通过。这样可以确保公平”。
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平带来的效率问题。“一个商业企业是民主决策来运作,不符合商业规律,商业活动一定要有一个高效率的管理层。每一项决议都由50人,甚至后面的500人去决定,它的效率能不低下吗?”舒可心说,“而且现实中不出纠纷是不可能的。出了事,谁可以承担责任?公司法也保障不了所有人的权益,只能保证50个股东的权利,商业风险是很大的。”
在于凌罡的设计里,房子可以节省20%到40%的成本,但有些成本却在设计之外,现实之内。比如公司的管理成本,尤其是将商业公司民主化管理,另外,房地产行业里的巨大隐形成本,算下来,房子的价钱就大大打了折扣。而且,加入合作建房团队的,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每个个体节省下来的金钱成本,却可能被耗费的大量时间成本所抵消了。
“为了房子还是为了理想生活?”舒可心说,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单纯为了房子,就大可不必了,最终并不一定会省钱。做不成,还会把前期成本搭进去”。
舒可心将他们形容为一群搭积木的孩子。“这是一群‘孩子’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做实验,意义在于,通过这次实验,有机会学会民主地讨论事情,学会共同承担风险。只不过,与过去许多政府部门拿财政的钱做实验有所不同,‘孩子们’这次即使失败了,也只是花自己的钱。这一群人是有共同精神需求的人,他们主要的产品是精神上的需求,副产品才是一个房子,让他们随便摆弄的一个房子。”
挑战房地产开发模式?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南京、厦门也相继出现了“于凌罡们”,挟着大同小异的合作建房想法在网络上迅速蔓延。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建房实验,放在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大都市环境下,放在一个房产泡沫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是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观念震荡。
虽然业主维权斗争一直未断,但之前都是在现有房地产开发模式框架下的反抗,于凌罡的合作建房计划,却是第一次针对模式自身的挑战。“合作建房”能发展成为一种与现有模式并行或者替代的新模式吗?
面对各地的追随者们,于凌罡保持了一份清醒,“外地可能没有北京的政策优势,另外,也没有这么多媒体支持”。事实上,于凌罡几乎每天都要跟各种媒体打交道,通过媒体将不断更新的想法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借助整个社会的关注和监督,推动一栋楼的建成。这让于凌罡节省了大笔招募的广告费,也将风险很好地分散出去。但是,第一个建楼的人媒体会关注,志同道合的人会被吸引,第二栋、第三栋呢?它们面临的困难,它们的建立或消亡,还会有整个社会去推动和关注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于凌罡的实验即使成功,也只是一个特例,很难被大面积复制。
“为什么地产开发以开发商的形式运作?这是社会对一种风险补偿机制的设定,比如土地贬值、股东退出等等,合作建房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靠个人信用,很难积累参加者的信心。”华高莱斯房地产咨询公司董事长李忠认为,“合作建房一样面临土地和融资等外部压力,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问题的解决没有作用。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式,不是规模经济,也不是一种符合社会分工和商业规律的模式”。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合作建房,有人想自己攒房子?“或许这次尝试是理想主义的游戏,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房地产市场现存的问题。“是不是太多考虑税收积累,土地资源的买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对房地产商的管制、对市场的管理,是不是有值得反思之处呢?”舒可心说。 一次合作房地产开发模式实验购房理想主义房地产业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