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当咖啡桌的《纽约客漫画大全》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于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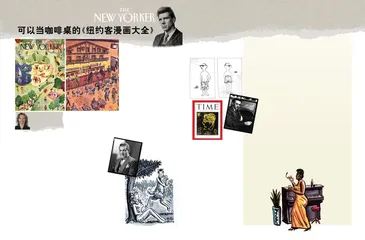 ( 《纽约客漫画大全》的总编辑鲍伯·曼考夫
《纽约客》创始人
哈罗德·罗斯
《纽约客》最早的漫画家彼特·亚诺及作品
詹姆士·瑟伯的漫画看似简单,但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对白。1951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
)
( 《纽约客漫画大全》的总编辑鲍伯·曼考夫
《纽约客》创始人
哈罗德·罗斯
《纽约客》最早的漫画家彼特·亚诺及作品
詹姆士·瑟伯的漫画看似简单,但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对白。1951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
)
《纽约客》以前出过好几本漫画集,比如《纽约客七十五周年漫画集》;《纽约客的艺术,1925~1995》;《纽约客真爱漫画集》,但最近出版的这本,叫《纽约客漫画大全》(The Complete Cartoons of The New Yorker)。凡叫某某大全,都不大让人信服。《纽约时报》说:“一看到这样的书名,就像见到《流行歌曲大全》或者《美人大全》一样,太幽默了。”这本漫画大全有655页,68674幅漫画。按说是本在旅途中,或入睡前神志不清时翻阅的书,但由于太厚,被称为“只能放到咖啡桌上,或者干脆,装上腿,它就是个咖啡桌”。
但翻阅这本漫画大全,可以揪出许多回忆,关于漫画、《纽约客》、甚至美国历史。1925年《纽约客》创立时期,正值喧嚣的“爵士时代”,欢呼战争落幕、经济复苏的庆功宴永无休止。第一期就出现了皮特·亚诺(Peter Arno)的一幅黑白线条漫画:一个扎着马尾的绅士,一个贵妇,他跳着当时流行的查尔斯顿舞,她却已经半卧床榻。她叫着:“老天呀,女人们,这是什么社会结构?”《纽约客》这本当时闲暇阶级的消遣杂志,用“社会结构”表明,那个阶级不仅会玩,还会思考。
30~40年代,《纽约客》的漫画确立了两种基本风格。一种是拿自己开涮。主角都是中产阶级:男人一律穿西装扎马尾巴拎公文包,以示是个生意人;女人则戴着镶大花的宽边帽,鞋跟高过9寸。插科打诨的材料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娱乐、穿着打扮甚至怪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詹姆士·瑟伯(James Thurber),他的画风乍一看,是“给5岁小孩看的儿童画”,但胜在对白。一个公司老总翻着日历,对着电话说:“星期四已经被约出去了,永远不见如何,永远不见对你方便吗?”他曾经形容这种幽默“是种自我认同,甚至是自我庆贺”。《纽约客》的中产阶级读者们拿起漫画,发现自己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不仅不生气,反而洋洋得意:能嘲笑自己蠢行的人,都不是蠢货。《阿甘正传》不是说了:“干傻事的人才傻。”另一种风格的主角则是权势人物,他们可能是胡佛,也可能是罗斯福,总之是影响社会的大人物。一个建筑师站在大坝上,一个政治家喊:“水从这边来。”另一个政治家则指着相反方向:“水从那边来。”大萧条、“二战”,在这一时期的漫画中都可以发现点滴片段。
50年代的《纽约客》漫画风格更加简洁,标题、对白越来越短小,有时候甚至没有;可主题有点找不着北。“爵士时代”、大萧条、“二战”,这些喧嚣、轰轰烈烈的日子都过去了,眼前是死气沉沉、压抑的冷战早期。一幅周·德(Chon Day)的漫画展示了这一状态:一个矮胖男人持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另一只手却堵住自己的耳朵。他既不想听到枪响,也不想真的开枪,他就想缓缓劲儿。《纽约客》的漫画也这样,每期登着,却不那么精彩。青黄不接延续到80年代,突然间大家有钱了,世界也宽容起来。这时期的漫画形式更多样,题材也五花八门。当时最著名的漫画家Charles Addams为《纽约客》画了相当一部分阴森、如同恐怖小说般的浓墨画,后来被制作成电视节目《亚当斯一家》。90年代后,《纽约客》上的部分广告开始享用漫画待遇。据说这跟新主编蒂娜·布朗的革新政策有关,她信奉“对故意模糊新闻和广告之间的界限一事,毫无不妥的感觉”,她上任后一年,美国人人想在《纽约客》上登广告。现实依旧从那些线条画后探出头来:一个人在电脑跟前大笑:“在Google上看到自己,真是开心!”波波族流行时,名为“三个确定的事实”的三幅漫画:骷髅头下写着“死亡”;拿着小票的天使,翅膀上写着“出租车”;一个鬈发着羽毛装的人,举着小牌:“波波族”。翻开今年10月18号的《纽约客》,两小孩在草地上谈理想:“我想以后多挣钱,当总统。”
《纽约客漫画大全》的总编辑鲍伯·曼考夫(Bob Mankoff)说:“这本书展示了我们是谁,这80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里面不仅有美国历史,还有每位读者的个人回忆。”
这本漫画大全应该算作为《纽约客》祝寿的礼物,今年它将80岁。虽然《纽约时报》讽刺说,这书厚得像个墓碑,很有葬礼气氛,但大概没什么比漫画集更能代表《纽约客》的了。■
干吗模仿《纽约客》?
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原来是个地方小报的编辑,1925年2月他在牌友的资助下创办了《纽约客》。本来要办一本幽默杂志,但他有从乡下带来的淳朴气质,杂志文风越来越文学化;他又很聪明,还比作家和智者们更擅长喝酒和互相吹捧,迅速把这本文艺气的消遣杂志和爵士时代、杂种曼哈顿、大众文化、阶级背景下的广告、电影、图书俱乐部、活页乐谱、小报和摩天大楼放在一起。《纽约客》有了雏形:时政、文学、诗歌、文化评论、幽默小品、漫画……什么都有;同时文章既有深度,又伶俐明快。他在主编位置上干了26年,一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副手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接替了他,在位35年。这两位性情都有点怪,但在杂志运行理念上很一致,共同执行了许多原则,比如“文章通顺好读,没有下流字眼”,“永远不写那些不愿意让我们写的人”,“不虚构,不编造”,“绝对不为任何隐藏的目的而刊登任何东西,或者写东西吹捧任何人、任何事,诱某人为恶,帮某人擢升,扯某人下台,纵容迁就私人朋友,或者徇私要挟,或者借机宣传”。符合上述标准的写作,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纽约客文风”。
但理想主义的威廉·肖恩,命运却是“起于《暴风雨》、经历了迷幻的《仲夏夜之梦》,最终的结局是《李尔王》”。1985年,缪尔·纽豪斯花1.68亿美元买下这本杂志,肖恩被赶出《纽约客》。继任的罗伯特·高特里勃不大招人待见,这时《纽约客》已经连续13年亏损。蒂娜·布朗被当成救星接任,她确立了个新规则:将贵族化和流行化结合起来。总之是既有品位,也不讨厌钱。杂志接了大批广告,增加了消费品引导栏目,杂志广告收入升了17%,每期发行65万份。但1998年《财富》的一篇揭底文章说《纽约客》一直在亏损,数额有1.75亿美元,蒂娜·布朗要负一半责。当年她离任,《纽约客》的专栏作家大卫·雷姆尼克接替。
当年威廉·肖恩被赶下台后,就有许多人感叹《纽约客》清新气质和绅士风度不再。“无法承受的轻浮和难以控制的坠落颠覆了美文和上流的品位所代表的悠久文明,喧嚣和骚动打破了致远的宁静。”还有许多让大家远离它的号召:“如果你被《纽约客》婴儿化了,离了它就不行了,变偏执狂,变傻了,被伤害了,停止抱怨吧,走出你的郁闷,走出这个玩偶之家,把门使劲摔上,一路哼着你忧伤的歌曲走进随便哪一家酒吧或妓院里。”但80年下来,《纽约客》已经是种风景和象征,“与洁净的指甲、大学、支票账户和良好的意图一样成为阶级标志的一部分”(作家约翰·列奥那德)。它挣不挣钱,自己看不看得懂,都没什么关系。
俄罗斯的《新见证者》不是最早模仿《纽约客》的杂志,但是模仿得最像。版式相似,栏目设置雷同,穿插漫画,新闻报道和文学、娱乐都有。《新见证者》读者群是“年龄在30~40岁之间,了解苏联时代却并不怀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2000年,中国的《作家》杂志改版,剔除了“中篇小说”,设置了地理,诗歌等栏目,有段时间它自称为“中国的《纽约客》”。但学者董鼎山认为《作家》还是文学气的,而不是综合或者时尚,作者大都是作家,并且形也不似。《书城》则是经过忽大忽小的改版之后,在2002年突然看上去外貌非常像《纽约客》。除了版式模仿,购买《纽约客》原版插图外,内容也宣称“再现文字之美”。《书城》据说曾经有一本落到《纽约客》的漫画总编鲍伯·曼考夫手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问:“这书跟我们的很像吗,卖得好吗?”实际上《书城》卖得不大好。■ 大全纽约咖啡书城可以纽约客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