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蛋化”的圣诞节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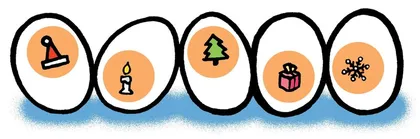
听到圣诞歌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购物,而且屁股后面有成群结队伸开手索要礼物的小孩追赶着嗷嗷待哺。这些2/4拍子的歌曲,还十分有助于营造购物的紧迫感,大包小包,外带一溜小跑。
除了节奏较为舒缓的《白色圣诞》之外,我认为大多数圣诞歌曲其实都变成了提醒购物的Jingle,这些歌曲的字里行间,似乎也不经意地留下了若干刺激购物的“端口”。当然,这并不妨碍Bing Crosby在1942年大卖500万张的唱片《白色圣诞》,本身更是长盛不衰的“圣诞商品”之一。
今年圣诞,鉴于美国的一些主要零售商“故意淡化圣诞节的宗教信息”,以“佳节快乐”等词语代替“圣诞快乐”,以迎合不同宗教人士的口味,加州“拯救圣诞节委员会”在网站上宣布:“一场冲着圣诞节而来、秘而不宣且欺骗众人的战争已展开,企图于圣诞节期间抹掉公众场所有关‘圣诞节’的东西”,听口气,似乎要向这些零售商发动一场“圣战”。此前,苏格兰圣公会曾于2002年圣诞在苏格兰各火车站张贴了一幅特别的圣诞海报。画面上,是传统的圣婴降生景象,而主角则是东方三博士中的其中一位。海报的刺点是:东方三博士的视线向下,骇然发现手上的“黄金礼物”仍然贴着售价标签。
用意也是反击圣诞节的商业化潮流。海报上有大字标语:“在这一刻,第一位博士才发现自己忘了把售价标签拿掉。已遗忘了其中精神?这个圣诞,不如到教会稍歇心灵。”
其实,无需劳动东方三博士显灵说法,更不用教会的警告,圣诞节早已经从一个神圣节日(holy day)蜕变为一个世俗的欢娱节日(holiday)。事实上,大多数的holiday本来也都源自holy day。2月14的情人节,起源于罗马“牧神节”,公元7世纪,基督教领袖以基督教殉教者瓦伦丁的名字重新命名。然而,“圣瓦伦丁节”之名虽一字未改,东方的过节者们现在却都在同一天晚上忙着安排各自的钱包为鲜花、巧克力以及烛光晚餐而义不容辞地“殉教”。
因此,对于大部分也过圣诞节的中国人,或者在中国社会调查所近期发布的问卷上明确表示“一定会过圣诞节”的那50%被访者来说,这个节日本身的“精神”和“意义”,基本上就属于“从来就没有想起,永远也不会记起”的事情了。但是,我发现和苏格兰圣公会以及加州“拯救圣诞节委员会”一样着急的,竟是中国的媒体。随手在节后的报上摘录几句,都是一派愤世嫉俗的腔调:“制造圣诞快乐和享受圣诞快乐的中国人,多少人真正明白圣诞节这个西方基督教最大节日的内涵?”“我们是否理智地想过:圣诞除了给我们带来商机外,还意味什么?”“西方圣诞节是一个被直接拿来的节日,不过它只被拿走了壳。这张壳被商业利用成精美的包装纸,裹在与其内涵并不相对应的商品身上,到处兜售。”就连友邦也惊诧,这一回竟在“圣诞节被商品异化”一事上出现了难得的英雄所见略同。平安夜那天,美国人Elizabeth Davnie在中国发表《圣诞节在中国流行真不可思议》一文:“圣诞节在中国流行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而据我所知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信奉基督教,也不明白这个节日的真正内涵。”
很显然,以实际行动“淡化圣诞节宗教信息”的阵营,包括了美国的零售商和中国的“圣诞族”,而与之对垒的“强化圣诞节宗教信息”阵营,除了加州“拯救圣诞节委员会”以及苏格兰圣公会之外,也包括了中国的部分媒体。对于后者来说,无论是看不惯中国人过洋节,还是批评过洋节的中国人“跟风,瞎起哄”,本质上,他们和西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样在乎“圣诞”的真意,“是否已遗忘了其中精神?”与“是否还不明白其中精神?”一样,都是瞎操心,因为过节的人都在忙着消费,中国的过节者还在乐不可支地互相发送中国特色的圣诞短信——“生蛋快乐”、“剩蛋快乐”,以“蛋化”越洋呼应了美国零售商们的“淡化”。
“蛋化”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是全世界圣诞商品的最大生产国,据说全世界80%的圣诞商品来自中国,其中又有60%来自广东。美国人购买的每10棵圣诞树里,有8棵是在广东生产。据说白宫专用的圣诞树,就是Made in Guang Dong。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人该不该学老外过耶诞节的时候,是否先不忙着提倡,也别急着反对——我的意思是说,就算全中国人民因种种理由都不该过圣诞节,至少应予广东人民一个实事求是的豁免,我的理由是:既然广东人民为全世界过圣诞节的人们辛苦制造并贩卖了如此之多的圣诞商品,这一天,起码也该休息一下,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权当是欢庆丰收还不行么?只要买卖双方都坚信“顾客就是上帝”,不管是宗教的也好,世俗的也罢,世上就没有什么不能过的节,更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节。■ 圣诞节中国人蛋化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