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造化爱几何
作者:鲁伊(文 / 鲁伊)

南开大学的学生自发来到设在学校的灵堂吊唁陈省身
12月3日晚7时,刚度过93岁寿辰的陈省身因病在天津去世。很多年前,和夫人郑士宁参观罗汉塔后,陈省身曾感叹说:“无论数学做得怎么好,顶多是做个罗汉。菩萨或许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罗汉谁也不知哪个是哪个人。所以不要把名看得太重。”然而,尽管芸芸众生对这位微分几何大师毕生致力的研究所知甚少,却并不妨碍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人们更多在哀悼一个传奇的、“好的数学”的时代的结束。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陈省身出生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下塘街。当时辛亥革命正到嘉兴,出生9天的陈省身便随全家逃难。他的祖母唐氏因此断言,这个孩子一生劳碌命。
陈省身的名字由父亲所起,典出《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陈父名宝桢,陈省身的阿拉伯数字和四则运算由他所教,他还从外面为儿子带回当时最著名的西方数学教科书《笔算数学》。1922年,陈宝桢在天津任事,举家北迁,11岁的陈省身插班进入扶轮中学。扶轮中学由交通部所办,陈省身的数学基础便在那时打下。
1926年,15岁的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师从中国第二个在国外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几何学家姜立夫。虽然陈的年纪在班上最小,他在数学上的天分却深得老师同学欣赏。很多年后,陈省身回忆说,姜立夫和张希陆(张伯苓之子)都喜欢让他作助手帮助批改卷子,每个月可以赚到10块钱。那时,10块钱可以买300斤大米,是笔相当大的数目。
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之一是数学家与教育家吴大任,他的表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的吴大猷。当时,吴大猷、吴大任、吴大业、吴大立这四个来自广东、在南开上学的堂兄弟,并称“南开四吴”。大学第一年时,陈省身与吴大任很少来往,快毕业时,两人却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吴大任属于那种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作业清清楚楚,考卷工整美观,相反陈省身却有点漫不经心,所以考试时候,陈的名次总在吴后。
陈省身与吴大任先后三度同学,友谊保持了71年。从南开毕业后,两人共同考取清华研究院,后来又都在汉堡大学研究数学。吴大任逝世后,陈省身曾撰挽联:“八里台畔,阿斯河边,永忆江湖;椭圆空间,积分几何,长留真理。”八里台是南开旧址,阿斯河流经汉堡大学,皆是陈吴二人旧游之地。
1931年,清华数学系的教授是郑桐荪、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是当时国内最强大的数学教师阵容。陈省身师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孙光远,孙的老师是著名的几何学家莱恩(E.P.Lane),1949年,陈省身赴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接替的正是莱恩的职位。
陈省身在清华担任熊庆来的助教,给本科生教授高等数学。1932年,他还当过清华录取考试的数学阅卷老师。那一年的国文考题由陈寅恪所出,其中一题为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满分者给出的答案为“胡适之”。但其实,最妥贴的下联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算学大师“祖冲之”。这个故事在当年的清华传为佳话,也足见数学系影响之大。
曾经有人问陈省身为什么选择数学,陈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说,他的手很笨,做不好实验,则理科之中,仅有数学可选。关于陈省身手脚笨拙的逸闻很多。吴大任夫人曾回忆说,在南开时,常常看到操场上练习开步走的队伍中一个人手忙脚乱,总不合拍,那就是陈省身。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师从陈省身学习拓扑学的吴文俊也提到过,经常看到陈省身用一个手指头打字,忙得不亦乐乎。和陈省身有同样毛病的是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的导师、美国氢弹之父特勒(E.Teller)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W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本想从事实验物理的杨振宁只好转攻理论物理,结果反而柳暗花明。
陈杨两家的渊源始于清华岁月,几代相交,情谊深厚。杨振宁的父亲是陈省身在清华研究院时的教授杨武之。在1934年陈省身面临毕业和出国问题时,杨武之给他的帮助甚多。当时,清华的公费留学一般派往美国,而陈省身希望去德国,跟从汉堡大学的几何学家布拉施克(Wilhelm Johann Eugen Blaschke)学微分几何学。在申请改派的过程中,杨武之鼎力相助,终于使陈省身得以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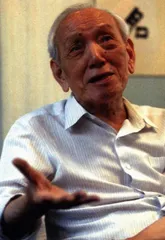
数学大师陈省身
在陈省身赴汉堡大学读书后,杨武之还撮合了陈省身与郑桐荪之女郑士宁的姻缘。两人于1939年结为夫妇,相濡以沫,直至终老。郑士宁本来学生物,与陈省身结合后,却当了很久数学老师。据说,40年代在上海时,一个邻家孩子拿一道中学几何题来请教陈省身与周炜良两位大师,两人都因一时不知从何着手而费尽思量,郑士宁恰好经过,却毫不费力,就替那孩子解答了问题。周炜良出身清末官宦之家,曾祖曾是李鸿章幕僚后又担任过北洋大臣的周馥,父亲是著名的邮票大王周今觉,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十多年数学系主任,是著名的代数几何学家。
陈家第二代的姻缘,也曾借杨家之力,不过这次换成了杨振宁。陈省身有一子一女,女儿陈璞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毕业,是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系硕士。她的丈夫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温超导体专家朱经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物理学家。陈璞与朱经武恋爱时,陈省身通过杨振宁向朱的导师打听情况,得到的回答是,“Paul(朱经武的英文名)很聪明,但May(陈璞)更聪明”。杨振宁后来当了朱经武的博士论文导师,并在他毕业后为陈璞和他做了证婚人。
在学术上,陈省身最重要的成果“陈示性类”,与杨振宁研究的物理学中的规范场强度异曲同工。两人相交二十余年,才发现“所碰到的是同一头大象的不同部分”。为此,杨振宁送给陈省身一首诗:“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1936年,在汉堡大学度过两年“单身有钱一族”逍遥生活的陈省身前往巴黎,师从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何学大师嘉当(Elie Joseph Cartan)。
1937年,陈省身从巴黎动身回国。同我们印象中刻板的科学家不同,陈省身是一个爱玩爱吃爱聊天的人,在德国时,就曾经号称“吃遍汉堡所有餐厅,一家不漏”。这一次,因为奖学金充裕,他乘坐“伊丽莎白号”邮轮转道纽约,在美国游玩了一个多月,“观光访友,看大腿舞”,才辗转归国。
从1937年到1943年间,陈省身供职于西南联大。由于战争使昆明与外界隔绝,陈省身得以定下心来研读嘉当的论文,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43年,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数学家之一的陈省身受邀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那里的两年,他给出了“高斯-博内公式”的新的内蕴证明,进而发现了陈示性类。基于陈示性类基础上的一系列研究,为他在1984年赢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大奖“沃尔夫奖”。陈省身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
1946年,陈省身回国创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专心于研究与教学。直到1948年的一天,完全没有关注内战状况的他突然收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的一封电报,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便利你来美,请告知”,陈省身才意识到政局的变动。1948年12月31日,他携全家离沪赴美。这一去,便是四十余年。
在美国,陈省身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手创立了伯克里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R.奥斯曼在《几何学在美国的复兴:1938~1988》中写道,“就美国几何学复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言,是陈省身于20世纪40年代末从中国移居美国”。
拉格朗日曾说,“一种数学理论应该能向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人解释清楚”。陈省身一直把这当作“好的数学”的评价标准。然而,近代以来学科的细化和专业化已经使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陈省身的晚年,他其实也一直为这个矛盾所困扰。
落叶归根,住进南开宁园后的陈省身,其实并没能得到他期盼的宁静。作为一名早已功成名就举世仰慕的数学家,他期望把最后的时间都用在做自己的数学研究上。但是,他亦深知,他的号召力,是给如今已渐趋式微的中国数学界争取经费和政策支持的重要推动力。正因为他与江泽民会见时的进言,才使得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而南开的数学研究所,如果没有陈省身一力争取,几乎不可能建立。不愿出名,却必须抛头露面,这早已成了许多中国优秀科学家必须面对的共同困境。
几年前,记者曾与陈省身先生有一面之缘。对于媒体来说,陈先生是很好的采访对象,博古通今,天文地理,提起来滔滔不绝,妙语如珠。在他的文集中,除了高深难懂的数学论文,还包括一篇《论清太宗孝庄皇后》的历史短文。然而,只有一个同行就读于数学系的儿子间隙中和陈老谈起几何问题时,他的脸上才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与自在。到如今,斯人已逝,他的数学,他的传奇,他的梦想与期待,怕只如他最爱的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