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团“嗑药”(31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于萍)

音乐家在舞台上容易遭遇一些生理问题。孟斐斯大学长笛教授迈克琳坦言:“80年代我在国家长笛协会当乐手时,一登台就心乱如麻,手脚冰凉。我想掩饰紧张,可嘴唇抖个不停根本无法演奏,恨不得当台把笛子扔在地上。”1995年迈克琳找到了解决方法:她的私人医生为她开出了一种阻滞剂镇静药物“心得安”(Propranolol)。服药后她说,“我完全平静下来,演奏连贯极了”。可等把这种药物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时,她丢了工作。
怯场并不是音乐界的新问题。在借助镇静剂之前,音乐家们倚仗另一些方法。1942年,纽约的一个钢琴家组织了个“胆小者互助会”,一群音乐家互相嘲笑以便提高胆量。还有人求助于宗教仪式、酒精刺激,甚至自喷Valium安定剂。1976年,英国医药杂志《The Lancet》发现阻滞剂药物的镇静作用,自此被音乐人士广泛使用,到1987年,根据世界交响乐团协会统计,有近1/4的乐手经常服用镇静剂。《纽约时报》说,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阻滞剂的镇静作用已被科学证明,反对的声音便以“关心音乐家”的名义提出:长期服药,是否足够安全?1998年,一位医药学教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撰文说:“阻滞剂镇定药物应该接受身体检查后才能服用,因为患有哮喘病和心脏衰竭的人服后,会造成呼吸不畅与心率过慢,引发危险。正常人偶尔服用会有幻听、麻木和多梦等轻微副作用,如果长期服用或每天服用超过700毫克,则很不安全。”根据世界交响乐团协会的统计,乐手一般每次服药的剂量为5~20毫克。但问题是,获得阻滞剂这种处方药,他们大都不通过医生。据统计,有70%的服药乐手是从朋友、亲戚或郊区的不正规药店获得药物的。一位叫莫林的纽约交响乐团乐手曾给交响乐团协会写过这样一封信:“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坐在中提琴演奏席的最后一排。两年前我的父亲在表演前给了我一瓶‘心得安’,我吃下10毫克。现在我终于成为乐团的正式成员,这离我第一次坐在后排那天,已经22年。”这位曾经失落的中提琴手,似乎对镇静剂心怀感激。
其实音乐与药物的纠葛,最绞缠不清的是摇滚乐。60年代有“摇滚一毒品阴谋”论,之后又留下新的流派“迷幻摇滚”,其间有无数星光耀眼的名字与毒品瓜葛不清。但毒品,或者说药物,只是摇滚反抗社会的方式之一。对古典音乐来说,虽然不是为了表达愤怒,可镇定剂也不是只为镇定那么简单。有反对者认为服用镇定剂能够提高乐手的演奏技能。虽然没有硬性的判断标准,但看看服药者的体会:“心态平静”、“演奏更流畅”等等,似乎可以想象演奏水平也应该相应提高了。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米勒说:“阻滞剂镇静剂分许多种,睾丸激素类可以增强力量、提高速度;心得安一类的只能降低心脏过度兴奋,减轻焦虑,对提高演奏技能、弥补准备不足并无作用。”
但在同样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提高运动员成绩的情况下,阻滞剂药物在奥运会成为“违禁药”。被禁用的项目有:射击、花样滑冰、雪地摩托和雪橇。在一些竞赛性的现场表演中,交响乐团是否也应该禁止服用阻滞剂药物?洛杉矶交响乐团前负责人吉姆·华克说认为,服药已经是音乐界的“秘密游戏”,自己人怎么会提出禁用呢?而外人对交响乐的关注程度哪比得上奥运会,“如果耐克也让音乐家来做广告,解决这事才算有门”。
就镇定剂问题,记者采访了曾在中国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工作的张诗正女士,就演奏经验来说,她说乐队中的乐手不太容易紧张,独奏演员的台前焦虑现象多一些,至于解决方式,那是个人自己调节的事。而音乐评论家吴房则介绍说,服用镇定剂对中国的乐团成员来说没必要,原因有二,中国乐手没有国外乐手压力那么大,责任感也不强,不会乱吃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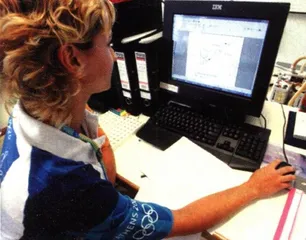
阻滞剂药物在奥运会是“违禁药”
阻滞剂(Beta blockers)
具有镇静作用,主要用于镇静剂药物中,作用为减少心脏的过度兴奋,降低焦虑、稳定情绪。目前有9种,如心得安、心得宁、心得平等。我们熟知的倍他乐克(酒石酸美托络尔)就是一种阻滞剂药物,其主要成分酒石盐酸提取自吗啡。
Valium
是安定镇定喷剂的主要成分,具有安眠和松弛肌肉的作用。在阻滞剂发现之前,音乐人士也使用这种喷雾缓解紧张。暴露在Valium烟雾中会令人困倦及思想错乱,分量过重会影响呼吸系统及导致内脏缺氧分量极重则会致命。2002年,俄罗斯车臣叛军劫持人质危机中,有许多人质死于“不明气体”,Valium是疑似气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