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尸与谋杀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赖希·拉尼茨基
李敖写的人物传记,我读过两种:《胡适评传》和《蒋介石评传》。
《胡适评传》其实才开了个头,该写的只写了1/10。不过这1/10部《胡适评传》还是很见功力。作者对材料的爬梳之细、比勘之精、判定之明称得上独步一时。当年老李假如未曾渡海赴台,以他的材料功夫,完全可以在大陆的各类专案组里出人头地。
《蒋介石评传》学术水准不高。李敖写蒋介石,一肚子邪火,差不多是抄家灭门挖祖坟的心情,杀气腾腾,对传主不厚道,不公道。
作者写抗战一节,题目是“蒋汪双簧之谜”。按照题意,作者应该拿出蒋介石汪精卫勾结配合通敌卖国的事实,可惜书中近万字的引文没有一项过硬的证据,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情节和深文周纳的推论。结尾的一段文字比较滑稽:“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明一暗的‘和平运动’,只因阴差阳错,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并无默契”,怎么能叫“双簧”?没有默契的双簧,就像没有菜肴的饭局没有文字的写作没有交媾的通奸一样不合情理。
但对大陆读者来说,《蒋介石评传》有些情报相当新鲜。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一案,以往的说法是受陈其美的指使,《蒋介石评传》却凿凿有据地证明,刺陶的主使人是孙中山和黄兴。大陆最新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8月第1版)《蒋介石评传》把原书中的证据部分全部删去,但结论留着:蒋介石“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其实孙中山、黄兴、陶成章都是洪门中人,同盟会、光复会就是两大堂口,堂口火并,也是帮会工作的一部分,那时候不太讲究现代政治的礼貌。
读《蒋介石评传》,你会觉得作者反反复复在说两句话:老蒋一生全是罪,蒋家三代无善类,整本书就是为这两句话收集例证。《蒋介石评传》水平不高在于它大量地引用三教九流的回忆录,而回忆录是最不可靠的史料。
李敖吃过蒋家的苦头,坐牢六年。他不是什么高人,当然要纠缠于冤冤相报。他只是文人,只能以笔墨为刑具,在书中对蒋介石施以私刑。
马丁·瓦尔泽在德国作家圈里地位崇高,听说几乎能与君特·格拉斯齐名,如果德国作家像水浒英雄那样排一排座次,瓦尔泽肯定能进前五,身份不会比梁山户口里天雄星豹子头林冲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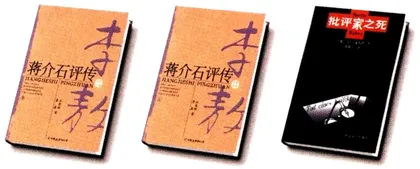
两年前,瓦尔泽以一本《批评家之死》在德国引发大风波,这本书的中文译本(黄燎宇译)姗姗来迟,今年9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批评家之死》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得罪很多人的文学批评家、著名的电视文学节目主持人忽然失踪,警察和大众都认为是一位作家把批评家干掉了,这位作家被批评家伤害得很深。围绕着案情,各种线索交集,小说作者的意见很明白,批评家罪有应得,活该千刀万剐。但到了小说的结尾,批评家和情人幽会后重新出现,生活就是那么荒唐……
小说中的批评家真有其人,他就是有德国“文学教皇”之称的赖希·拉尼茨基,赖希·拉尼茨基是犹太人,《批评家之死》惹出的笔墨官司,就是它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在德国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相当于在中国替“四人帮”翻案加反对改革开放加看足球支持日本队,是了不得的罪名。不过没有几位中国读者熟悉反犹主义的典故,所以读《批评家之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难有德国人的体会和乐趣。比如小说中写批评家和怀孕的女人苟且,这里就需要一点西方的文史知识:犹太人喜欢搞怀孕的非闪族妇女是反犹主义散布多年的流言。
撇开欧洲犹太人的历史恩怨,《批评家之死》还是有它的跨国话题:作家对批评家的敌意。西方语文里已经有不少对批评家的挖苦,说批评家是文学血管里的水蛭,后宫里的太监,号称认路但不会开车的司机,没有腿的长跑教练,《批评家之死》表达的不仅仅是挖苦,而是仇恨,不仅仅是一般的仇恨,而是深仇大恨:“你(作家)很高兴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的1/4决赛中被保加利亚淘汰,因为你有一个热切盼望德国获胜的对手(批评家),德国失败使他遭受比你更为沉重的打击,所以你为德国的失败感到高兴。”
对与文学无关的老百姓来说,只有杀父之仇辱母之耻夺妻之恨才能激发这么恶毒的想法。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