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座樱桃园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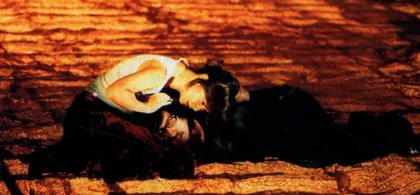
《樱桃园》剧照
听那些在俄罗斯学过戏剧的人说,在那里,当他们的作业做得不够好时,老师会“威胁”他们说,你们再不好好做功课,下一个戏,我就让你们做契诃夫的作品。于是他们就更努力,因为契诃夫非常难把握。在很多人眼里,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水,你用什么样的器皿去盛它,它就是什么形状。契诃夫的戏剧是有自身重量和形状,只有合适的器皿,才能体现他的精髓。另一方面,单就契诃夫的剧本而言,又确实具备着多种可能性:无论是最传统的戏剧现实主义,还是最开放的戏剧现代主义,都可能在他的戏里找到支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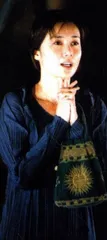
俄罗斯国立艺术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的《樱桃园》和林兆华在北剧场上映的《樱桃园》无意中形成了一种打擂台的氛围,将契诃夫戏剧演出季推向高潮。
我们看到了两座完全不同的樱桃园。作为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之一,有着83年辉煌历史的俄罗斯国立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和戏剧大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洛维奇·鲍罗金在舞台上几乎重现了那座优雅美好的贵族庄园:长长的宽幅白纱、精致的古典家具、变化细微而层次丰富的灯光。那种端庄凝重会让你想起《日瓦格医生》、《战争与和平》。而导演舒缓的舞台节奏、演员们宛如身在其中、不夸张、不做作的舞台风范真是对斯坦尼体系的最精准阐释。即使结尾,贵族们被迫搬离樱桃园,演员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夸张的肢体幅度,他们就那样抱在一起,轻轻地和樱桃园告别。那种忧伤和美好事物一去不返的惆怅暗暗在剧院中弥散。
面对俄罗斯版的《樱桃园》,林兆华不是没有压力,他说:“排契诃夫是有阴云的,到底他们的传统比我们要正宗,但对它的再认识和重新解读阐释的障碍也更多。”林兆华《樱桃园》的重新阐释几乎像一个令人吃惊的恶作剧——舞美易立明设计的舞台仿佛是一个农村大棚,华丽的房间变为被塑料帘子遮起的窝棚,美丽的樱桃园不过是一片生长着几棵光秃秃树木的荒芜的土地,探照灯式灯光扫来扫去,天际线被刻意压低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的高度,压抑而诡异。在这样的樱桃园中,贵族们充满情感描述的湖泊、春天、阳光,听上去完全是幻想的妄语;而庄园的主人,女贵族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的快乐、愤怒、忧伤、对巴黎的怀念都成了歇斯底里。林兆华把剧中每一个人都中国漫画化了:说着一口东北话,喜欢蹲在地上的商人陆伯兴;一口京片子的老管家;一口生硬汉语的随从亚莎。当陆伯兴用东北话叫大学生毕嘉“大兄弟”,演亚莎的法国演员一会儿京腔,一会儿法语的时候,那种后现代的拼贴感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你想起“实验”、“颠覆”一类的词语。但林兆华认为,他正是在还原契诃夫本意中的《樱桃园》。100多年前,斯坦尼拉夫斯基执导的《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映,在观众们和剧中人物一起为《樱桃园》的消逝依依惜别的时候,契诃夫说:我这部戏是笑不是泪。契诃夫的好友丹钦科也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用细腻的柔情掩盖了契诃夫对贵族、对农民、对新兴商人的善意的嘲讽。
毫无疑问,林兆华希望能恢复这种嘲讽,恢复契诃夫对这些在俗世中挣扎的人们俯视的悲悯,而不是身在其中的感伤和柔情。他对演员们说:如果你们在表演时候每天都能感受到契诃夫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就是成功的。他的演员们不悲伤不哀婉,他们时而像喃喃自语,时而像相互干扰,而且他们大多独自面对观众或是在台上游走,他们像野兽一样奔跑、扭动、挣扎。从齐着舞台天际线的观众席上看过去,看那些100年前社会转型期中的人的失落、得意、不甘、无奈,真是说不出的凄凉。
然而,在结尾,林兆华终于还是没能忍住,他让那些失去了家园的贵族们坐在黑暗里,坐在委婉的音乐里;他让一身黑衣的老管家用标准的嗓音在幕后念出过往生活的印记,“少爷没穿皮大衣,穿着夹大衣出门了”。那一瞬间,林兆华终于禁不住表达了他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温柔和怀念。樱桃园是园林,但更是爱,是回忆,是传统,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东西。林兆华想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告诉大家这最柔软的东西不过是一场乌托邦,是一场在荒芜土地上的乌托邦,却发现自己比谁都渴望这这个乌托邦。他想构建一个寓言,却发现依然是一首惆怅的抒情诗;他虽然忍住了眼泪,却没能忍住心里的悲哀和苍凉。在采访中,他自己也承认:“对于旧的留念或者是对过去的美好的怀念是永远留着的,尤其是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一切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一幕:“樱桃园,这是一个美妙的名字。”契诃夫对他的合作伙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禁不住压低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