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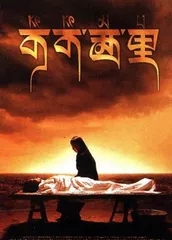
《可可西里》海报
陆川在《可可西里》对死亡的处理方式,令人想起法国电影大师布列松的《少女穆谢特》:穆谢特套上雪白的裙子,躺在湖边,先滚了一下,位置不对,她起身换了一个地方,然后向下滚去,“咚”一声掉进湖水里。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影片中人物一旦被人认同,如此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不能被人接受,所以巡山队长日泰、队员刘栋的死不断被人提起。想起日泰毫无征兆就被盗猎分子一枪打死,忽然觉得耳边“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惟一的生命”的歌声真是很扯淡。
不干扰镜头前的事实,不过分纠缠人物内心,让《可可西里》极端简洁干净。所以很多人说它干净,一定不单纯指镜头前的天地自然。但这种不事装饰,与布列松《布劳涅森林中的夫人》的不事装饰完全不同,该片出来后,一时受到冷落,在安德列·巴赞看来,那是因为“理性色彩过浓”,布列松是法医面对尸体的心态,只给出尸检报告,不品评此尸生前为人。观者如有悲悯,全在看了报告之后想象死者生前如何得到这些伤痛。而陆川的激情则满满贮在冷静影像背后,两者结合起来,让《可可西里》观看现场即充满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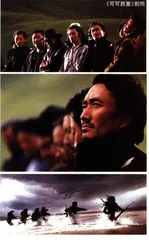
《可可西里》剧照
矫情,《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故意违反常情,表示高超或与众不同。”看过《可可西里》的人都认为它不矫情,大约就是陆川没有在影片里安排一点违反常情的东西,在个人最直接的体验和影像传达之间没有加入任何多余成分。
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篇《可可西里》的负面评论。惟一一个称不上好消息的新闻来自票房:《北京青年报》总结“十一”期间票房时,提到《可可西里》在新影联票房还不足10万元。“十一”期间好片云集,为何《可可西里》票房不佳?以国内影片下档后就难觅踪影的惯例,靠累积增加票房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
受到好评,几乎是《可可西里》一旦成片后必然会得到的待遇。对于目前中国电影来说,简单而有血性的电影太少,《可可西里》令人耳目一新。陆川本人虽书生面目,但极有血性。为了保证自己的原意不被修改,他每场戏只拍一个机位的镜头,要么制片方全盘接受一部完全“陆川的电影”,要么花更大的代价重拍。这部电影影像干脆利落,每个人物都站得住,仅此一点,就值得去电影院看一看。
还说巴赞,他评论布列松《乡村牧师日记》时提到了一些人的评论,这些人也会用“美不胜收”来形容这部杰作,但仍然言不及义,没有道出最根本之所在。单就《可可西里》论《可可西里》,或者加上对拍摄过程中的艰辛描述,很容易既降低了这部电影的地位,同时拔高了其艺术成就。《可可西里》中有句台词,巡山队员对记者说你现在走出的每个脚印都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一个脚印(大意)。陆川《可可西里》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电影开拓了新领域。这一点他自己可能也很清醒,说自己这部电影不是典型意义的中国电影,不能入选威尼斯很正常(大意)。
陆川开拓的,并不是把可可西里变成另一个涿州影视基地,而是走了一条目前还不知道通往哪里的路。《可可西里》比一些肉不唧唧的所谓艺术电影多了决断少了陈腐,但并未实现商业上的成功。目前能确定的,就是陆川仍然在往前走。仅此一项,就值得观众喝彩鼓掌。
其实,《可可西里》并不复杂,主题也未见得深远,并不很经得起反复地、一层层地读解。但这并不妨碍《可可西里》变成文化事件。《新京报》报道10月27日该片一次“内部”放映后,陆川上台致谢,“当场泣不成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对陆川说:“中国还能被寄予希望的导演不多了,陆川,坚持下去!”这篇报道,加上非常类似“用生命代价拍摄电影”的报道,让人将巡山队员的想象与陆川叠映在一起,两者的交集点就是悲壮和坚持下去。在看到票房记录后,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可可西里》获得好评,是因为几乎人人都看到中国电影的局限与范围,而任何突破都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