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于萍)

意大利Giorgio Barberio导演的莎士比亚经典剧目《暴风雨》
戏剧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曾经这样形容探询莎士比亚身世之谜的人:“你像是看压在玻璃下面的一张画面非常黯淡的照片。起初你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你开始能辨认出面容,然后你会认出它们原来就是你自己。”这种对莎士比亚自我认同式的研究方式,其实很值得同情。有关这位作家身世的资料的确就这么简单:他156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小镇斯特拉特福德,父亲是个倒霉的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他13岁前曾在当地公立学校学习,之后辍学;18岁结婚,21岁有了3个孩子。约1586年他突然抛家弃子跑到伦敦,并神秘地逐渐成为剧院的演员、剧作家、股东;此后成为蜚声英国的著名剧作家和诗人。1616年他病死在自己的家乡斯特拉特福德。这种庸常的经历让后人发掘的潜力很小,想象空间却很大。新论著不断涌现,却只能翻版前人资料,添加主观猜测;曾有新潮理论断言“莎士比亚是另一个人”。但在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眼里,那些冲动的学者都搞错了方向:“他还留下37部剧作,154首十四行诗和2首长诗。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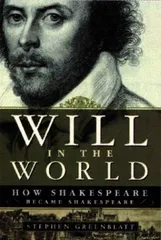
斯蒂芬的新作《意志永存于世》正是通过分析莎士比亚的传世作品来探究这位作家的身世。对莎士比亚迁居伦敦前的经历,虽然有史料可查,但按照斯蒂芬的观点,依然可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印证,那就是《仲夏夜之梦》。“这是莎士比亚最具自传性质的剧作,他的想象源泉正是童年经历的三个片段:儿时对异教民间传说和礼仪的记忆;来自父亲的乡下商人经历,包括木匠、裁缝、手套商;年轻人在树丛中偷欢,下场却是悲惨的婚姻。”
根据斯蒂芬的分析,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对异教及异教徒的描述正反映了他有亲身的“异教体会”。莎士比亚年轻的时候,激进的新教是主流教派,而保守的天主教徒则是反政府的异教徒。但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大半辈子都在推崇保守天主教的亨利八世统治下度过,母亲又来自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有不只一人因不奉新教而被处死。斯蒂芬因此推断莎士比亚的童年正是在这样一个异教家庭中度过。但旧宗教的浸润、新教的冲击在莎士比亚的青春意识里潜伏下来。
斯蒂芬着重分析了莎士比亚的父亲,那个乡下商人。他本来是镇上的首脑,市政厅的议员,但突然家道中落,生意勉强维系着,政务早就撒手不管。就在这时,13岁的莎士比亚辍学,成为父亲的帮手,经营非法的木材生意。这时候“父亲”在莎士比亚眼里意味着:酗酒、异教徒、非法商人;生活也处处透出拮据、劳累和悲凉。斯蒂芬断言,正是此时,莎士比亚决心摆脱困境,穷其一生为自己和家族寻找出路。
1582年18岁的莎士比亚突然举行了一个“如枪击一般”迅捷的婚礼,妻子安妮·哈泽薇比他大8岁。“这场婚姻给莎士比亚带来了婚礼后6个月就出生的大女儿,一个儿子和小女儿,以及一生的噩梦。”这似乎可以与《仲夏夜之梦》中偷欢和悲惨婚姻的情节契合。而在斯蒂芬看来,日后莎士比亚抛妻弃子只身前往伦敦,也说明他对这场婚姻并不满意。

电影《哈姆雷特》剧照
莎士比亚单薄的教育背景曾使众多学者质疑他是否真的是那些伟大作品的创作者。斯蒂芬却认为莎士比亚13岁前在斯特拉特福德公立学校所受的教育足够为他开启文学殿堂的大门:他学会了拉丁文、接触到古典文学。而童年两种宗教的交错影响、家庭与婚姻的悲惨情状,使莎士比亚在长时间磨练中形成一种爆发力,它来自血液深处,不需要教育的训练和锤打,却是超越这之上的卓越性格。
进入伦敦戏剧界的莎士比亚自然不会放弃来自儿时的敏锐观察力和改变命运的决心。一部名为《马耳他的犹太人》的戏剧和一场处死“叛国贼”罗杰伊格·洛佩茨(Roderigo Lopez)的绞刑促使他实现了一个飞跃——在1594~1598年间创作出不朽名作《威尼斯商人》。正是这部剧作让诸多学者怀疑莎士比亚的真正身份:这样一个从没离开过英格兰的孤陋寡闻之人,如何能刻画出既卑鄙又可怜的犹太人夏洛特形象?斯蒂芬说:“他善于观察。”由同时代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创作的《马耳他的犹太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表面臣服于基督教,内心却阴险的犹太人形象。而犹太人罗杰伊格·洛佩茨因被怀疑通敌西班牙而被施以绞刑。临刑前这个犹太人大喊着:“我效忠女王,如同效忠耶稣……”场下一片讥笑。斯蒂芬猜测,莎士比亚也许正是观刑讥笑中的一个。剧作与事件成为《威尼斯商人》的来源,又在《威尼斯商人》中得以展现。“你们要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段《威尼斯商人》中的对白让人们感慨莎士比亚是如何敏锐捕捉到犹太人在自己的信仰与基督教夹缝中挣扎的心态。斯蒂芬提醒说:“别忘了,他儿时经历的宗教冲突。”
莎士比亚中后期的作品一边延续着家族烙印,一边又反映了当时伦敦戏剧界的面貌。1596年,他惟一的儿子11岁的哈姆耐特(Hamnet)夭折,随后他的父亲也去世。这让在心理上一直没有脱离家族影响的莎士比亚陷入无尽黑暗。随后几年,他带着悲怆创作出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斯蒂芬注意到,这四大悲剧中的主角都卤莽、偏激,缺乏谨小慎微的判断力,这些正是导致悲惨命运的来源。斯蒂芬断言,这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审慎、精明的处世哲学的肯定。而这一方面总结自父亲的命运——莽撞地信奉异教而丧失权势;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伦敦戏剧界的风云。
同时代的两名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和克里斯托弗·马罗,前者因信奉天主教被投进监狱;后者为新教充当间谍而最终被刺杀。种种动荡,让莎士比亚这个小地方来的人行事谨慎,他服从秩序、信奉权威,躲避一切暴乱、刺杀、革命的变化。正是这种处世方式让他在反复无常的伊丽莎白时代明哲保身。与此同时,他在老家斯特拉特福德镇购买地产,准备归隐。
在斯蒂芬看来,莎士比亚的后期作品,如《冬天的故事》,都如同幽幽的神话小故事,莎氏典型的癲狂与激烈冲突不复存在,这又反映出家族变化和他当时的心境。丧子后的莎士比亚将希望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大女儿苏珊娜投身医科;小女儿朱迪斯纠缠于糟糕的婚姻。已经功成名就的莎士比亚感觉到只有自己才是整个家族的亮点,同时上流社会的变幻莫测也让他厌倦。他喜爱的作家蒙田曾说:“归隐是绅士之举。”对莎士比亚这样一个心怀改变家族命运的背井离乡者来说,该是荣归故里的时候了。与其说他厌倦了伦敦,不如说他在伦敦得到了一切。1610年,莎士比亚回到家乡斯特拉特福德镇,1616年病死在那里。墓碑矗立在小镇的教堂旁,上面的墓志铭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不要动我的坟墓,妄动者将遭到诅咒,保护者将受到祝福。”这是莎士比亚留给世人最后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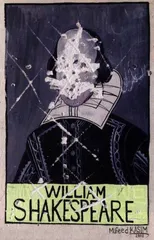
咨讯
莎士比亚身世的几种传说
1.他是剧作家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不屑于让自己的名字扯进演戏这种低级职业,就花钱租用了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乡下人的名字。支持这种说法的有马克·吐温和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
2.他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
英国“德维尔学会”认为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才是莎士比亚37部戏剧作品的真正作者。“他是最适合这种工作的人,”该学会秘书理查德·马利姆说,“他受过相应的教育,并有相关旅行经历,而莎士比亚没有。”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刚到伦敦时,恰好被贵族德维尔抓住,于是充当了德维尔具有讽刺意味的写作和表演的“掩护”。但有人反驳说,德维尔这样一个当时的大忙人,不可能在各种活动间隙写出如此多的杰作。
3.他是剧作家兼政府间谍克里斯托弗·马罗
马罗是当时政府大间谍华兴安(Francis Walsing Ham)的手下,因触犯国教被捕。后华兴安将马罗保释,为保他不死,又安排假刺杀计划,假传马罗已死。实际上马罗被藏匿在华兴安的保垒里专心写作。“莎士比亚”正是马罗的笔名。持这一观点的有霍夫曼、海勃朗纳、梁实秋、余光中。
4.他就是莎士比亚
更多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就是他自己。因为那个密探、窥视和刨根问底普遍存在的时代,民众的好奇心使得任何秘密都无法隐瞒。假如莎士比亚戏剧不是莎士比亚所作的话,一定会有确凿的记载或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