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遗产日:文化的弥撒
作者:曾焱(文 / 曾焱)

平时只有外宾和政界名流出入的爱丽舍宫,遗产日也向普通人开放,不过,破晓时分就要起床排队
夏日度假结束,法国人的罢工季节就快来到了。不过在这之间,还有一段温和的“文化蜜月”可供享受,其中最能抚慰法国人的节目,一是从9月开始的所谓文学季,各大出版社新书出笼上市,紧接着盛大的文学奖项揭晓,从名震天下的龚古尔奖、女评判奖、法兰西学院奖到各种自娱自乐的小奖项,轮流热闹一番,捧出若干文学新贵;另外一个万民同乐的节目,则是一年一度的法国文化遗产日:每年9月第三个周末,全法国上万个文化古迹和历史建筑同时向公众免费开放,除了隶属国家的著名教堂、博物馆和宫殿之外,许多平时老百姓不能涉足的权力中心像总统府、政府各部办公地址、巴黎市政厅、法兰西银行总部,也会开门纳客,这些地方都是一两个世纪前的老建筑,里面金碧辉煌,名画深藏闺中,平常人难得一见。两天时间,1000万以上的参观流量,这种盛况怎么来描述呢?法国《世界报》几年前有一篇报道,将其形容为“伟大的弥撒”。
保护和时间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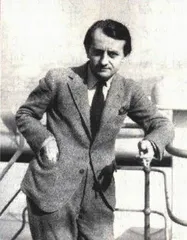
安德烈·马尔罗,这位戴高乐时期的文化部长对遗产日的设立功不可没

20世纪的文化遗产:建于1900年的巴黎地铁入口
每到遗产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就能看到很多手持地图疾走赶路的游人,都希望能够争取时间多看几个地方。有些场所可以预定参观,但大部分只能排队等候。每年最可观的长队都出现在爱丽舍宫外,绵延两三条街,参观者往往凌晨就起床,耐心排上六七个小时队,然后进宫参观20分钟,运气好的时候能和总统及夫人对话。若是参观位于皇宫花园一侧的文化部,在部长办公室担任讲解的很有可能就是部长本人。
遗产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为此会特别开放一些参观场地。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和技术”,宣传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要地位。很多收在博物馆里的科学仪器会展示出来,而一些工业建筑、天文学建筑和航天航海建筑将推荐给参观者。现在已经公布的参观地址中,有两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酩悦轩尼诗(MoetHennessy)酒窖,这个名酒品牌将开放它在兰斯、厄佩尔尼和白兰地的公司,部分制作场地属于首次开放,喜爱名酒的人肯定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另外,法国博物馆研究和修复中心也是首次开放的神秘之地。修复中心位于卢浮宫地下的卡鲁塞尔厅,由暗梯通达地下十几米深处,面积5000平方米,是全世界有名的秘密实验室,每每在法国购买重要艺术品时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据说这里面的科学家掌握有独门秘技,可以解开很多艺术品身上的历史之谜。曾经有媒体披露,实验室里面有两台世界最尖端的检测和修复仪器:一台是“阿格莱”元素分析加速器,长26米,重10吨,依靠发出的质子蓝光,不需抽取样本就能检测出收藏品的化学成分,最著名的案例是分析公元前2600到2350年间的埃及木乃伊。另一台仪器衍射计能够分析原子组合的方式,1999年科学家发现“古埃及化妆品”就是它的功劳。
主题对每年的遗产日有着画龙点睛的功效,主题选择若是独具匠心,那一届遗产日的影响力也就是世界性的。很多人还记得2000年遗产日的中心议题——“20世纪的现代文化遗产”,帮助居民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认识自己生活的城市。法国有40万个被列为古迹保护的建筑物,属于20世纪的只有1100个。怎么才能保护自己亲历的这个世纪?这是每个国家的人都面临却没有正视过的问题。法国文化遗产管理处披露过一个数据,工业时代之前的被保护建筑60%是宗教场所,而到了20世纪住宅变成大头,以宗教建筑物形式出现的文化遗产降低到4%~5%的比例。否定同时代人显然比否定先人容易,否定日常建筑显然也比否定宗教建筑简单,2000年遗产日因此而让人们关注到创造和覆盖的现实难题。20世纪的建筑在材料和技术风格上实验的痕迹较重,建得多,毁得也多,常常在一二十年之后就被抛弃,导致现代建筑不容易存留。法国人曾借2000年遗产日反省了几个重大失误:法国19世纪的建筑家巴勒塔,他在19世纪中后期建造了巴黎市中心的Les Halles,也就是中央菜市场,几十年后被拆毁重建,但大厅绿色铸铁顶棚的优美造型令人难忘,很多专家感叹这个杰作在“冷漠中消失了”,由此而生的悔意数年后终于挽救了奥塞车站,后者没有被粗暴覆盖,而是在小心改造后变成了今天著名的奥塞博物馆。巴勒塔的建筑如今在巴黎市内几乎荡然无存了,要重温大师的作品,得坐上快速地铁,到离巴黎10分钟车程的小城Nogent sur Marne,那里有几处复制品。另一个受害人是20世纪初期欧洲“新艺术”建筑运动在法国的领军人物赫克托·吉马尔,他的作品被损毁了1/3多,只有巴黎几个建于1900年的老地铁入口,告诉后人它们的建筑师吉马尔有多么了不起。
马尔罗和民间干预

名酒、酒窑也是法国今年力推的参观项目
从年份上看,遗产日从1984年开始设立,由法国文化部发起。但是很多法国人愿意把它归功于戴高乐时期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关于马尔罗,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知识分子和政界要人,法国知识界评价不一,不过他10年在位期间对于法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毫无争议的。马尔罗的第一身份是作家,早期小说大多以东方为主题,其中1933年《人类的命运》讲述蒋介石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获得龚古尔文学奖,50年代后转向艺术史研究,先后完成《沉默的声音》、《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和《诸神的变异》等艺术哲学论著。他在这几本书里将各国各个历史时期艺术珍品的图片搜集起来,看图“说话”,用艺术来观照历史,思考人类命运,引起的学术争论横跨哲学、史学和美学三界。后来他将几本书的精华部分集结成一本《无墙的博物馆》,书名已经充分体现了马尔罗不向普通民众设防的大文物观念。1958年就职文化部长之后,马尔罗做了三件载入法国文化史的大事:第一是建立了法国文化艺术珍品总目。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的文物古迹遭到很大破坏,马尔罗发动全国对历史珍品登记造册,大到教堂古堡,名画古董,小到居民家里祖传下来的银勺银盘都做了仔细盘点,这个举动使得普通法国人都对保护文化遗产有了认同感。由他实行并存留至今的第二个惯例,是定期对巴黎建筑的外表进行全面修饰,包括年代久远的居民住宅也一样受到重视,巴黎因此而成为欧洲历史建筑保护得最为完善、城市面貌却最整洁的地方。1962年颁布的《马尔罗法》是他留给法国人的另一份大礼。该法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纳入城市规划的管理体系,任何人不能任意拆除保护区内的建筑,维修和改建也要经过“国家建筑师”核定并指导进行,国家对符合要求的修整计划给予资助。《马尔罗法》不但使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也由于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追随,促使国际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从保护宫殿、教堂这样的建筑艺术珍品,发展到保护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建筑,那些有生命的仍在使用的街区。法国目前的国家级保护区将近100处,其中著名的里昂老城区就是1964年由马尔罗亲自主持认定的,那里保存了大量16到19世纪的古老街巷,除了250栋文物建筑,连20世纪初期的工人住宅也被依照原貌保存,同时为了让居民能够永久居住以延续保护区的生命力,政府还在住宅内部加建厨房、卫生间、电梯,古老外表现代设施,这样的保护模式在法国各个城市都推广得很好。
马尔罗凭一己之力,为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创了民间认同和干预的传统,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除了官方的文化遗产管理处,法国目前有6000多家以保护遗产为使命的协会,而为了资助一些缺少资金的小型协会,法国政府新近又专门成立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充当官方和民间保护之间的桥梁。基金会的初始资金来自企业赞助和私人捐赠两条途径,有权收购濒危的建筑物,特别是在古老建筑的拍卖上享有优先购买权,这样一来,很多所属不明朗的地方古迹比如一些古堡什么的,就不至于被境外富豪大量收购而导致文物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