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公车货币化”是权宜之策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马丽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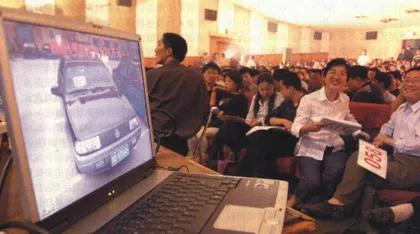
2004年5月,江苏无锡市惠山区第一次公务车拍卖推出了60辆公车,前往竞拍的市民达数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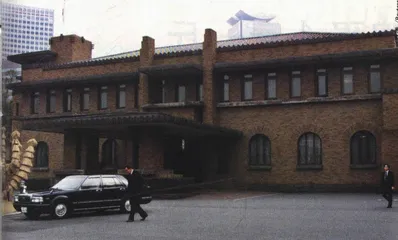
在日本,对公务车有着严格的车辆配置
公车货币化,就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公车在中介机构评估定价后都拍卖掉,以车补形式,按行政级别发放给公务员津贴。
以山东威海为例,车改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级别每月领取200元至2400元不等的交通补贴。其中,正处级领导2400元/月,正处级非领导职务的1800元/月;副处级领导1600元/月,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1200元/月;正科级600元/月,副科级400元/月;科员、办事员及工勤人员200元/月。
在广州,其车补标准最高的为正处级,每人每月补贴2800元;最低的是副科级以下人员,每人每月补贴400元。
改革者期望通过向公务人员发放定额的用车补贴,作为其用车消费的惟一来源,以专用“车贴”的数额限制公务人员的用车行为,进而限制行政管理费用的畸形增长。
货币化的“赢与亏”
在公车消费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三个1/3”:原来在公车使用中“公务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公车改革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当然是算经济效益账。
从目前开展的几个试点来看,最明显的便是车改前后,公车支出的急剧减少。减少的比例从20%到40%不等。威海估计,全市的公车费用支出比车改前将节约41%。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谢谷梁介绍广东省的公车改革时说:“车改”前后对比,交通费用一般可节约30%左右。但是这笔经济账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谷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不过在有关南京的一则报道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二:92个涉农街道2003年实际支出的车辆费用总额约为6225万元。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后全年费用合计约4242万元,降低支出32%,可以节约1983万元。
由此可见,在大同小异的节约后,账是这么算的,将以前的购车费、修车费、汽油费、路桥费、司机工资等总费用,减去车改后的车贴总数之“差”,就是“节约数”了。节约数比上原来的基数就是降低开支的比例。
这样的节约数字是以浪费严重的公车耗费现状作为“基数”得来的。时下诸多地方公车费用支出至少有2/3是不该发生的,应按纯粹的损失浪费额剔除出去。而惟此把浪费额剔除后的公车费用支出,才有资格作为“基数”与车改后的公车费用支出进行对比。换言之,假若把时下公车耗费的水分全部挤干后再进行对比,那么节约的41%、30%、32%就远不是实际上应该能节约的比例了。本应该可以节约的那部分财政资金,实际上已通过公车改革方案变成了“补贴”落入了个人的腰包。
但是,毕竟这个吞噬巨大资金的“黑洞”在一点点缩小。
但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著名行政管理专家毛寿龙也提到关键的一点:“在货币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由尼斯·卡宁定律中描述的官僚机构膨胀问题。也就是说,公车补贴的数目比实际需要的数目要大的多。比如原来从来不用车的人,都会在这次公车改革中搭上便车,实际补贴下来比原来公车的消费开支还要多,这会导致一些地方在货币化的过程中,更多地侵蚀公共财政。”
“公”“私”依旧不分
与中国相比,发达经济国家里“公车费用”的支出非常小。记者查询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不过据毛寿龙向记者估计:“公车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不会超过10%,远远低于中国的38%。”
比邻的日本算是严格控制车辆配置的国家。日本政府各部门内部用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用车,另一类是公用车。专用车供正局级以上领导执行公务时使用,不能用于办私事,上下班一般只接送到车站,然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公用车是副局级以下的公务员因公外出时申请使用的车辆,其数量编制根据需要用车的领导人数和公务活动的频繁度核定。用车时事先到总务课填写用车申请表,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后到车队乘车。在公用车中,包车和租车占较大比例。
在德国,只有国务秘书以上(副部长)才能拥有自己的司机和公车,这个数字不会超过1000人。德国各主管单位对因私用车都有明确的收费规定。如柏林市,所有因私用车都得收费,包括汽油费、停车费、磨损费(按里程计)。联邦和各州主管部门为节省支出,都尽量减少公车数量。例如,柏林市仅有公车92辆,其中个人专车37辆,一般办公用专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这些公车中还有相当数量是租赁来的。
通常,只有在严密、长期、严格的制度约束下,社会才能培育出一种健康的行政文化,才能形成一种严格区分公私的行政伦理。这样,即使在公私难分的领域,公务员也能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芬兰,政府开始施行公车制度时,是在公车上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的,监测公车的用途,一旦发现公车私用,便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后来公务员们普遍接受了这种做法,定位系统才被拆除。
谁都不怀疑,我们应该积极向区分公私的理想状态努力,并对公权私用要有严格的制度打击。在这种完善的约束制度缺失和漫长的道德教育完成之前,我们不必幻化中国官员的道德准则,也无法依赖屡屡失灵的道德攻势,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这样说来,公车消费货币化无疑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折中办法。上海市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胡伟认为,这种折中方案因为无法奠定一个基本制度,而显得权宜。围绕着外围转的办法,是不是能在不产生新问题的情况下,减轻现有的矛盾,还很难判断。
毫无疑问,“公车货币化”可以迅速控制畸高的行政管理成本,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却侵蚀了公共财政使用目的的“公共性”,模糊了公务人员用车行为的“公私”界限。也就是说,政府公务人员完全可以用公共财政支付公务人员的私人消费行为,或者为了节省个人开支,该办的事情不办。
“这导致了投入的钱有没有效率。从理论上说,如果公务消费产生的效应是边际递增的,不管花多少钱,都应该予以支持和报销,多用车本身并不是坏事。相反如果是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车用得再少,也是挤占、浪费国家公务资源。”胡伟说。
但是,当我们实行“公务消费货币化”之后,两者的界限有时变得非常模糊,难以分清。目前,政府官员的用车行为存在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政府向公务人员支付数额庞大的用车补贴且又无法说明其用于公务还是私人消费,那么很容易让公众产生“公共财政私人化”的印象,极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与置疑;这使得“货币化”的改革措施在公共财政使用的政治合法性方面打了不小的折扣。
“权宜之策”
从来不想否定货币化的好处,尽管我们一再说它是个“权宜之策”。但在没有更好的新的办法和制度出来之前,“公务消费货币化”便成了车改的主流方法。
“货币化最好的一点是,政府能够施加更多的控制。”国内金融专家易宪容在接受记者的另外一个采访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在社科院和香港大学任教的易教授极力主张国有资产货币化改革。
犹如双刃剑,公车消费的货币化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
其一,中国官员在公车使用上获得的不仅仅由社会地位和权势带来的成就感,还最大程度地挖掘了“身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毛寿龙认为:“在诸如‘诚信’等道德力量相对缺失的环境里,将‘公车消费’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折算成现金,会产生贬值,导致官员的不满意。”因此便难以杜绝,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最大化的满足自己的利益:包括拍卖的价格,竞标者,以及最直接的车补数量和形式。
其二,工资改革没有全面开展,差距没有拉开的情况下。官员的工资收入上一下增加了很多收入。一个副处级的每月1600元的补贴也远远高于不少人的工资,并足够养一辆像样的车。这势必会在公众心里产生“落差感觉”,积聚社会压力。
最后,为广大官员纷扰的恐怕还包括,重新安排为自己效劳了多年的司机。如果全国的公车数量算下来,那又是怎样的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