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0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石头 朱门酒 困困 贝小戎)
烛影摇红
石头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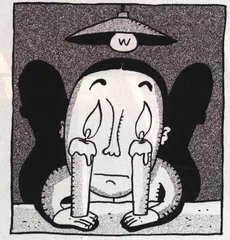
独自在家,停电了。天上还亮,屋里先黑下来。摸出个半导体,一个票友正在很难听地唱着《让徐州》。
出门买十支蜡烛,门厅一支,卫生间一支,桌上六支,备用二支。
烛光温暖而宁静,桌上的亮度居然不逊于白炽灯炮。一米之外便朦胧,绒绒的光影晕染在粉墙上,温柔蕴藉——虽然那只是粗蠢冰箱的投影。意想不到烛火这种至静的美,颀长纤细的红烛像微抬下巴的少女,亭亭的,矜持地保持着姿态。
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在这样出奇宁静的烛光下,每一举手投足,每一柔肠初转,都有了典出。
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想起陶渊明情致宛转的句子。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太阳升起,蜡烛就黯然失色。从前有个小妇人戚戚地说,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眼前的红烛却没有那么苦情,常常爆出噼啪的响声,灯花爆,喜事到,好彩头呢。烛火总要人去侍弄,一时不剪,火焰就弯曲晃动起来。采采苡,薄言采之。剪剪红烛,薄言剪之。剪烛要细致,烛芯一不小心就会滚落在桌上。剪下的烛芯带着点火苗停在剪刀上,一星如豆,迅速熄了。立刻就有一弯篆烟透明地散开。浮生恰似烟中火,一缕轻香入太虚。
这样的烛火,宜读书,宜作画,宜饮酒,宜调情。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可惜斯人不在。想打个电话,又一味坐着,不愿打破这宁静。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过了两三个钟头,红烛居然已经燃掉一半。从前的青青少女变作半老佳人,泪流够了,身形也谦和许多。好像有无限怀抱氤氲。有的烛短而辛苦,堆下许多烛油,一枝寒泪作珊瑚。有的呢,高高的,几乎没什么滴泪,皮肤还是那么光鲜,身材苗条,保养得很好。看来平等二字对蜡烛来说也是奢侈。
夜半,那些高高低低的红烛都凝成一小堆红泪,熄掉了。看来想要替人流泪到天明,须得一支超大蜡烛。睡了。烛火盈梦。忽然惊醒,庸俗的电流冲进钨丝,台灯明亮刺眼,红烛一夜恍如迷梦。
烛夜比较费钱。十支普通红烛五块钱,只够点半个晚上。一度电四毛四,一般来说一夜走不了十度。而且这样的夜晚,没有电灯,没有绣窗,没有电脑,没有珠帘,没有音响,没有玉炉,没有空调,没有花影,没有电冰箱,没有云母屏,没有电饭锅,没有红袖女。没有古典也没有现代化,只有烛影摇红,今古如一。
静若处男
朱门酒
古人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现在可不能这么说了,现在的小丫头都很早熟,很in,很cool,很hi,很你懂的单词你不懂的用法……这些新时代的处子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已经不复她们的前辈当年,安静地如同大家闺秀或者小家碧玉,即使偷偷看上男人一眼也会羞红半边脸。
我昨天在一个饭店用餐时,曾遇到过几个高中女生——也许是初中女生,谁分得清呢?
现在的孩子如同养鸡场的鸡一样,很容易就被各种食物催长的。她们旁若无人地大肆喧哗,席间对班上多位男生大加评价,甚至互相谈论各自的恋情发展状况,一般都是说到床边上的时候才停下来。这让我想起更早些时候去爬山的路上,我当时是个硕士生,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博士,我们在公交车上就遇到了大批大学生和高中生,其中不乏关系暧昧者。大学生情侣通常是站在车厢里牵着手,在车体晃动的时候互相扶持一下。而高中生只能用出位一词来形容了,只见一对稚气未脱的男孩和女孩在车厢中搂得紧紧地热吻,其火热程度让他们的同伴欢呼,让大学生情侣脸红,让我们这些老硕和老博汗颜。
这年头惟一安静的人也许算是处男了。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这是过去的口号,现在改成了处男,你的名字是弱者。一群男孩在一起闲侃,其中最木讷或者最没有话语权的就要数处男了。一般来说,他们脸上神采飞扬的程度和经历恋情的次数成正比。更有不幸的消息是,据说中国目前男女比例已经达到1.06∶1,而在20年后,这个数字将大幅提高到1.2∶1。这意味着20年后将有3000万热血男儿在自己的适婚年龄中找不到老婆,而如果其中处男比例即使是40%,也要有一千多万啊。想想看,一千多万身强力壮的处男静静地矗立在祖国的广阔大地上,而同时代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性们则在男人堆里自由穿梭如鱼得水,男人稍有令其不满意的地方也许就会立刻被蹬掉。想到这,我暗下决心,如果将来结婚要孩子,拼死老命也要个女的,否则还不得为儿子的处男问题操死心啊。如果他像他老爸这样风流倜傥也罢,万一只继承了我基因中的另一面,岂不是他最大的悲哀?
这是个静若处男的时代,而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是静若处男的时代了,而是呆若处男的时代。那时候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男人看到女人就停着不动流口水,你就可以确定他不是色狼,他也不是变态,他对社会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他是处男,他生活在呆若处男的时代。
远离让我爱上你
困困
对城市的情感,有人推崇类似天赋爱欲的说法。原理是一个叫阿兰科尔班的法国人在《气味的历史》中提出的:所有感情的来源,全依仗一个叫鼻犁器的器官作出什么反应。这种理论应用于城市,那就是你爱上一个地方,全因为你闻到了喜爱的味道。简单地说,你与该地气味相投。但以此为依据,我就是个冷血的人,因为我的鼻犁器在闻过许多城市后,都上下皱了皱,发出厌恶的信号。
以曾经暂居的英国小城谢菲尔德为例。它鲜为人知、死气沉沉、了无生趣……如果非要描述点特征,可说的只有两支破败的球队和更加破败的重工业。当然这不是我的鼻犁器对它的判断,但这种背景不能不影响这个敏感器官的运行。我一站上这座城市的土地,就闻到死气沉沉的味道。那是种无聊的,却自认聪明以不变应万变的气息,套用亨利·米勒的话说:“即使太阳像迸裂的直肠一样鲜血直流、地球偏离了轨道、鹅毛大雪从夏天飘下、全世界的城市都濒临死亡,它也牢固地站在那儿,没有创造性、俗套、思想窒息、无冲动,随着世界分解过程的加快而越发具有离心力。”于是我的鼻犁器说,不喜欢这里。而对于在此之前我久居其中的北京,鼻犁器也没被那灯红酒绿迷惑,因为它闻到了喧闹、浮躁、粗枝大叶的味道。
可事情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当我远离谢菲尔德,心却背叛鼻犁器地思念起这座城市。鼻犁器厌恶中心广场上的雕塑,永远是个八个士兵,永远有一堆陈旧的花环簇拥;思念却捕捉到花簇中的黄色水仙,它像块衣衫褴褛的土耳其女奴偷藏在胸罩里的金子,折射着无法掩藏的光。鼻犁器不喜欢一个连一个的青石店铺;但思念却觉得它们的门可爱得紧,每一扇都很低,仿佛专为侏儒和小妖精设计。鼻犁器还讨厌千篇一律的大教堂,可思念却定格在教堂尖顶的铁公鸡——它很有个性地总是朝着东南方向。在鼻犁器的记忆里,谢菲尔德仍带着牙龈脓肿一般过去的味道,可思念在重游此地时,已经跳出记忆——我想念着这个地方,甚至都听到了像炸薯条的油锅一样咕咕的声音,那是曾经蹲在伯顿巷上的一只流浪狗肚子的奏鸣。可我真的像条狗一样蹲在伯顿巷街边的时候,在夜降临谢菲尔德之前,我思念起了北京。
人也是动物,可鼻犁器并不能解释这种对一个曾经不喜的城市的思念。情感或许有神圣莫名之本质,可对于城市的情感,似乎另一种朴实的说法更能表达:城市,总是让人亲近的时候厌恶,离开后又想念。
文思受阻
贝小戎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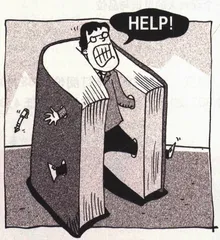
科学研究有个规则,能简单、就近地找出原因,就不费劲去找遥不可及的、复杂的原因。以此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作家写不出新作的三个原因。首先是先前一部作品获得的赞誉。约瑟夫·米切尔1938年入《纽约客》做编辑,佳作不断,1964年他写出了他最牛的作品《现代奇航》。然而在其后的32年间,他每天都照常走进办公室却再也未着一字。1996年《纽约客》在纪念他去世的特辑中有人回忆说,曾经听到过米切尔自己感叹,他一直平心静气地写作,突然有一天跳出一个教授来,夸他是“在世的最伟大的英语叙述大师”,这一夸令他自此武功全废。
艺术家都愿意声名远播,但是名气大了也会噎着他们,甚至砸了他们的饭碗,尤其是在他们事业的初创时期。菲茨杰拉德是成名快、消逝也快的例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遭遇到了文思枯竭,而且反过来以此为题搞创作。1937年他在随笔《论成功过早》中说,过早取得成功让人产生神秘的宿命观念,它拗着个人愿望而行。过早成功的人相信自己心想事成是因为命运星在闪烁。但是星星什么时候不闪了,个人也是浑无办法。同年菲茨杰拉德奔赴好莱坞,想靠写剧本挣钱。上班的时候他还能老实待着,但天天晚上他都要喝得烂醉,直到朋友找到他然后送交医生。很快就没人雇他工作了,只得靠给《绅士》杂志写系列小说谋生,在小说中他还调侃自己: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剧本作者,周薪2000美元——他写剧本的时候周薪其实是320美元。
文思受阻往往发生在写第二部作品的时候。没人在等着你处女作的出炉,但是如果处女作一炮走红,所有的人都会翘首以待,你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作家、写小说的机器,但是你知道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你本来一无所有,现在开始患得患失。1960年,34岁的李哈珀出版了处女作《杀死一只知更鸟》,一时洛阳纸贵,因之她获得了普利策奖,改编的电影也非常成功。但是她的第二部作品一直没有出来,1961年她接受访谈时说她正在写第二部小说,但是写得很慢,一天一两页。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能读到它,但是现在她已经78岁了。
一些作家不知为何自己再也写不出来,有些则是明白人。福斯特出版了6部小说后,在45岁宣布收山。据分析,原因是他三十多岁时终于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觉得自己不能再写异性婚恋,他那个时代同性恋小说又不让出。
写小说总免不了暴露自己的私生活,读者对作家比对自己的亲戚了解得还多,塞林格为此隐居,渡边淳一为此不要家庭生活。“哪怕你写的不是小说,写图书和舞蹈评论都会有陌生人走上前来告诉你他明白你的感受,没错,因为你写文章告诉了他们你的感受。”作家之所以有这么多原因会致使写作中断,只是因为在写作时他们是作家,不写作时他们就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