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代到第六代——奥运中国的个人色彩及其他
作者:李菁(文 / 李菁)

19岁的滕海滨在雅典奥运会上经历了从摔倒到站起的过程
从第一代到第六代
没有一个领域的较量比奥运会更直接、更残酷,也更被人铭记。在社会学家夏学銮理解中的奥运会,是“没有世俗的种族偏见,没有社会分层的歧视,没有民族文化的隔阂,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民相聚一堂,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为了实现共同的奥运理念和奥运目标而努力拼搏,追求人类身体和心理极限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奥运会首先是人类的、国际的,“其次才是民族的、国家的”。
但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得不承认的现状是,让体育回归纯粹的体育、让个人成为纯粹的个人,只是近似乌托邦的美好理想。当前的体育无可避免地担负着超越体育之外的种种功能,我们看到的只是直观的肉体竞技,看不到的却是背后纷繁复杂而强大有力的政治、商业等诸多因素。相对而言,在参加奥运这场国际大游戏之初,中国选手承担的政治意味更浓重,“金牌”与“国家荣誉”相对等。在巨大的“国家”和“集体”之下,运动员的个人色彩和个性光辉显得微不足道。
当20年的变化使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实力已不需要仅仅通过体育来体现,体育承载的道德负担和政治负担才逐渐减弱,更多地回归到它竞技、娱乐的本性,运动员作为一个“个体”和“人”,他们的个性,色彩和光芒也才能得以凸现和释放。
深入观察中国奥运选手第一代到第六代的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荣誉”和“政治荣誉”仍是这场游戏中最重、最无可撼动的两个因素,但与此同时,个人荣誉和经济利益也渐渐加入,丰富着这格局,此外诸如商业、娱乐等因素也注入到一度相对简单的“集体”与“个人”关系中,更使得20年中国奥运之路中的“人”的变化多彩而富有趣味。
金牌之重,个人之轻


亚洲两位“蛙王”赛场之外的传闻同样引人关注
相信这个镜头已经深深铭刻在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1984年,身着红色运动服的许海峰站在领奖台上,接受萨马兰奇的颁奖。这一刻被赋予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已远远超过一个运动员和一项运动本身。
王义夫当时与许海峰仅一步之遥。在此次雅典奥运会上,六朝元老王义夫再度获得金牌。上届悉尼奥运会上,王义夫拿回了块银牌,在首都机场,人们对待金牌获得者的狂热曾深深刺激了他。他当时就对女儿说,等着下次爸爸给你带块金牌回来!
同样的境遇在姚明的叙述更有趣。上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只有20岁的姚明一直是孩子的游戏心态,对输赢并无多少感觉。直到飞机返回北京,因为有领导人要接见同机舱里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男篮被“赶”到机舱后门匆匆离开。也许就在那一刻,才会让队员们体会到拿金牌的意义和分量是什么。“金牌和银牌,就是不一样啊!”回国之后,王义夫在白岩松面前曾忍不住感慨。王义夫既是第一代,也是第六代,而今,“为国争光”的政治责任或许减弱,但金牌仍旧“重”得超乎想象。
奥运开赛头几天,被寄予厚望的体操小将滕海滨、肖钦相继失利,值得玩味的是,纵然国人对这些像集体感染“低级失误”病毒的小伙子们不甚满意,但是当19岁的滕海滨说因自己的失误造成团体金牌的丢失而有“有强烈的负罪感”时,大家又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呼吁将体育从各种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让体育回归纯粹的体育,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运动员的成绩更多时候仍紧紧与“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中国女足失利后“要向全国人民道歉”的心理基础。
如果没有体育,“弹弓大王”许海峰也许现在仍是安徽和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奥运金牌给他的改变也并不仅是工资从供销社的9块5涨到98块的“高干级”,在这样的格局里,对许多运动员而言,体育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不多的机会。
据说在此次奥运会曾被寄予厚望的女子举重运动员李卓上场时,教练都要用这样一句话激励她:“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你!”此次在雅典获得举重冠军的石智勇的母亲告诉记者,“他太想赢了,太想拿冠军来改善家里的现状了”。除了“为国争光”这些我们已并不陌生的表述之外,为了个人利益而奋斗,也是选手们并不隐讳的动力之一。
在8月21日举行的女子200米仰泳比赛中,曾出现了颇令人意外的一幕:战殊和陈秀君两名中国队员以全速奋力游了100米触壁后,突然放慢速度,放弃后一百米游程,在30多位参赛队员中双双跌至最后。这个举动引起许多人不解,晚上,记者采访游泳队教练后才得知,这是中国游泳队为几日后进行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而进行的测试。为此,几天前刚刚获得百米蛙泳金牌的罗雪娟也放弃了200米蛙泳的比赛,但中国队花如此代价的结果是只获得了第四名。
NBA球星姚明VS中国队13号姚明
奥运会的几场比赛使得一个幻象终于破灭:来自NBA的巨星姚明和同样来自NBA的哈里斯,并不能扮演中国男篮拯救者的角色。
姚明发怒曾引起大家的争议。姚明最大的无奈或许是自己所从事的项目是一个典型的集体项目,于是大家引发的争论是,在一向推崇集体利益至上的中国队中,在推崇坚忍、内敛的中国土壤里,什么样的姚明才是被需要的?
2003年,被NBA选中的姚明一脚跨入了美国,也一下子被送到了轰然作响、高速运转的造星机器上,“YAO”顿时成了最具商业价值的中国球员。有人开玩笑说,参加奥运会的整个中国军团的身价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旗手姚明。但在本届奥运会上,NBA球星姚明首先要承担“中国队队员”的角色,他还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无法超越这个集体。
对目前的中国篮球队而言,无疑需要一种有个性、有血性的人带来一种冲击力。问题是在这块土壤上,能多大程度上容忍这种个性,反之,这种个性对这个集体是否也会有伤害?现在这一切似乎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著名的体育记者苏群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首先,姚明“有资格”发火,其次,姚明表达的愤怒从效果上讲,“并没有伤害性”,“不过,如果姚明没有走出去,以他的性格,他真的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在中国,不允许个性的发挥”。
当年,姚明加盟NBA时,有评论说,“两个巨人走到了一起”,其实两者背后还有一个巨人——中国的篮球环境。很长一段时间,姚明努力周旋在两个巨人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段关系,避免王治郅事件带来的阴影。
王治郅2001年成为了中国NBA第一人,在很多人看来,他为一年后成为状元秀的姚明做了“开路先锋”。如今,无论在名气与市场价值上都远远在落后于姚明的王治郅还在NBA孤独地打球。已在美国作了父亲、住在能看见大海的公寓里的王治郅,离中国篮球越来越远。他告诉前来采访的媒体,他并不后悔。
王治郅的问题是,他首先是做“运动员”,还是首先是“中国的运动员”,王治郅选择了前者。除了篮球,他什么都不愿意谈。其实王治郅也比谁都明白,和任何运动一样,篮球,并不仅仅只是篮球。
场内场外的爱情

霍尔金娜和瓦尔德内尔是雅典奥运会没有拿到金牌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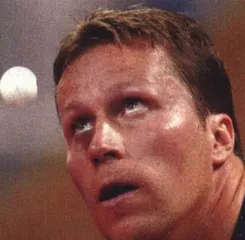
瓦尔德内尔

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应真正事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在本届奥运会,上届射击冠军陶璐娜只取得了令人尴尬的倒数第三名。在出征本届奥运之前,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后的陶璐娜大概也希望像媒体说的那样,能在雅典“用金牌印证伟大爱情”,但偏偏难遂心愿。
尽管陶璐娜一再公开否认因恋爱而失利,但媒体已经宣称“爱情双刃剑割伤卫冕冠军”,射击队总教练许海峰也含糊其辞地说,“恋爱对女孩子影响很大”。当恋爱中的运动员遭受失败时,“爱情”无一例外地成为“千夫所指”。
在雅典奥运会之前,有关“运动”和“爱情”,最轰动一时的新闻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正定情变”——今年元旦刚过,中国乒乓球队突然将四位运动员开除国家队,其中两位分别是马琳和王皓的女朋友,此举显然是为了保障这两位奥运主力专心训练。
拥有铁的意志、为了国家和集体荣誉而舍弃爱情,甚至亲情的故事和细节,一向是媒体在报道运动员成功之路必不可少的重点。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大多数媒体却对此举持否定态度。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获得28块金牌,其中在以乒乓球为代表的优势项目上所取得的金牌数便有26枚,占总数的93%。乒乓球在中国更承载了“国球”角色,每届奥运会之前,民众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期待,已不仅是“能取得几枚金牌”而是“能否夺得大满贯”。外界的种种厚望,转而成为这个集体“一切以国家荣誉和集体荣誉为第一”的最高信念,在此之下,禁止恋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选择。所以也有赞扬者说,正是此举,让人看到了“国球”十年不衰的真正原因。
雅典奥运会的结束,实际也宣告了中国乒乓球队又一轮艰难任务的开始——2008年在家门口,更是要确保国球不失。只是不知是否仍会有有情人为此付出“爱的代价”。
长久以来,在集体荣誉的大局面前,个人情感的牺牲总是毫无条件的。长期以来,禁止恋爱一向被认为是合理、正常的管理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队员谈恋爱也渐渐成了半公开的事情,很多运动队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只要不太出格,都采取默认态度。
但问题是,“爱情”一定是与“成绩”对立吗?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对乒乓球队的处罚决定表示“理解”,但认为恋爱是私人选择。这或许也与李永波教练自己的经历有关——当年,21岁的李永波与15岁的艺术体操运动员谢颖一见钟情。他随后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在个人与爱情、国家荣誉构成的三角关系面前,后两者未必一定是对立的。也许正是个原因,像上一届的孙俊、葛菲,本届的高凌、陈宏等,羽毛球队的情侣一直都是“阳光下的情侣”。
也并不是所有的情侣都愿意把自己曝光,随时要接受各方“是否因感情影响成绩”的疑问。中国跳水队的男女主角田亮、郭晶晶是外界最喜欢提及的一对,有意思的是,“亮晶晶”的爱情并没有得到主人公的明确证实,但全国人民好像早已迫不及待地祝福他们。自我形容为“青梅竹马”的两个人从来不避讳谈彼此,但就是一直不肯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大约就是怕奥运会有所闪失,使爱情成为靶心。国家跳水队的教练说:他俩关系越好,我们越高兴,因为爱情可以孵育出金牌。
运动员的感情生活一向受人关注,特别是明星运动员。当年伏明霞的感情经历就已经超越体育范畴,进而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奥运前一个电视节目到香港拍下了伏明霞像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在菜市场挑选为家人煲汤的材料,周末和夫婿带着女儿到海滩游玩。当初有人分析伏明霞选择梁锦松,其背后的心理因素是过早被挑选进专业运动队,长期缺乏关爱,而大她很多岁的梁锦松恰好填补了早年运动经历带来的缺憾。虽然之前很多人并不看好伏明霞与梁锦松的感情,但镜头前伏明霞一脸知足的样子令人感慨。
本届奥运会上,亚洲两位“蛙王”罗雪娟和北岛康介的传闻一直若有若无地笼罩其中,北岛康介从不掩饰对罗罗的好感,更是到100蛙泳现场为罗罗加油,但在这个事情上,罗罗并不像其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敢爱敢恨,或许,作为一个中国的奥运冠军,她已体会到自己并不能像普通女孩子一样,心无旁骛地接受和享受一段纯粹的爱情。
不过传闻是真是假,中国游坛曾经的“五朵金花”之一钱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却很有意思,作为上一代的运动员,钱红羡慕罗雪娟这一代运动员拥有的情感空间,钱红当年的教练虽然是男教练,但是事无巨细,“是个妈妈教练,管我吃饭,管我很多事情,包括去参加比赛的行李都要管,绝对不让我带爱情方面的书”。所以,钱红羡慕极了像罗雪娟就可以明明白白地跟教练说她还有网上的“男朋友”,“我那时候有男的来找我,跟我说话,教练都把人家轰出去”。
体育的快乐与残酷
每一届奥运会似乎都成了超级巨星的最佳诞生地。单以男子游泳来说,从俄罗斯的波波夫、澳大利亚的索普到本届的美国人菲尔普斯。
当索普或菲尔普斯像鱼一样畅游在水中,仿佛游泳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快乐、轻松、享受。
奥运竞技的最本质应该是快乐的。但在现在,恐怕即使那些站在最高领奖台的选手,也很少有人从中感受到体育本身带来的快乐。瓦尔德内尔在双打中淘汰孔令辉/王皓后说:“对于中国乒乓运动员来说,拿不到冠军就意味着失败。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比他们放松,因为我不怕输,我是来参加比赛的,但更是来享受乒乓的快乐的。”
在现代奥林匹克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的,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他们未必是那些金牌获得者——比如让我们又敬又爱又怕的老游击队长瑞典人瓦尔德内尔。二十多年了,每一次都会把他的离去当成最终的告别,但几年后,他又神奇地杀了回来。
快乐的前提是热爱。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老瓦不会像真正的大侠一样,将比赛结果抛在一边,全身心享受这个项目带给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单挑了数代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男单1/4决赛被淘汰后,39岁的老瓦却像获胜者一样,在全场观众一致的鼓掌中离开赛场。那一刻,老瓦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早已远远超出胜负范畴,他其实就是英雄。支持体操女皇霍尔金娜的,也一定是那种热爱,否则她怎么会在体操场上露出那样迷人的笑容?她的优雅征服了所有人,拿了全能亚军的她仍然得到了全场的欢呼。她是比金牌获得者更受尊敬的运动员。
本届奥运会头几天,男子体操队的肖钦和滕海滨的频频失误给志在夺取团体金牌的中国队造成很大压力,后来媒体记者见到的肖钦和滕海滨始终在队里的兄长保护下与媒体保持着距离,只有19岁的两名队员“像个小孩子一样,冽在角落,几乎不说一句。问到他们,两人总是很一致地摇头或者点头,像是听不懂记者的提问,麻木到让人怜悯的地步。当被问到是否打电话回家时,肖钦轻轻地回答“没有”,“我不敢”……当无法享受体育带来的最本质的快乐时,吃苦、隐忍才成为主题,这样,体育的胜利就要付出残酷和无情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