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有约:与张锦秋、韩骥、贾平凹对话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闫琦)

理想主义者的遗憾
主持人:6月份,北京有700年历史的护国寺西配殿毁于一场大火。痛惜之余,我们还获知,北京不可移动的文物有3500多处,其中60%以上被单位和个人占用不合理使用,西安是否也有类似情形?
韩骥:我国文物保护实际上只有50年历史,保护名单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感觉在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失误,“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在西安,比较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四大遗址”——周朝的丰京和镐京遗址,秦代的阿房宫遗址,汉代的汉长安遗址,还有唐代的大明宫遗址,都是世界级文物。前些年我们与日本合作保护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工程做得相当不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来视察,给予很高评价。但这个遗址周围的环境可以说糟透了,抗战时期,很多河南难民到西安就居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最近新城区下决心把它整理出来,要花多少个亿。
改革开放20年来,保护文物的重要性被逐渐认识到,但西安仍然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考察国外的保护经验后,觉得我们政策上太死。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应该建立一个古都保护基金,而且应该卖股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这个办法,因为跟国家要钱在哪里都不容易,如果有这样一个机构就可以从全世界融资。如果哪一位企业家赚了大钱,他捐出来一些用在文物保护上,国家还可以为他减免税收,保护的文物还可以他命名,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可以做的。
主持人:我仔细读过韩先生的一些文字,您的一些表述给我感觉是一些矛盾的东西。比如您在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中,更多是赞美西安古城保护中做得好的东西,而在参与曲江新城项目评估中却有“西安城市建设搞了这么多年,越搞越令人担心,魂不附体”的感慨。在城市发展和保护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是成功的东西,有一些是败笔。您参加过西安的两次半城市规划,您有没有遗憾?
韩骥:搞城市规划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西安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代表城市,周秦汉唐中华民族的盛世都在这块土地上,从《周礼·考工记》开始,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制度最早也是建立在这块土地上,像中国古代皇城方形的城廓,井字形的道路,皇宫放在中心这样一个典型格局也是最早出现在西安。所以西安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中国的圣地。
当然,理想主义者跟现实一碰撞,就会头破血流。遗憾是很多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就是对农业城市的一个彻底否定,在国外也是如此。国外能保存下来的古城也不是很多,凡保留下来的古城都因为国家非常强大,只有国家强大,它才对自己的传统特别重视。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罗马,都保存得很好。凡保存不好的都是国家比较破落,比如希腊的雅典。雅典早期很辉煌,后来沦为殖民地,土耳其统治时期甚至把伊斯兰的一个教堂就盖在一座神庙里头。上世纪30年代独立后进行了很多清理,但看起来整体上还是很破败,文物破坏也很严重,后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恢复得很好。我就希望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要快,有了这样的基础,遗存保护才有希望。
张锦秋: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存在和发展始终是在不断出现各种遗憾的过程中前进的。中国从古代起就有破坏文物的习惯,改朝换代要将上一个朝代的国都毁掉,然后建自己的新国都,只有北京,保留了明清的格局和古代的宫殿。罗马千年以上的国都保留下来了,我们没有。历史的遗憾我们不追究了,我要说我们现在的遗憾。中国在历史名城保护和古建筑保护方面比发达国家晚了好几十年,但可以学习,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做得还不够好,甚至出现了建设性的破坏,这是最遗憾的。不是我们认识不到,那是因为什么?有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单纯追求商业利润,单纯追求某一届政绩的原因,忽视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避免当前的遗憾,或尽量减少当前的遗憾。
新规划两项重大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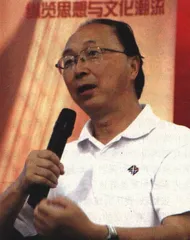
韩骥

张锦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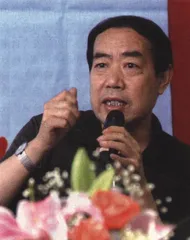
贾平凹
主持人:我们知道,西安在第四次城市规划中邀请了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规划师就方案提出建议和评估,有什么比较有价值的新建议和新想法?
韩骥:其实古城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早就有的,这些见解我们也有,但人家外国专家一说,领导就更重视一些。从个人比较,其实大家学问也不相上下。大伦敦规划委员会的主席来了,伦敦他搞得很好,他提了一些建议,说话就很有说服力。这次规划我感觉比较重大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把西安的古城保护放在八百里秦川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考虑,这个意见是我国的大专家郑孝燮提出来的。他有一个观点,关中是一个文化带,由四个要素构成:一是南边的秦岭山脉,他说不要简单地把秦岭看成就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看成一片绿色,秦岭在历史上孕育了西安的发展,而且在秦岭山络上有许多寺庙,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文化活动在这个地方发生。秦岭是一个文化带,渭河是一个文化带,渭河和秦岭之间是一个历史的城市带,什么丰京镐京、咸阳、西安,都在这个带上发展。另外,渭北是一个古代的陵墓带。我到埃及考察过著名的帝王谷,在一个山沟里安置了几十个帝王的陵墓,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墓群。我拿它跟渭北一比较,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渭北从周朝的陵墓一直到唐代的陵墓都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帝王陵园,而且跟埃及的格调很不一样。埃及是在一个山谷里面放了这些陵墓,很阴沉;我们这里是在渭北高原上安放这些陵墓,特别是乾陵,异峰突起,前面是渭水,非常气魄。如果能从八百里秦川这样一个背景来保护西安的文物古迹,应该说前景是非常美好的。第二,市政府已经决定了要把行政中心从旧城迁出去,至于是南边还是北边正在比较。这是一个重大步骤,北京就吃了这个亏,领导机关在旧城,许多东西都围绕它发展,这个城市越大,旧城就越拥挤。西安已经错过了时机,本来在80年代初期就应该迁出去,那样旧城就不是现在这样拥挤的局面了,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改造,破坏了许多民居。上面这两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希望能够促其实现。
主持人:历史名城保护涉及规划的一块,也有古建筑保护和新建筑如何体现城市特有文化特征的一块。记得司徒雷登当年创建燕京大学时明确提出:校舍的外型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征,里面要有最现代化的设施,我们要让学生明白,学校希望你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对一切科学新知积极追求。后来我想,这可能不只是对一个办学宗旨的追求,是不是在新的建筑上要体现传统文化的东西,这种内外结合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呢?
张锦秋:这个原则在欧洲古建筑保护中一直遵循着。欧洲的古建筑是砖和石头垒起来的,几百年没有变化,但内部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人住在里面很阴湿。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经验,保持建筑的艺术价值,保持其外貌和城市风貌不变,但设施要现代化,使得现代人住在传统建筑里面还是很舒服,这是对古建筑加以保护的一种好方法。像北京的四合院,说它很好,格局很人文化,天人合一,最后里面的厕所却是干厕,就不行。西安的历史街区如书院门、北院门,那里还有很好的宅子、大院子,怎么让那里的人觉得住着舒适呢,就要把现代设施接进去。
新建筑创作要分清所设计的建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在老城区,怎么跟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相适应,甚至旁边就有钟楼、鼓楼,或者跟任何一个文物建筑相邻,新建筑设计就要充分考虑谐调和城市的综合美,就不能随便做玻璃盒子,做轻钢的轻型屋架。谐调不一定是要一模一样地去仿古,但是高度、色彩、风格要相适应。如果是给高新科技开发区或者南二环以外的城市新区设计新建筑,可以更放手地盖高层建筑、大跨度的轻型屋盖,使用玻璃幕墙等。建筑界对新区的建筑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你可以无所顾忌,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另一种认为西安的新区跟深圳等新开发城市的新区还不一样,还有一个文化的延续,使人感觉这是西安的新建筑。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不是简单弄一个灰瓦屋顶或者灰砖墙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就要求建筑师要有创意。
主持人:您个人是否认同后一种方式?
张锦秋:我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新区的最高要求,最好是还有这个城市文化的一种意蕴反映在现代建筑中。但这很难,不能要求所有的建筑师都达到这一点,国际上也是如此。比如体育馆,古代没有体育馆,现在是大跨度大空间的,没有什么传统风格可言,可日本的丹下健三设计的体育馆,完全也是新结构,怎么一看就有日本味,这不是一般建筑师能达到的。
历史名城要追求高贵气质
主持人:刚才贾老师说到许多城市差别越来越小,大家都有旅行的经验,比如坐着飞机到了西安、广州、成都,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好像只有站在西安的南门、朱雀门下,我才觉得这里是西安。所以,虽然是对设计师很苛刻的要求,但真是希望每个城市有他自己特殊的标志,有一些体现他独有文化的东西,不知道贾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贾平凹:我同意。因为人和人的区别是在脸上,一个人没有特长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城市没有特点就是一个平庸的城市。我觉得人有灵魂,城也应该有灵魂,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城市的风格和气质是什么。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中央机关所在地,一系列政治事件发生在那里,高官多,有天安门、中南海这些建筑在那里,这个硬件有了以后,城市环境就影响市民心态和精神的东西,所以北京人一说就是政治局的事情、总理的事情,西安人一说就是处长、科长的事情。北京人口气大,会说,那种气质就出来了。广州是个经济城,有广交会,咱们这里批服装的都去那里,硬件产生后,那个城市的人就有了经济头脑,会做生意,价值观念变了,对数字的崇拜和财神爷的崇拜很普遍,就形成市民文化的东西。中国在汉代唐代最强盛,有人家里收藏很多汉罐,其实那不是当时的艺术家做的,而是一帮工匠做的,但是那些东西非常质朴、大气,为什么大气呢?国家强盛老向外扩张,它渗透到一个老百姓一个工匠的意识里去,做什么就都大气了。
说到西安,历史上建立了13个王朝,有钟楼、城墙等保留下来,这些年张大师给西安贡献了很多好的建筑,这些建筑和古建筑很和谐,是大师级的作品。虽然理解张先生所说的不能要求所有建筑都有这样的水准,但还是更要提倡和推荐大师级作品。我觉得西安现在有一些标志性建筑,在领导人理解中,这些建筑要有实用性,我觉得不一定,可以是一部分有实用性,一部分是象征性、标志性的。城墙和钟楼从使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来讲毫无意义,还影响交通,但是城墙给西安增加了好多光彩,是说起西安就会想到的一个标志。在家里也一样,西安老城形成人的灵魂就是很质朴、很浑厚、热爱收藏的人多,爱字画的人多,古文化城市就是产生这样的文化。西安好的收藏家很多,他收藏东西不是为了倒卖,他是为了在家里摆设,为了养他。你到人家里看到这些好东西,你马上对主人就尊敬了,觉得他很有品位。所以一个城市要有实用性建筑,但也要有一点标志性的建筑,就像家中的收藏品一样,比如你家收藏了兵马俑,只能到你家去看,这样马上会对这个城市起敬意。
张先生已经做了许多好的作品,我很自豪,外地来人总是带着他们去欣赏一番。我觉得仿古得让高水平的人来仿,不要让人以仿古的名义搞些建筑垃圾。一定要有古意,钟楼附近、书院门附近和南门附近的一些建筑,我不满意。提倡民族传统为什么总搞些明清以来的东西,最强盛时期的汉唐风格搞得很少。挂红灯、耍狮龙灯等都是衰败时期世俗的东西,不是精神高贵的东西。西安还要营造规划分类,要有历史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古乐馆、遗迹馆等,标志性大的建筑再加上一些小的规划古文化氛围,那么这个城市的灵魂肯定就圆满了。
读者:西安的城墙作为西安的一张名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把城墙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好像与600多年的城墙留给我们的历史和资源比,相差很远。就城墙下一步的开发和保护,如何从建筑学和文化传承的方面进行统一?
张锦秋:我认为城墙和城门楼首先是保护,保护是有规定的,就是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和它的综合性。真实性就要保持原有的面貌,按现在的文物保护法是不能随便在上面盖亭子,建花园的,这就改变了城墙原来作为防御工程的历史真实。但我觉得可以很好地把历史文物利用起来,比如说四个城门楼是关起来,还是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利用起来?文物局的人只是把房子修好了,还没有想到怎么来用,应该有更多的热心人向政府提出建议。我们要赋予历史遗存新的生命力就要很好地去用它,而不是去改造它,把城墙挖空了。
城墙还是一道很好的风景线,有电瓶车在城墙上走,往城外看,风景很好,可头一扭往城里看,顺城路就丑陋不堪,现在西安市政府要启动顺城路里面的保护和改造工程。一些老的倒闭的工厂破破烂烂,个人私搭乱建的危旧房屋也很多,有些路根本就不通,这道风景线只能往外看,脖子不能转。所以城墙里100米范围之内应该很好地规划,好的民宅和寺院都要保护下来,不好的也不是简单一拆去搞房地产,旧城沿城墙这一圈怎么改造、保护,保护建筑的周围也要盖四合院,怎么个盖法,就要根据城市原来的机理很好地织补,这个规划设计必须是高水平的,如果让开发公司的设计室搞很多商品房,那这道风景线也就破坏了。
读者:我家在渭南,改革开放后那里出现了城中村,虽然房子很丑,但像贾老师说的他喜欢丑石,因为丑中也有美的东西。住在那里不担心会塌下来,因为房子很结实,有智慧在里面。这样的房子能不能也保护一些?
韩骥:城中村本来是要改造的,但是你的愿望很容易实现。现在不是保留的问题,而是拆不动的问题。以后都改造完了,再留下一个,这样的想法也很好,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村子,留下来,将来让人们看一看。这也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一种古城保护的观点,就是说,不要只保护文物,现在的东西再过几百年也是文物,只要它在历史上发生过就要保护它。下次我再做规划的时候,一定参考你的建议。
张锦秋:全世界要保存的城市或者建筑,要符合三个要求——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刚才说的城中村,没有艺术价值,没有科学价值,但我认为,它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保留一个村我是赞成的。
(对话全部内容请登陆西安“古城热线”live9.xaonline.com和本刊网站www.lifeweek.com.cn“做客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