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特富龙:杜邦的信任危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尚进)

“不粘锅有害,还是用传统的铁锅安全。”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了民间自发的应对反应
当7月8日美国国家环保署对杜邦公司的一项指控传出后,谁也没料到在此后的一周,全氟辛酸铵(PFOA)问题没有成为不沾锅使用率超过95%的美国百姓话题,反倒引起了仅仅5%人口使用不沾锅的中国民众的怀疑。实际上美国国家环保署仅仅是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及杜邦公司没能够及时提供有关全氟辛酸铵(PFOA)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存在风险的信息,违反了美国环保署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资源修复法的内容规定。而问题的核心全氟辛酸铵,从一种杜邦特富龙不沾锅生产过程中的化学助剂,一下子成为了所有问题的焦点。
因为全氟辛酸铵有8个碳原子组成,所以在杜邦内部被称作C-8,美国环保署的指控正是围绕这8个碳原子展开。而并不是国内普遍报道的针对特富龙或者不粘锅。实际上全氟辛酸铵引起美国环保署的关注,还要追述到2003年夏天,美国广播公司曾经播出一段节目,当时一名曾在杜邦西弗吉尼亚工厂就职过的女工在1981年生下一个畸形儿,她认为是因为自己接触过全氟辛酸铵所造成的后果。而一个名为“公众利益看门狗”的民间组织则把全氟辛酸铵的怀疑直接附加在了不粘厨具上。尽管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都拒绝对特富龙进行调查,但是美国国家环保署还是盯上了全氟辛酸铵。
当国内媒体看到美国同行根据美国国家环保署新闻稿撰写的稿件后,杜邦和不粘厨具一下子成为舆论的焦点,而最初并没有人关心真正的焦点全氟辛酸铵。杜邦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任亚芬告诉记者:“杜邦美国总部非常惊奇于中国媒体和公众对特富龙的恐慌,即便在特富龙不粘厨具普及率95%以上的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实际上科技类媒体对于全氟辛酸铵的疑问早在2001年7月就开始了,当时《自然》杂志发表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斯科特·马伯瑞的论文,关注含氟聚合物对于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任亚芬告诉记者:“特富龙不粘锅已经使用了近半个世纪,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认为特富龙涂层作为家庭厨具是安全的,类似国内消协的美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也认为不粘涂层是安全的。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美国环保署提出来的针对杜邦的问题,是一个行政报告程序的问题,而并不是要否定所有人用了一辈子的不粘厨具。”
目前对特富龙不粘锅的安全争论,主要集中在了温度上。杜邦技术经理王文莉告诉记者:“全氟辛酸铵这类氟化物在130摄氏度以上就开始分解,350摄氏度时就能够完全分解气化掉。而杜邦的特富龙不粘锅技术工艺要求在427摄氏度下连续烧5分钟。”目前国内的疑问集中在全氟辛酸铵是不是会有残留,而杜邦对特富龙的使用标准说明上,明确可以在2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烹饪。询问技术经理王文莉得知,杜邦之所以设定260摄氏度的标准,主要是为了保护不粘锅的使用寿命。那么在生产工艺中是不是会产生全氟辛酸铵残留,残留的含量是否安全,以及全氟辛酸铵到底与所谓致癌物质有多大的联系,直接成为了疑问的延续。尽管杜邦公司的相关人员不断解释全氟辛酸铵是助剂,会在生产过程中挥发,但是德国汉堡大学实验室曾经进行的研究认为全部挥发并不容易。而国家质检总局也从7月13日最初的没有检测这个技术的设备和能力转变态度,已经开始与美国环保署配合,准备在9月份拿出检测报告。目前国内不粘锅市场除杜邦以外,日本大金、江门建厂的Whiford也有用不小的市场份额。而杜邦仅仅在中国、比利时和美国生产有关特富龙的产品,而美国和比利时更多生产特富龙容器管道类产品,中国则为全球市场制造不粘厨具,杜邦授权技术标准几乎成为了中国厨具业国际化生存的一部分。
公众信任的空洞:退回到铁锅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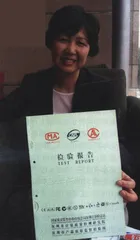
杜邦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任亚芬拿着特富龙的国内定期监测报告


户外运动中的杜邦材料在背包、鞋、手套和外衣的服装上使用,可以使其坚固耐磨
杜邦公司的员工在接受采访中更喜欢用误报来看待目前特富龙危机。在他们看来,杜邦没有被罚款,也没有被美国环保署裁定过错。他们更普遍将此事件看作美国环保署跟杜邦之间关于行政报告程序的争议,在中国却演变成了一场炊具安全大讨论。传播研究界的潘先生视这次特富龙的国内媒体报道为怀疑主义的盲目,在他看来,这与去年众多国内网站集体刊登比尔·盖茨被刺杀,或者2002年著名的木乃伊怀孕了,本质是类似的。如何有效和准确的引导公众舆论,尤其是安全消费的舆论成为了特富龙信任危机后面对的问题。
“杜邦总部很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怀疑主义情绪。”杜邦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任亚芬说,“公众对于自身健康安全的重视似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不断的毒酒和毒奶粉事件,以及黄花菜、银耳、韭菜等等爆出的一系列食品问题所积怨的信任危机,被释放到了杜邦身上。“不粘锅有害,还是用传统的铁锅安全。”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了民间自发的应对反应。
实际上公众对于杜邦的印象更集中在不粘锅上,似乎特富龙就成为了不粘锅的代名词。其实杜邦的产品早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很多细节。譬如高露洁牙刷的纤维、枕头中的尼龙填充物,以及纸张布料等诸多需要汰白粉的产品中。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化学新技术,成了特富龙危机中新的话题。尽管任亚芬反复向记者讲述自己和所有杜邦员工对特富龙安全的信任,以及反复谈及北美不粘厨具的普及率,但仍然有专业人士提出,化学用品是不是也需要长期临床观察,满足商业需求以外的安全需求成为了新的矛盾点。
“保守主义的技术恐慌永远是每一个时代的磨合期故事。”马歇尔·麦克卢恩在他的《电子积木》中写道。这场特富龙危机俨然与罗马俱乐部1968年的《增长的极限》中的信任危机一样,公众对到底该信任谁产生了迷乱。杜邦的一面之词仍然不能说服大多数公众,国家质检总局的技术不足论和缺少检测能力也令人失望,而美国国家环保署则成了遥远的安全观察者。影响更为深远的远不止直接针对特富龙,到底能不能信任化学改变生活,成为了特富龙危机后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而就在大家还对特富龙满腹狐疑的讨论时,7月17日的特富龙用户俱乐部活动并没有受影响,使用特富龙不粘锅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做菜中大量放油的问题,与油类增长脂肪的危害相比,对特富龙的怀疑危害显然要小得多。难道只有退回到铁锅时代才是安全的吗?
特富龙(Teflon)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包括聚四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及各种共聚物。由于含氟表面具有耐腐蚀和耐磨润滑的特性,从不粘厨具到人造动脉,从汽车活塞到大型管道都可以看到特富龙的身影。
化学是如何改变生活的
1802年法国难民杜邦家族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白兰河地设立了火药厂,将铅单射击的更远成为了19世纪杜邦的目标,而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令杜邦火药生意积累了大量财富。
石油化工成为了20世纪初所有化学人的最大发现,杜邦首创的人造丝、人造橡胶、尼龙、各类合成纤维成为了大化学时代的产物。
1938年尼龙的出现,让刷牙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牙齿不需要再与猪鬃牙刷打交道了。
1969年阿波罗计划,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登月服可以抵抗瞬间温度从零下120摄氏度到零上160摄氏度的骤变,当年宇航服的21个保护层中20层来自杜邦。
1971年杜邦研究出的凯夫拉纤维彻底改变了战争伤亡概率,依靠这种纤维生产的防弹衣成为警察和军队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