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幸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彼得·梅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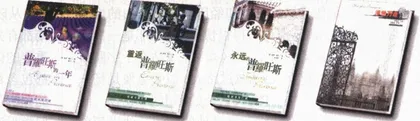
有一天,你突然不告而别,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向。两个星期后,当朋友已经不再谈论你的失踪,快要把你遗忘的当口,所有的人突然都收到你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淡淡的红酒酒渍,有法国南方阳光的余温——明信片寄自法国普罗旺斯。你和你的朋友都是段位不低的积年小资,大家明白这是你闷骚型的炫耀,但还会有很多人向你致敬,因为普罗旺斯是全世界小资心目中的天堂。
普罗旺斯的天堂地位是由小资教父英国人彼得·梅尔1989年钦定。那一年,49岁的梅尔出版了《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全球畅销,给梅尔带来了滔滔不绝的声誉和版税。BBC将《普罗旺斯的一年》制作成电视片,但电视片的风评不佳,普遍感觉摄像机无法表达梅尔文字的情调和趣味。
今年64岁的彼得·梅尔出生在英国的布赖顿,21岁赴纽约从事广告业,在国际顶级广告公司工作了15年。35岁退休,开始为时尚杂志写专栏,以专家资格评介吃喝玩乐,成为享誉国际的美食评论家。岁登五秩之际,以一念之得,带着夫人和两条狗,直奔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不过,梅尔人隐而文彰,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媒体间。他的九本书都在他隐居期间大卖——这九本书都有中文译本,其中三本是普罗旺斯系列:《普罗旺斯的一年》、《重返普罗旺斯》、《永远的普罗旺斯》。今年他的第十本书《美好的一年》也已上市。
梅尔的普罗旺斯代表着一种很时尚的隐居生活。该赚的已经赚到了,想看的已经看够了,能玩的已经玩遍了,于是远离尘嚣,仔细地过自己的日子。他在普罗旺斯买下了住宅,“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可达3500英尺,由西而东蜿蜒64英里。参天的衫树、松树和橡树使卢贝隆山终年郁郁葱葱,为野猪、野兔及各类鸟兽提供了理想的家园。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麝香草、熏衣草和蘑菇随处可见。如果在天高气爽之时,站在山顶登高远眺,目力可及之处,一边可遥望阿尔卑斯洁白的雪峰,另一边则可将蔚蓝的地中海尽收眼底。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在山区散步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影。无形之中,我们的后花园向外扩充了247000英亩,这里俨然形成了一片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想象一下这种生活,起码可以发现都市“豪宅”的俗气、可笑和局促。
在《永远的普罗旺斯》中,梅尔回到伦敦,发现“自己居然改变了这么多。挂在每个人嘴上的永远是钱、房产价格、股市或者大大小小的公司琐事。曾经被人抱怨个不停的天气现在没人提起,虽然它还是那么糟糕,这一点倒是一点都没变。日子就在满天飘着的灰蒙蒙的细雨中度过,街上的行人弓着背躲着下不完的雨。交通几乎停滞,但是大部分司机似乎都感觉不到——他们在忙着打电话,忙着讨论金钱、财产。想念着普罗旺斯的明亮、空旷,还有晴朗开阔的天空,这时,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城市居住”。
梅尔笔下的那些普罗旺斯居民,差不多就是从巴尔扎克时代活到现在的法国外省人,热情,狡滑,爱管闲事,其实十分天真。永远没有城里人守时、效率、私人空间……等等现代文明的观念。那里很普通的一顿正餐会有十道菜,要喝掉六瓶酒,历时三个小时。值得一提的宴饮起码在五个小时以上。那里有各种古怪的口音、礼仪和身体语言。大家都懒洋洋、醉醺醺、没心没肺、快快乐乐地活着……要概括梅尔的三本书不太容易,最好还是去读他那些重重叠叠的小故事,把普罗旺斯的一切串联起来,你居然会有一种很幸福的印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普罗旺斯系列,译文很对得起原著,是我读过彼得·梅尔的中文译本里最好的三种。
孙曜东是稀世奇珍级的老上海,曾经是周佛海的机要秘书,也是地下工作者,现任上海市徐汇区的侨联顾问。由他口述的《浮世万象》(宋路霞整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记录了与老上海相关的种种流言蜚语。他和张伯驹是换贴把兄弟。而张的第三任夫人潘素,原来曾在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她和张伯驹成就因缘,还是靠孙曜东的搭救。我看过的所有黑白老照片里,惊艳的丽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林微音,一位就是潘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