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操纵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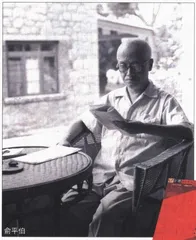
俞平伯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知觉是有范围的,心理学的专门说法叫“知觉阈”。能被人感知、被人意识到的信号必须在强度上超过知觉阈限,有很多信号的强度高于人的“登录阈”(对眼睛、耳朵等器官发生影响),但低于知觉阈。换句话说,你对这些信号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觉,但这些信号对人的行为具有意义,它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亚知觉”(subperception),它进入人的潜意识,不知不觉地改变人的行为。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维克里曾经做过实验,他和一家电影院的老板谈妥,安放了第二台电影放映机,在影片画面间歇的一瞬间(0.003秒)在银幕上投射“可口可乐”和“请吃玉米花”的字幕,这些信号低于知觉阈限——只有持续时间不少于0.05~0.06秒的视觉形象才能为意识所接受,甚至预先得到提示的人都无法注意到这些画面,但眼睛却看到了。维克里推测,这些信号会在潜意识的某处留下痕迹。实验进行了几个月,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第二部电影放映机打广告的那些场次,商亭可口可乐销售量增加了16%,玉米花的销售量增加了50%。这大概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意识操纵”,据说西方国家明令禁止利用亚知觉进行广告宣传。
《论意识操纵》([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全书80万字,作者不遗余力,把有关“意识操纵”的各种材料和研究成果几乎搜罗殆尽,涉及符号系统、思维、情感、想象、注意力、记忆、社会意识、大众文化、公众设施、大众传媒、电视……卡拉一穆尔扎是正统的苏联学者,对苏联帝国的崩溃痛心疾首。他认为苏联在冷战中的最后失败就是败于西方的“意识操纵”,败于西方对苏联社会文化核心的“分子入侵”。翻译成中国人的话来说,苏联和西方原来都是内外兼修的绝顶高手,武功不分上下,西方最后技高一筹不战而胜靠的是邪派功夫摄魂大法。
比较有趣的是,作者用来支援自己的学术材料几乎都来自西方,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西方媒体批判理论的集锦。作者最为深恶痛绝的是现在大行其道的“马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知识由分散的碎片组成,这些碎片是靠时间、谐音、联想等偶然的关系连接而成。这些碎片不形成结构,但它的聚合力不亚于古老的逻辑联系。这些知识“不是由教育系统,而是由大众传媒形成的”。“马赛克文化”的概念也来自西方学者。
即便作者对当下“意识操纵”黑幕的种种描写都是事实,他对美好旧时光的怀念仍然不能成立。硬性的意识灌输和软性的意识操纵有根本的区别:受众的权利大不一样。在“意识操纵”时代,观众有拒绝、抗议和批判的权利,甚至能够像卡拉-穆尔扎那样,干脆写一本《论意识操纵》,与大众媒体分庭抗礼。
团结出版社今年推出一套“红楼大家丛书”。这里的“大家”不是大众,而是大师。已出的三种是《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点评<红楼梦>》、《周汝昌点评<红楼梦)》、《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几位大师中我比较喜欢俞平伯的文章,俞大师的文章心平气和,说话有根有据,读《红楼梦》就是读小说,没有激烈的言辞,很少想入非非的杜撰。对曹雪芹能以常人视之,知道他高明的地方,也能看出他的笔误。香菱跟黛玉学诗,黛玉告诉她说:“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便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俞平老看出了毛病:“当真做律诗,把虚字对实字,实字对虚字,岂不要搞得一塌糊涂?难道林黛玉这样教香菱而《红楼梦》作者又这样教我们么?这是承上文‘平声对仄声’,句法顺下,因而致误。恕我不客气说,恐非抄者手底之误,实为作者的笔误。”还有刘姥姥在大观园吃的茄子,尽管凤姐说的头头是道,俞平老一琢磨,那样的“茄胙”根本没法做。
考据也是中国功夫,过去比少林功夫更有成就。《趣味考据》(王子今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2004年3月第3次印刷)半年里发了一万多册,应该算成绩不错。这本书收的都是今人的作品,题目也很有趣,从豆腐到触器,满目琳琅。如果图片再多一点,会更好看。